♀ ♂
「如何閱讀一本書」初版發行於一九四〇年初,最令我感到驚訝,同時我也得承認,使我感到慶幸的是,這本書立刻成爲當時的暢銷書,並且名列美國暢銷書榜首達一年多。自一九四〇年以後,本書繼續以精裝和普及本廣泛發行,同時還被翻譯成各國文字:法文、瑞典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然而,我們爲什麼又要爲這時代的讀者重寫,及重新編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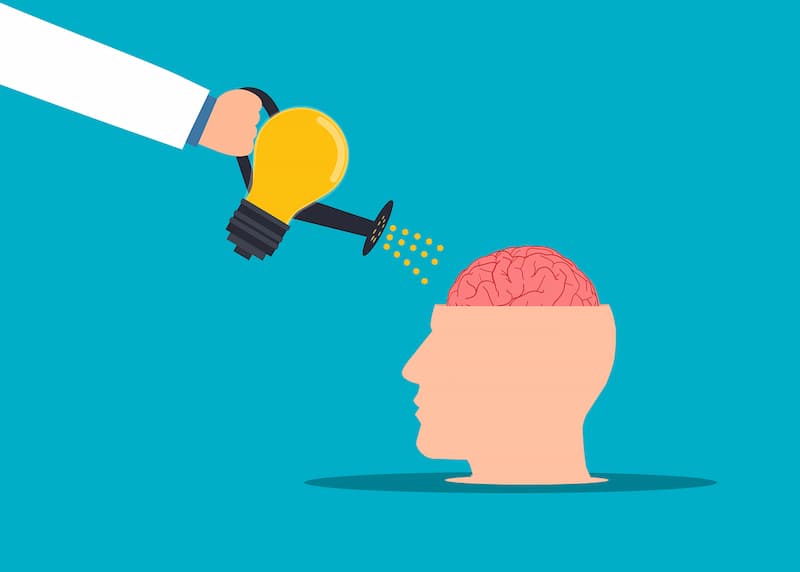
我們所以重新發行這本書,主要的目的是爲了使這本書所討論的主題,能順應近三十多年來的社會變遷。在目前的社會中,大部份青年男女都有機會接受高中及大學教育,或藉着電視、收 音機的普及,脫離文盲階段,而且一般人的閱讀興趣;也已走出虛構的小說而轉向非小說的作品。國內的教育家也認爲教導這些年輕人閱讀的方法,是我們目前教育上最重要的問題。一位健康教育、福利主管部門的現任秘書指出:八〇年代是閱讀的時代,他同時還指出美國聯邦政府不皆提供經費支持一連串有關教育的措施,以增進大眾在閱讀的基本技能上的熟練程度,這些做法不僅使孩子們對閱讀的藝術有所啓發,而且也使許多成年人紛紛被某些標榜增進閱讀速度及閱讀能力的速讀補習班所吸引。
無論如何,近三十年來,還是有某些精神仍然保留不變,其一是 —- 第一個人如果想要達到閱讀的目的,就必須懂得以不同的、適當的速度閱讀不同的作品。正如同三百年前法國巴斯卡所說的:讀的速度太快或太慢都一樣無法了解任何作品。因爲速讀已在國內造成風氣,因此「如何閱 讀一本書」最新版就針對這個問題,以不同的閱讀速度閱讀不同的作品,作爲解決的辦法,以追求更顯著的閱讀效果;閱讀的速度有時必須提高,有時則必須慢慢來。
很遺憾另一件沒有改變的事是 : 除了初級層次的閱讀指導之外,再沒有增加其他的閱讀指導。六年的小學教育中,教育上的大部份注意力、金錢、心血都着眼於閱讀指導方面;此外,幾乎沒有提供其他正式的訓練,以引導學生進入更高層次的閱讀。 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的詹姆 士‧馬歇爾教授 (James Marsell) 一九三〇年在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 「學校教育的失敗」一文中,提出很貼切的評論,下面我們所引用的兩段話,至今仍然沒有改變:
學生在學校教育中,是否曾有效的學習他們的母語?小學五、六年級是整個學習階段中最 軌道的時期,大部份學生都接受有效的教導和學習,我們不難發現該階段的教育已趨於普遍的穩定和進步。但是除了這個階段外,其他時期的學習曲線都降至最低,但這並不表示小學五、六年 級是個人學習能力的自然極限,反而有很多證據一再顯示,年級更高的學生經過特別的指導之後,學習能力可能會有更大的進展。然而,這並不表示大多數人都能閱讀所有實用性的作品,很多高中學生的成績不佳,是因爲無法了解書中的意義,事實上,他們只要改變閱讀技巧,就可以了。
一般高中畢業生都已經閱讀過不少讀物,如果他們能進入大學,就必須讀得更多,但是他們可能是一位無法勝任的讀者(請注意,這只針對一般學生而言,而非指受過特殊訓練者而言),他也許能閱讀簡單的小說,但如果閱讀經過縝思撰寫、結構緊湊的作品,或者必須運用思考的文 章,就可能無法勝任了。從某些事實中,我們可以證明,例如:一般高中學生都拙於敍述所閱讀之文章的意思和重點,另外,大學生在各方面的表現也都顯現他只有小學六年級的閱讀水準。
根據本書第一版的銷售情況來看,如果三十年前需要本書,那麼今天的閱讀情形,更需要這本書。但是我們重寫本書的動機,並不是爲了響應這種迫切的需求;相反的,對「如何閱讀」這個問題的新領悟、對複雜的閱讀藝術做完整的分析、如何彈性地應用不同的閱讀方法、找出並制訂閱讀的新規則、以及有關閱讀書籍的金字塔觀念,從廣泛到專精閱讀的選擇等,這些我在三十年前完全沒有提到的閱讀精神,都是我重寫、重印這本書的眞正原因。
「如何閱讀一本書」出版後不久,另一本模仿它的作品「如何閱讀兩本書」跟着也在市面上出現,同時理查敎授也寫了一本有關「如何閱讀一篇文章」的作品,我提及這些模仿作品的用意是要指出:這些書所提及的閱讀問題,尤其是閱讀一系列相關作品時,所必須面對的問題,都包括在這本重寫的書中。因此,讀者如果閱讀那些作品時,對於同一主題其他作者所補充或衝突的部份就能一目了然。
在這些重寫本書的理由中,我們強調閱讀的藝術及對這種藝術更高水準的需求,而這在第一版中我們並未提及或詳述。如果讀者想要比較本版和第一版的內容時,只要參考目錄就能了解增加的部份。書中的四個部份,只有第二部份「詳述分析閱讀的規則」和原有的內容分量相當,但也已經過大幅度的改寫。第一部份中四種閱讀層次分類初級閱讀、檢視閱讀、分析閱讀、綜合閱讀的介紹,是本書結構及內容上主要的、決定性的改變。第三部份有關不同閱讀題材——實用性和理論性作品、想像文學 (抒情詩、小說 、 史詩 、 戲劇)、歷史、數學、科學、哲學及雜誌、參考書、甚至廣告等各種不同閱讀方法的解說,是篇幅增加最多的部分,最後,第四部分綜合閱讀的討論則是全部新增加的部份。
重寫這本書時,我得到查理士・范多侖 (Charles Van Doren) 的幫助最大,多年來他一 直是我在哲學研究機構的助理。我和范多侖有八年共同寫書的經驗———我們一起指導許多叢書的討論會,並在芝加哥、舊金山及里斯本的討論會中擔任主席時密切合作的經驗,這也正是使我們合作重寫這本書時,更得心應手的基礎。
我非常感謝范多侖在這些合作努力中的貢獻;我們還要感謝我們的朋友亞瑟 . 魯賓(Arthur L. H. Rubin) 對我們提出很多建設性的批評和指導,並且說服我們做很多重大的改變,使新版的內容和原版有所區別,也變得更充實、更有用,而這也是我們所期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