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白人父親

(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
簡 介
他是一位十九世紀的「基督徒醫生」,也是第一位深入非洲 —- 當時在西方世界眼中的黑暗大陸,在那宣揚福音的英國人;他不僅是一位披荊斬棘的探險家,更是一位為理想奉獻的傳教士。時至今日,在非洲地圖上,仍有三十幾個地方 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非洲土著們稱他為「非洲人的朋友」,李文斯敦的仁慈長存於非洲土地上。
身為一位英國傳教士,李文斯敦展現出不同凡響的風範。他一生充滿了說不完的冒險傳奇故事,更為他的傳教生涯增添了不少英雄色彩。年輕的時候,他立志要讓非洲成為全世界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地方,而除了致力將福音傳入非洲以外,他更以文明世界的經驗,幫助當地發展貿易、交通、經濟與教育;並且身體力行、深入蠻荒,以其所學來幫助因醫療技術落後而病魔纏身的人們。他是維多利亞時代最為人尊敬的英雄,他所建立的典範,也影響了近百年來的傳教志業。
好奇的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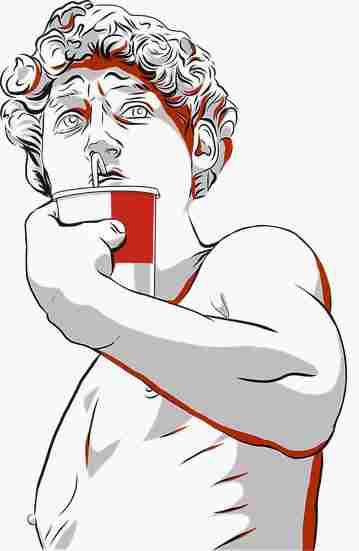
1813年3月19日,大衛・李文斯敦出生於蘇格蘭的布蘭泰爾,一個貧窮卻虔誠的基督徒家庭。
年幼的他聰明伶俐,不到十歲,便因背誦聖經詩篇第119篇(詩篇最長的一篇)而得到背誦聖經獎。擁有強烈好奇心的他,更在生活中展現了過人的勇氣與毅力,在孩童時代,他的足跡就已踏遍家鄉,四處採集植物與觀察生物,從不對未知的世界感到害怕而卻步。藉著這樣的行動,充分滿足了他認識大自然的渴望。
學習的熱情
1820年,李文斯敦進入布蘭泰爾小學就讀。1823年,蘇格蘭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農產品價格大跌,失業率也水漲船高。李文斯敦的父親所經營的茶葉買賣,也因茶葉的銷量銳減而不得不喊停。同年李文斯敦與父親、哥哥都進入了鎮上的綿紗廠工作。兄弟兩人只能等到下班後,才能到夜間部的小學上課,直到晚上十點鐘才能回家;而隔天早上清晨六點,就得起床準備到吵雜的棉紗廠開始一天的工作。
李文斯敦在棉紗廠辛苦工作,第一個星期的薪水,只有五先令。他將一半的薪水交給母親貼補家用,另一半的薪水則拿去買了一本簡明的拉丁文辭典。不買零食、不買糖果,一個十歲孩子的第一份薪水,竟然是拿去買一本辭典,實在是令人感到讚許以及慚愧!
在吵雜的棉紗廠裡,紡紗機運作的轟隆聲響,令一般人頭痛欲裂;長時間的工作,常常讓人精神難以集中,工廠的領班甚至經常用皮帶來抽打工人,迫使其保持專注,以免因為工人的疏忽,而造成棉紗的瑕疵。枯燥的工作環境下,有一部紡紗機上卻擺了一本書 —— 無視於環境的困難,李文斯敦在這種情況下卻還能利用時間來閱讀。
「嘿!你!在幹什麼?給我拿出來!」有一次工廠的領班發現,李文斯敦似乎自顧自地看著什麼東西出了神,因而對著他大吼。「對…… 對不起…… 先生…… 」李文斯敦帶著驚慌的神情,顫抖地將手中的書交給了工廠領班。工廠領班見到眼前這個孩子手中的不是玩具,而是一本聖經跟一本拉丁文著作,先是大吃了一驚,但隨之而來的就是愛憐與惋惜湧上心頭,於是便領著李文斯敦進到較為安靜的領班辦公室。
「孩子,是誰送給你這樣一本精美的聖經的?」工廠領班以溫和的語氣問道。
「先生,這是我在詩篇背誦比賽贏得的獎品。」李文斯敦道。
「喔…… 既然這樣,你就證明給我看吧!」領班半信半疑,有意要試試眼前這個枯瘦的孩子,心想倒要聽聽看他可以背出聖經中的哪個篇章。
李文斯敦深呼吸一口氣,帶著穩定的節奏,不疾不徐,一個字一個字地背誦出自己所喜愛的章節,這也是讓李文斯敦在聖經背誦比賽中大放異彩的篇章。「天啊!詩篇第119首!」也難怪領班先生會如此驚訝,第119首裡,可是包含了176節,一共2300多字!
「夠了,孩子!我沒辦法聽這麼久!你叫什麼名字?」
「先生,我的名字是李文斯敦……。
李文斯敦此時堅定、自信的眼神,深深打動了工廠領班,領班不禁自忖,眼前的這個孩子日後必然大有可為。這一天,工廠領班特別讓小李文斯敦可以提早下班,去準備晚上的拉丁文課程;而從此以後,得到工廠領班的默許,李文斯敦再也不需躲躲藏藏,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工作時同時準備自己的課業了。
驢子與郵票
李文斯敦會把學校的課本打開,插在紡紗起重機的架子上,每當他經過這個起重機,他就會緊抓這片刻的時間,湊到課本旁,閱讀幾段書本上的文章。就在紡紗機不斷的吵雜聲中,他一點一點地建立了自己的學問基礎,同時也沒有在工作上懈怠。同事們都打趣地以「驢子」來稱呼他,藉以形容他對於學業、工作方面皆認真又執著的固執與韌性。
除了工作和學業上的好表現以外,李文斯敦更是個孝順的孩子。有一天,結束了漫長的工作以及下班後的課程,李文斯敦回家時,一如往常已是滿天星斗,家人也都睡了。此時李文斯敦卻發現自己忘了帶鑰匙,但是貼心的他並沒有在門外大聲敲門,而是選擇坐在家門口的台階渡過漫漫長夜。直至隔天一大早,母親發現兒子一夜未歸,帶著擔心與焦急走到門口,一開門,才發現兒子竟睡倒在玄關,寒冷的天氣讓他在自己的破外套中蜷曲成一團。
孝順、貼心、堅毅還不足以形容李文斯敦,他在學校也是以守規矩、品行優良而出名的好學生,而與同學間的相處,也頗受好評。他的同學稱他為「郵票」,因為他總是言出必行,受人之託或是許下的承諾從不違背,就像一張郵票一樣的可靠。
不屈於貧困的自尊
李文斯敦在布蘭泰爾紡紗廠工作了十三年之久。半工半讀,再加上小學與中學都是唸夜校,李文斯敦直到二十三歲才完成高中學業。在世俗的眼光中,比一般人晚了四、五年才從高中畢業,是貧窮帶來的不幸,李文斯敦卻曾如此寫道:
貧窮是給孩子的良好訓練,雖然訓練的過程會有點嚴峻。如同給一頭尚未成熟的犢牛背負一個耕田的軛,剛開始犢牛會深感吃力,舉步維艱,但隨著一天一天的努力與適應,沉重的負擔反而使這頭犢牛,在長大之後變得比一般的成牛更為壯碩與堅毅,可以拉動更重的車,走上更遠的路。而且,貧窮使我對受苦的人有一種深切的同情與關懷。如果人生能夠重來,我想我還是會選擇這種卑微的起步。
志業的開端
二十歲時的他正式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參加了由教會執事所組成的「海外佈道會」關懷小組,並且將自己辛苦存攢下的積蓄,全數捐給這個團體。有一天,他偶然間讀到馬太・亨利(Matthew Henry)的傳記,這位著名的宗教家與解 經家一生為基督教的貢獻與對後世的影響,讓他深受感動,年輕的心熱血沸騰,於是便立下心願,日後要成為一位為基督教奉獻的傳教士。
後來他與一位從中國佈道歸來的傳教士深談後,讓他要到海外傳福音的志願更為堅定。他說:「主為我捨命,我願終身致力於主的工作,以表達我對主的感謝。」從此,向全人類宣揚福音的志向,在他心中根深蒂固,從未動搖。
家人的支持與鼓勵
為了實現夢想,他加入了漢彌爾頓獨立教會,該教會會員資格的申請與認可非常嚴格,而且還需要由教會中資深的會員實際引領、考核長達五個月之久。
除此之外他也繼續深造,前往蘇格蘭格拉斯哥的安德森大學進修醫科,為海外的醫療傳教做準備。安德森大學一個學期的學費與生活開支,是十二英鎊,而李文斯敦當時在紡織廠工作的月薪僅有一英磅,即使他一整年不吃不喝,所存下來的錢也只夠他在安德森大學進修一個學期。然而當他將前往格拉斯哥的想法告訴家人時,全家不但沒有反對,而且還大力地幫助李文斯敦,因為他的家人知道,這個每天汗流浹背工作十四個小時,下班後卻還苦讀到需要人家將書本由手中抽走,才肯上床睡覺的孩子,一定不會讓他們失望的。
如願以償到安德森進修的他,在自己的隨筆中寫道:「多令人愉悅啊!十三年來,我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剩下的念書時間只有幾小時;而現在我清醒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拿來學習,這真是天堂啊!
因緣際會
1839年,甫自醫科學院畢業的大衛‧李文斯敦,寫信向位在倫敦的傳道會提出到中國當醫療傳教士的申請。倫敦傳道會核准了他的申請,也要求他在接受派遣之前,先在大學裡修讀一些進階的神學課程。然而就在李文斯敦修業的期間,在中國卻爆發了著名的鴉片戰爭。
一心要到中國傳教的大衛・李文斯敦,他的行程便如此地被戰亂所阻。就在引頸期盼的同時,他有機會與一位自非洲返國的老傳教士長談,也因此瞭解了非洲的宣教狀況。老傳教士凝視著李文斯敦,緩緩說道:「在晨光熹微中,我向 北方遼闊的平原望去,千村萬戶,炊煙裊裊,卻見不到傳教士的足跡。老傳教士悵惘又略帶失落的語氣,讓李文斯敦聽完後心中大受感動,深知非洲更是一個亟需他投入傳教工作的地方。
1840年11月16日黃昏,他回到布蘭泰爾的家中向父母道別,當晚三人促膝長談,直至東方破曉。清晨用過早餐,家人一齊閱讀詩篇135篇和121篇,並跪下禱告,奔流不止的淚水中混雜的是難捨的親情。李文斯敦的父親陪他步行至格拉斯哥搭乘前往英格蘭的蒸汽船,準備動身前往遙遠未知的非洲大陸。自此之後,李文斯敦與父母終身沒有再見過面。
步行三千哩
前往非洲佈道的大衛・李文斯敦醫生,像一位苦行僧,步行深入非洲三千哩,為實現心中的理想抱負吃盡苦頭。他不止醫治當地土著身體上的病痛,也救贖了他們內在的靈魂。廣大的非洲散佈著為數眾多的部落,部落與部落間的語言又各不相同,因此,李文斯敦必須非常努力地學習各個區域所使用的語言。要使用這些語言來傳教佈道,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每當求好心切的李文斯敦對土著們講道時,總是比 手畫腳、汗流浹背,叫人看了都為他的殷勤與認真感到佩服。
有一位非洲酋長,也在李文斯敦的引領下,接受了耶穌的懷抱。有一天,這位酋長看到他講道得十分吃力與辛苦,於是便對他說道:「以講道的方法,來叫人民信耶穌要等到什麼時候呢?我卻能叫他們馬上相信。若你同意,我可以召集整個部落的人民,只要我揮動我的皮鞭,他們馬上全都會歸信主。」
李文斯敦微笑著告訴酋長:「傳道的真正目的,不是要人們表面上做主的臣民,是要叫人從心裡受到主的感召,得到主的救贖。」
身經百戰
他不只是位傳教士,也是醫生、探險家、改革家。在傳教的漫長旅途中,他研究非洲當地的毒蟲、植物、鳥獸,各種可吃與有毒的果子,也對讓當地人飽受折磨的各種傳染疾病做了鉅細靡遺的研究。他到了非洲最黑暗的蠻荒之地,發現許多非洲不為人知的湖泊、河流,每有所獲,都寄回倫敦大學作為研究資源。他更竭力遏止當地販賣黑奴的勾當,改革當地由來已久的陋習。
在非洲大陸積極奉獻、醫療傳道的生涯中,他也歷經了無數的危機與考驗。他被好戰的土著攻擊過,被凶猛的大猩猩包圍過,被黑奴販子追殺過;多少次渡過湍流,爬過險坡,也曾在叢林中染上瘧疾、在沙漠中口渴難當,手臂上更留下了被獅子咬傷的一排齒痕。他經過了許許多多的危險和磨難,但卻沒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阻擋他把神的祝福,散播到非洲的土地上。
在非洲工作的頭四年,他一人獨自工作。結婚後,他與妻子瑪莉二人同心協力養育了五個孩子,但後來他們的女兒伊莉莎白卻在一次又一次的遷徙中夭折了。要在非洲這樣險惡的環境中來養育一個家庭,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了讓孩子能在安全、穩定的環境下成長,李文斯敦只得忍痛將家人留在蘇格蘭,隻身前往非洲。這次的分離整整有四年半之久。李文斯敦說,這是他一生最困難的決定。
犧牲的權利
1857年,在一場劍橋大學的演講中,李文斯敦向在座的學生,娓娓道出他多年來為主的恩典奉獻、努力,這一切生活之下的心境與感想:
「在我看來,我的喜樂因神交付我的差使而從未休止。人們談及我在非洲所做的工作,總覺得我犧牲很大;但當這差使帶來了健康的活動、蒙福的成果、行善的機會、平安的心境以及從神而來的一切喜樂與盼望,這些還算是犧牲嗎?我要強調,這不是什麼犧牲!倒不如說這是權利吧!雖然不時要面對憂慮、疾病、受苦或危險,甚至諸多的攻擊、家庭的責任等等,這些困境可能使我們停頓,使我們的靈魂動搖、意志消沉,就讓這些意念只醞釀一瞬間即消失吧!因為這一切,都不足以與那向我們顯現的主的榮耀相比,所以我從未作過任何犧牲 ……。」
黑奴的救星
當時的非洲,由於尚未開化,能發展的產業相當有限,很多當地的人民,常常被人口販子欺騙,成為失去自由的奴隸,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黑奴的悲慘遭遇時有所聞。李文斯敦本來對這些傳言有所保留,認為它們也許言過其實了,直到他親眼目睹這些慘絕人寰的悲劇,他才了解,這些人民所遭遇的不幸,是無法三言兩語就道盡的。
有一次他乘坐蒸汽船前往非洲的內陸,他親眼看到,沿途的河面上竟然漂浮著無數令人怵目驚心的屍體!每當隔天要開船時,船家都得清理推進器上的螺旋槳,因為上面黏滿了遇害者的屍肉,讓推進器無法轉動。
而有一個繁榮安詳的村莊,在他初次到訪後的十八個月再度造訪時,竟然已血流成河,成為了一座死城。從行動不便的老人,到襁褓中的嬰兒,所有的村民竟是無一倖存。從罹難者驚恐的表情,以及散落一地的事物來看,這個原本平靜的小村莊,遭受了突如其來的血洗。這等殘酷的人間煉獄,使李文斯敦痛心疾首,他難過地說:「從來沒有看過人類的生命如此地被毀滅糟蹋。」
當時的奴隸販子抓到土著後,就用長枷鎖將他們串成一列,跋山涉水地走上千百里路到海岸,送上船運到奴隸市場去販售。沿途如果有人體力不支,就當場射殺,將屍體隨意扔在路旁。這些可憐的人們,在途中還得負責扛著奴隸販子的行李;有的女人一手抱著她的孩子,一手拿著行李,當體力無法負荷時,奴隸販子甚至會殺掉她手中的小孩,讓女人空出手拿他們的行李。
當李文斯敦遇到這樣的隊伍時,都會極力說服奴隸販子釋放黑奴。李文斯敦也向葡萄牙官方積極遊說,因此取得葡萄牙國王的同情和支助。國王交代當地葡萄牙官員軍警,幫李文斯的宣教事業,所以李文斯敦手中有一道葡萄牙國王的「聖旨」,而販奴者大都不敢違背。李文斯敦在非洲受當地土著的愛戴,也是因為他在拯救奴隸方面的盡心盡力以及貢獻良多。
李文斯敦生於貧窮,長於貧窮,他深知生活困窘之苦,由此而生了他的知足感恩之心,也因此對這些奴隸的遭遇感同身受,為他們奔走挑戰販奴利益,贏得他們的尊敬。
令人不禁追隨的典範
1871年,紐約時報曾派遣一位記者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iey)前往非洲尋找李文斯敦。他在交通不便的非洲蠻荒尋覓了好一陣子,終於找到了李文斯敦;和他所想像的人物不同,他所見到的是一個枯瘦、一臉滄桑、長滿鬍鬚,年屆壯年卻已掉了牙齒的傳教士。斯坦利與李文斯敦一見如故,成為摯友。在李文斯敦過世後,斯坦利在隨筆中回憶兩人相處的時光:
我與他如影隨形,共同生活了四個月又四天之久,我無法挑出他的一丁點毛病。在前往非洲前,我對宗教頗有成見,可以說是整個倫敦最難接受信仰的一個人。像我這樣的記者,只管戰爭、國會、和政治事件等等,關於內心的情感,我向來漠不關心。
但在非洲,我遠離塵世間的俗務,有很多時間可以思考生命的意義,我看到這位孤獨的老人,便不免捫心自問:「你為何留在這裡?是什麼樣的力量激發你來到這片不毛之地?」相處幾個月後,我發現自己的心在聆聽李文斯敦,我非常驚訝這位傳教士已實踐「撇下所有來跟隨我」這句話,雖然他從未說服我歸信主,但是,貼身觀察到他的虔誠、他的仁慈、誠懇與安靜的工作態度,我也漸漸被他感化了。
與世長辭
李文斯於敦斯坦利離開後一年過世。1873年5月1日早晨,他的非洲僕人發現他親愛和藹的主人跪在小床旁過世了。當地人們感佩他為非洲所做的一切,將他的心葬在大樹底下,與這片他奉獻青春的土地合而為一。
他的遺體,則由人專程護送,不辭辛勞地經由內陸運往三千公里外的海岸,遠渡重洋,最後運回英國。英國人在西敏寺大教堂以國葬來彰顯他的偉大,出席追悼會的有來自全國的貴族與名流。英國人紀念他,迎接他,世人也深信李文斯敦在天上,也將追隨主的左右,蒙受主的恩典。
1874年,當李文斯敦逝世週年後,南丁格爾說:「我們這一個世紀,最偉大的人走了。在李文斯敦的身上,醫療已不只是技術,不是兌換福音的工具,而是他生命的流露。」坦桑尼亞也有一個智者曾說:「他(李文斯敦)有三個妻子:一個是條河,名叫尼羅河;一個是反對奴隸制度;一個是宗教。」
李文斯敦語錄
◎ 我寧願為求在神旨意中而住在非洲之內,卻不願意坐在英國的皇位上而在神旨意之外。
◎ 父母教導我四點,使我一生受用。第一是勤勞的美德,勤勞是除了必要的休息之外,不浪費時間在無意義的事情上;第二是節儉的生活,節儉是對物質需用的節制,以最少的需求去面對每天該盡的責任;第三是讀書的習慣,使我一生在不斷的學習中進步;第四是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是上帝塑造人性格的鋼骨。
◎ 我的一生,除了解救人的靈魂之外,沒有第二個選擇,我將全力朝此目標,裝備自己。
◎ 我並不看重我所擁有的,或者我可能會擁有的一切事物;我看重的是我和基督國度的關係。如果有什麼東西可以擴展國度的益處,只有在榮耀祂的前提之下,予以保留或給出。祂是我目前和永遠盼望的對象。
◎「我的耶穌,我的王,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我再次將我整個生命奉獻給你。接納我的奉獻,使用我,使我在今年能完成我的使命。」—— 李文斯敦五十九歲隨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