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打坐時,首先會面對的問題就是妄念的干擾。這些念頭,有的比較有組織性,有的則較散漫,都會直接干擾我們用功。但實際上並不是妄念在干擾我們,而是自己覺得它煩,才變成干擾。
想趕走妄念的念頭,也是妄念
在日常生活時,有些妄念可能會讓我們產生歡喜的心。比如在想所愛染的人或事,便不覺得妄念是干擾。如果想的都是不喜歡的呢?這時便會起瞋心,也就覺得它是干擾了。但是有時起瞋心,發覺某種程度上可以讓自己發洩一下。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能對這個人無可奈何,這時可以在心理上對付他,就不覺得這些是煩惱,反而紓解了一些壓力,或取得某種平衡。這樣看來,妄念好像也有一點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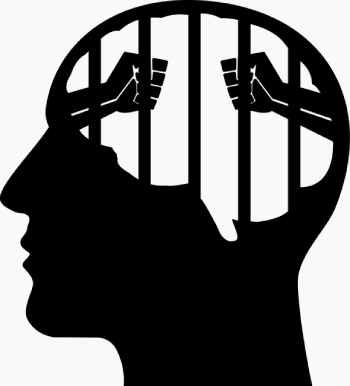
平時妄念很多,我們常隨順它,讓它繼續流轉,有時還加一點力量去推動它;習慣了以後,就不覺得它煩。
可是為什麼打坐時,會覺得妄念都很煩人?那是因為我們想要攝心於方法上,卻被妄念拉走,才發覺這些妄念的干擾。
如果注意到這些妄念的話,會發現其實它們反映的都是我們的生活,也就是我們所想的一些事,包括我們的習氣。在生起這些記憶時,我們不是後悔做錯了決定,便是執著我們做得對的決定。所以在回憶中,我們會有兩種情緒:一種是感到非常歡喜,因為都是甜蜜的回憶。另一種則是不斷地懊惱,後悔那時做的錯誤決定,然後就會做許多假設:假如我這樣、那樣,這件事就不會這麼糟了。但是那些假設永遠不會發生,因為當時的因緣已經過去了,我們不可能再回到以前。不斷地假設,就會愈來愈煩。
妄念現前時,一定要面對它,因為我們無法加以阻止。比如念頭生起來了,攝不住心時,不妨讓心稍微放鬆一下,看看念頭,會發覺它只不過是我們生活中的某些情況出現,或是心裡經常思考、轉動的一些念頭。這樣看了以後,雖然知道這些念頭的力量很強、會把方法拉走,我們還是不要去理它們,盡量把心拉回到方法上。因為想趕走妄念的念頭也是妄念,這是瞋心,這些都是在打坐用功時,一般比較粗顯的現象,這種情況會慢慢地過去。當工夫用上時,就只是專注在方法上,讓方法一層一層地進去,心也一層一層地進去。但是,即使工夫用得很好,這些妄念從來沒有離阿姨8過我們,只是粗的妄念會暫時放下,比較細的妄念會出現。
工夫一層一層地進去時,妄念也一層一層地陪著我們。有時在某個階段,工夫會用不上,就是因為那個層次的妄念已經起了作用。所以打坐時,發覺有很粗的妄念浮現時,不要去應對它,也不要趕走它,只是守住方法,慢慢地那組妄念就會消失或變得比較模糊不清。當守到某個階段,心調得比較好、工夫調得比較細時,又會有一些妄念很清楚地現出來。
如果細心去觀察前後的妄念,會發覺它們的情況不一樣:先出現的妄念很粗;較後出現的妄念,或工夫調得比較好時出現的妄念則比較細。然後,它會一層一層地進去,每一層的妄念都可能會拉走我們的心,因為當覺察到妄念出現時,就很有可能被它拉走。同樣地,當覺察到妄念要拉走心時,就再把它拉回來,繼續守住方法。
我們先從數息法開始用功,當數的工夫非常穩了,就把數目字放下,這即是證數了。剛開始修數時,數目字常常會被拉走,等到證數時就不會了,因為這時心是緊緊地 貼著數目字。一旦發覺數目字愈來愈粗,就放下它修隨。在修隨時,妄念可能會拉走用功的心,就回到數。那些妄念從清楚到模糊,慢慢地感覺好像不存在了。實際上它還在運作,只不過因為心調得比較細,對這些粗的妄念,我們的反應比較小或可以不去反應它。把這個基礎的工夫穩定了以後,再進入隨;隨了一段時間,工夫很穩了,就安住;證隨之後,再修止。
正確的心態與知見

開始修止時,往往不知道所謂「止在一點」是在哪裡?或者知道,心卻很空虛,想要攀一些緣或一個境。
因為隨息雖然比較細了,不過還有呼吸讓我們去專注。但是止的時候,這些都沒有了,甚至有時期觸覺也沒有,只是一種意相。這時心裡會感到很空虛、很空洞,而想要捉一些東西。之後覺察到呼吸,又退回去隨息;隨了一段時間,又會進入止。或有時一些念頭轉粗時,可能就掉回數息;數了以後會再隨,隨了以後又會再進入止。到證止時,心就可以安住在方法上,知道有妄念,但不會受妄念所干擾。這 是屬於欲界的定境。
假如能夠一直保持這個工夫,不必刻意用力,守住那個境,漸漸地就可以進入比較深細的定。但是過程中,妄念還是一直跟著我們,只不過方法用得愈深,心住得愈細,會出現的妄念往往都是我們心裡潛伏著的,或是比較深細的煩惱。如果打坐時,覺察到妄念是最近發生的事情,就表示這些妄念還很粗,工夫也很粗。當工夫很穩時,就會與善法相應;反之,就很容易被妄念拉走。如此上上下下,慢慢地用方法,用到終於能夠把自己的心安住在一個境上時,即是修止。
止了以後,就可以修觀,或進入比較深細的定境。有些人修行,可能是想從定中得到感應或神通。也即是說,能夠入定的話,心的力量會加強。不過,那時若沒有智慧的引導,這些力量可能反而會左右了我們。因為力量強了以後,若自己內在的道德或知見不夠,將無法控制這種強而有力的作用,最後便會被它牽引而去。這好比我們手上有武器,假如沒有正確的道德來指導,這項武器就會變成造業的工具了。所以修定之前,若沒有正見引導,就會出現這種問題。
但有時不只是知見的問題,往往是心態出了問題。我常常提醒大家,打坐時要一心一意地用功,因為工夫用得好的話,便能夠得到禪定,再依禪定作觀而啟發智慧。這些見解大家都有,可是坐下去時,心就不是這樣想了。所以有些人打坐會愈坐愈偏,是因為微細的心理未能緊緊地依正見做調和;其中,最容易阻礙我們用功的心態便是慢心。一旦有慢心,種種問題就會跟著來了。比如打坐時,要和別人比較。別人坐得好,就會自卑;別人坐得不好,就想表現自己的工夫。如果這時工夫用得好,慢心就會愈來愈強,如果輸給別人,妒嫉心便會生起來;妒嫉心生起,就會想用「門面工夫」來裝飾自己,有一點點動作就弄得很大,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有修行。或是旁邊的人坐得很好,就設法干擾他,讓他坐不好。我們不要以為每個人用功時,心念都很善良,一旦妒嫉心生起,什麼花招都會出來的。
妄念本來就是在反映我們現實生活的狀況。生活中的一些習氣,會熏入我們的心裡,成為妄念。如果會因為別人勝過自己而做出一些反應的話,在打坐時也會的。這些心態都很微細,一不小心讓它得逞,後果就嚴重了。那時已忘記應該要調整自己的心態來用功,因為慢心、妒嫉心或自卑的念頭太強,覆蓋了所有的善念,所以工夫用不上,也不能夠進步。愈無法進步,就愈不甘心別人坐得那麼好;愈是這樣,就愈往另一個方向去了。
以上情況,是還沒有進入定的工夫;如果進入定,力量會更大,就更危險了。一個禪七打下來,不僅什麽工夫都沒有用上去,還把自己弄得很慘。這種很微細的心態出現時,如果不調整它,不只無法精進,而且會愈來愈往後退。因此,我們真的要很細心地注意自己的妄念。
修行要往内修,不是向外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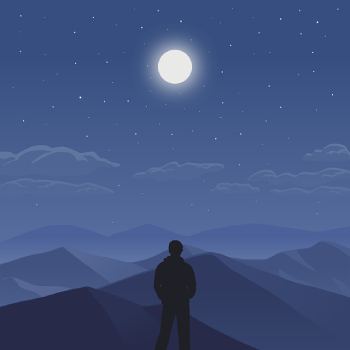
不過,也有人慢心生起時,會使他更用功,這通常是意志比較堅定的人。
你坐兩支香,他撐三支香給你看,即使腿已經痛到身體冒冷汗,非放不可了,還是硬撐,就是要表現自己比較有工夫。那是不是在用功呢?佛教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因為慢心,造了許多業。他故意主張禁止佛陀在修行方法裡面沒有禁止的事,比如不能吃魚、吃鹽之類的苦行,來吸引依佛陀出家未久而對佛法還不了解的弟子,把他們拉出僧團而成立自己的僧團。他還挑撥頻婆娑羅王的王子搶父王的王位,當上新王,自己就因此成了新佛。提婆達多還是佛陀的堂兄弟、阿難的哥哥,也是釋迦族,而且樣貌非常好,佛陀三十二相、他三十相,但是妒嫉心、慢心一生起,便使他造了這些業。
我們可以想想:提婆達多的工夫不好嗎?沒有知見嗎?據說他可以背誦佛陀所講的道理幾十萬頌,但是修行出了問題,煩惱沒有斷。我們都會有這些問題,所以修行時要很注意自己的心態。有時只是一個很微細的作用閃過,就會把我們拉到另一個方向去;尤其是慢心,一定要設法調整。
慢是根本煩惱的一種,樣樣都要跟別人爭的人,在用功時就要注意自己的心理,這種心態一定要調整。要告訴自己,修行是個人的事,不能和別人比較,修行也沒有第一名、第二名的。世間的某些利益也許可以用爭取或不合理的方法得到,但是修行絕對不能。修行是要將自己的整個心打開來看的,愈真誠地對待自己的心,就愈能夠把工夫用好;愈是加一些東西進去,就愈無法用功。因為修行是要往内修,不是向外追求的。如果打坐時發現我們有這種心態,就要不斷地提醒自己把它調整過來;調整之後,知見就會發揮它的功能,將我們帶到正確的方向和目標去。所以不要因為煩惱和妄念的出現而覺得煩躁,從中我們才能夠真正看到自己的問題。
妄念其實是在傳達很多重要的訊息給我們,只是看我們怎樣去吸收它、接受它、明白它?所以不要怕妄念,面對它,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些問題,包括不正確的心態;一旦看清楚了,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就設法去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