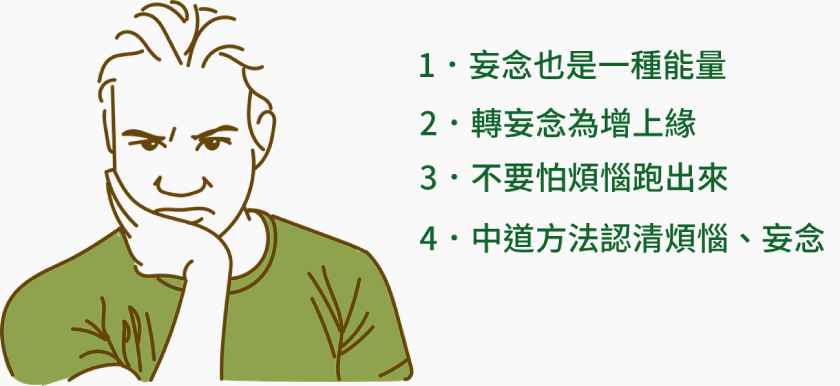
有些人會覺得不能參加禪七,或在家裡用功的時間、空間受到限制,是外來的因緣干擾。實際上最大的干擾不是來自外在,而是我們的心。如果我們的心不會因煩惱而形成障礙的話,在任何情況下,還是有辦法用功的。因此,問題一定是出在我們的煩惱和妄念;尤其用功到某個階段時,深細的煩惱和妄念所造成的障礙可能會更大,必須把它看清楚。
妄念也是一種能量
一般上修行者對煩惱的態度,都會抱持最好不碰或知道它的態度。因此,有些修行者在生活中出現一些惡行時,往往不敢正面地去看問題到底是如何發生,而想用善法,比如布施等善事去掩蓋。也有一些人在行善時,其實夾雜著煩惱,卻又不願意去面對。他們在布施時,可能心裡是想得到回報或獲取一些名聞,出出風頭。如果這些念頭不是很強烈,只是心裡的妄念,便不會造成什麼干擾。但是長久下來,這些妄念會變成業和報,形成流轉的力量。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常常看到很多行善的人,得到的果報裡總是夾雜一些不善的因緣。即使他得到善報,也還是不斷地在流轉之中。

很多人在禪七修行時也是這樣,一味地追求境界,得到一點好的覺受,就以為自己用功得力了。
其實心裡明明充滿著妄念,卻不願意面對它;甚至在談這些問題時,都盡量避談自己的煩惱。有時小參也不願意談它,或只是略略帶過,認為這樣就沒有問題了。但是煩惱還在心裡,這會形成修行的障礙。
在用功時,會有很多不正確的心態浮現,我們常常繞道避開它們。但是繞來繞去,還是在原地繞,跑不出去。如果不把它們挖出來看清楚,就解決不了它們。這是我們其中一種對妄念、煩惱的態度,就是避而不談,或當作沒有這一回事。另外一種心態,是把煩惱誇大。比如某件事做不到,就認為自己業障很重;想修行時,家人障礙,也認為是業障重。其實有時不是外在的業障重,而是自己心裡障礙重,這不是業障,是煩惱障。業會形成障,但是如果不把它當作障的話,它就不是障。所以業障不一定是指不好的,其實有很多人是在逆緣中修行的,這時的惡報反而不成為障,而變成增上緣。
而對一些人來說,善報可能反而變成障礙。為什麼?例如在家裡生活太舒適,一想到打禪七要挨腿痛就不敢參加了。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善的環境中如果不懂得珍惜,就變成是障礙了── 障住了上進的心。很多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很好的修學佛法因緣,卻把它變成障礙。我們要了解,不管是煩惱或善念,都是心理的一種作用,也是一種能量 ── 煩惱是負面的能量,善念是正面的能量。佛法講「煩惱即是菩提」,就是把負面的能量轉化為正面的能量。
現代所謂的EQ,就是情緒智商。情緒是每個人都會有的,只是我們常常讓它變成負面的能量,導致有時候不能把生活處理好。如果我們能夠在情緒波動時看清楚它,將負面的能量轉化為正面的能量,它就能發揮功能。比如碰到有人罵我們,不要逃避生氣。為什麼?因為有生氣這種情緒,表示自己還是正常的人。被人家罵了還不會生氣,這大概有幾種情況:一是聖人,二是傻瓜,三是死人。我們是凡夫、正常的人,被罵時,情緒一定會顯現出來的。如果用負面的能量去對抗對方的話,可能會造成彼此間的對立。但是,若能讓對方知道我們生氣,或讓他知道自己在生氣,那就有辦法轉化了。
做媽媽的有時也會碰到類似的情況,罵了孩子,孩子對你說:「媽媽,您生氣了!」這時你就氣不下去了,為什麼?因為孩子把你的情緒告訴了你,他就是在幫助你轉化。你聽了就會想:「為什麼自己會生氣?是為孩子好,還是想要發洩情緒?」返觀一下,就有辦法去調和。如果生氣時告訴自己:「生氣,生氣,生氣;放下,放下,放 下。」覺照自己的煩惱,是會有作用的。這正如聽到聲音時,不要去分別是什麼聲音,只是「知道,知道,知道;放下,放下,放下」,回到方法上,那個聲音就不會干擾自己了。
煩惱與妄念一直跟我們一起流轉,不可能避開它們。但是,它們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可怕。很多人把煩惱講得很可怕,認為貪、瞋、癡三毒會把慧命毒死了。其實若能 將它們轉化成另一種情況,比如無貪、無瞋、無癡,就變成菩提了,這即是善心所法。
貪、瞋、癡等煩惱都會在妄念中出現,如果不懂得如何處理的話,可以暫時放下,不要理它,這是修止的方法。但這些妄念還是在繼續流轉,我們只是放下一些比較粗的妄念。這好比說,假如我們每天能夠放鬆自己的身心,讓白天一些比較粗重的妄念疏通掉,它們便不會累積。如果每天都能夠把當天所面對的種種壓力、問題,通過打坐或其他方法先清理掉一部分的話,就不會把它們帶到睡眠中,也就不會累積成第二天的毒素,心就比較清淨,空間也會比較大。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在不斷地累積問題,從小妄念到很粗的妄念。這個根,若讓它一直往下深入,一旦攀住了心,要清理就麻煩了。用「止」的方法,就是先把粗的部分清理掉,比較細的部分就要用觀想的方法來斷除它。
轉妄念為增上緣

在禪七用功過程中,當心調得比較細時,會看到細的煩惱。它雖然細,卻很有力量,
因為黏得比較深、攀得比較緊。所以有時一些比較粗的妄念過了之後,深細的妄念就會出現。它的干擾力量滿強的,即使不理它,繼續用功,它仍不時會跑出來,我們只是暫時避開它,並沒有真正把這個動力斷掉。這時該怎麼辦?繼續打坐,盡量回到方法上,慢慢地就能比較放得下了。但這些都是攀得比較深的妄念,而我們只是清理它的枝葉,樹幹可能也弄掉一點,可是根還在,過一段時間它又會現前,繼續干擾。因此,必須用觀想的方法,以智慧從根去斷除,這就需要長期用功才行。
我們在觀想時,要以佛法為依據。當妄念出現時,可以用佛法中的無常、無我去剖析它,不過這需要很大的工夫;或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妄念,即將妄念視為正常的事,把它看清楚了之後,就可以去轉化它,使它不會變成煩惱而轉為增上緣。這好比說,我們知道生活在這個世間不能離開眾人,但是愛染會讓我們不能解脫,就把這種愛提昇,轉化成慈悲,以慈悲心來對待人,而不是執著它。例如我們很愛父母,那就將那些年紀跟父母相同的長輩都看作是自己的父母,便會轉化成一種正面的能量。慈悲的心是與樂拔苦,愛他們就是希望他們快樂,沒有煩惱。那麼,就會通過行動去表示,於是就變成一種力量,也就不會染著。不過,要先把自己的妄念看清楚之後,才有辦法做到。
這種轉化的作用,中國禪宗的禪師就發揮了很多,這些禪師的個性都相當明顯的,是他們長期累積的習氣形成。他們不一定把這些習氣滅掉,反而轉成度化眾生的作用,因為某些習氣適合某一類眾生的根性。其實習氣也沒有所謂好或不好,只是我們長期養成的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如果和煩惱相應,就變成不好;如果和智慧相應,就可以應用度化眾生。
所謂「物以類聚」,業習相近的眾生,也會同類相聚。佛陀在世時,有一次說法結束之後,剛出家的弟子就圍著他們心目中的「偶像」—— 大弟子們,請教法義。喜歡苦行的會找迦葉尊者,喜歡議論的會找迦旃延,喜歡智慧的便找舍利弗。
佛陀是開放的覺者,所以後期部派佛教的出現,是正常現象。如果我們仔細想想,其實早在佛世就有部派了,真正民主的社會就是這樣。佛陀對這些現象並沒有感到煩惱,怕這些弟子以後會分裂。而這些大弟子都有各自的特長,這些特長就是由他們的個性所轉化的一種優點。因此,中國禪宗後期出現了好幾個宗派,每個宗派都有它的特色,比如「德山棒」、「臨濟喝」。
不要怕煩惱跑出來

看清楚自己的妄念之後,能轉化的轉化,須清理、斷除的就清理、斷除。這個過程是滿長遠的路,
如果不認真看待這些妄念,它們真的會障礙修行。其實只要我們真正很用心,應該是有能力去應對,不會完全束手無策的,只是有時是自己不太願意好好地去看它們。在用功的過程中,能漸漸懂得處理自己的問題,才是進步。所以不要怕煩惱跑出來,而要去觀察它,再運用一些知見或方法來調整它。
那些一打坐就會出現的妄念,清理的方法是不理它,只要守住方法,直到它脫落就好。因為這些都是很粗顯的煩惱,是意識很表層的作用,只要放下,不理它就可以了;等進入比較深細的煩惱,才須細心地觀察它。如果法義掌握得準確、清楚,可以直接用空或無我的道理來觀,也就是觀一切法或這些現象的本性,直透進去,然後把它切掉,那是最理想的。如果還沒有這個能力也沒關係,就只是看著它。
煩惱反映我們的生活、個性及心中種種的現象,一定都和自己有關係的。即使想到的是別人的事,最後會發現主角一定是自己。因為這些煩惱都是自己惹出來的,所以一定會回到自己身上,不會是別人的事。
有時我們打坐,會坐到有點像進入夢境一樣,忘失了身心。當妄念出現時,剛開始有一部分是生活中所沒有經驗過的,但是最後會發現主角是自己。做夢時也是如此,不管夢境怎麼轉,主角一定是自己,因為自己就是製造夢的人。有時又會坐到進入一種類似昏沉又不完全是昏沉的狀況,這是心比較專注了,但是對身體失去某種覺照作用。那時如果妄念的力量比較強,就會把我們的覺照作用拉過去,整個心隨著它轉。當引磬響時,才發現自己在禪堂,好像做了一場夢。這只是心比較沉,不是真正的昏沉。真正的昏沉是進入到昏昧狀態,整個心沉下去,然後打瞌睡,那時會有夢,但被引磬聲驚醒時會感到很累。
這兩者雖有類同、都是失去覺照,但後者是身體處在疲倦狀況,失去執持身體的作用而進入睡眠狀態,然後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了。即使「掉」了一個頭而驚醒,又會繼續「掉」。有時工夫是用到了,可是心沉下去而沒有覺照作用,還有妄念在。如果連妄念都覺察不到,那就要小心,因為再這樣下去會陷入無記,進入深定就變成無想定了。
在打坐用功時,若有這種類似做夢的狀況出現,其實就是比較深細的妄念,或是潛伏在內心的一些過往的經驗。如果在驚醒過來之後還有記憶的話,不妨審察、回憶一下發生的過程,可能我們在這一生或在有記憶的範圍內,曾經發生過夢境中的事。但也可能這個妄念過了之後,我們只是淺淺地留下一些印象,不是很深。直到某天發生了一些事情,感覺好像很熟悉,但就是想不起什麼時候發生過?其實就是曾在我們的妄念影像裡出現過。
中道方法認清煩惱、妄念

當前五根停止作用時,意識的作用往內攝,很多潛伏著的影像就會現前。
以唯識學來講,便是第八識(阿賴耶識)含藏著的種子會現出來。常常在那個時候,第八識才能和第六識(意識)溝通。溝通時,因為經過第七識(末那識),所以所有影像的主角都一定是自己,這就是我執的作用。也就是經過第七識之後,所有的作用都變成是「我」了。因此,不管那個夢境或是見到的境界怎麼轉,主要人物一定是自己。
若含藏在第八識的一些種子業報快要現行時,第六識能夠和它溝通,它的影像就會現在第六識裡面。第六識有了這個影像,就有了印象,因此會在打坐時或是夢中出現。這是因為做夢時,前五根的作用完全停止了。打坐坐得很好時,當身根的作用脫落,也可以達到這種情況。心專注時,第八識的種子就會現出來,第六識會感應或吸收到這個訊息,所以也許過幾天後,當那件種子業報現前的事情發生了,會覺得很熟悉,好像曾經發生過。可是回到現實的情況,用比較粗的意識(可以覺察的意識)去回想那件事,卻會發覺好像在印象中沒有發生過。
這些潛伏著的東西顯現出來,對我們是有幫助的,不出來的話,自己什麼都不知道。當我們一層一層地進去,會發現每一層的妄念都在傳達一些訊息給我們,每一層的煩惱也都在告訴我們一些事。
如果某種惡業造了很多,當這一期生命快要結束時,這類惡業可能就會把我們推往惡道去。比如那些從事屠宰業、殺業很重的人,往往臨命終時惡報會現前,看到自己要投生的那一道之相。這也就是表示他第八識的種子,包括第六識所造的業已經現出來了。這個是引業,本來是不會改變的,招感到人身就是人身,到這一期生命終結了之後才會改變。但是,那種惡業卻重到引業還沒有改變時,它的相已經現出來了。
每次打坐妄念現前時,可以看看自己哪些妄念比較多?從妄念中,我們能真正認識自己的煩惱,因為它是我們心理的作用。很多人一講到煩惱,常誇大成無藥可救了,其實並沒有那麼嚴重。有時候是我們把它講得太過嚴重,才造成很重的罪惡感。罪惡感太重的話,就會使心提不起來,無法用功;或工夫稍微用不上時,就認為是業障。從一個比較正面的角度來看,妄念反映了我們的生活。比如造作了身口的業之後,它會回熏内心,反熏意業,又變成意業裡所含藏的種子,或是含藏的一種習氣;再運轉時,就會看到它。
如果自主的力量,也就是能觀的作用加強了,可以提起理論或是法來觀想時,不妨故意提起一些會讓自己起煩惱的往事來想,試試看自己觀的作用是否有用上工夫?這時若心調得很好、很穩,那些煩惱念頭一生起就滅。為什麼?因為太粗了。你的心住得那麼細,粗的煩惱根本就貼不上去。
如果打坐時有很粗的煩惱,心很容易被拉走,表示工夫還沒有調好。不過沒有關係,不要煩躁,愈煩躁就愈用不上工夫。只要提醒自己不斷地回到方法上,調和自己的心,把專注、覺照的作用盡量凝聚在方法上,便能克服問題。你不用去對付它,只要能夠把心調細,妄念就會沉下去了。如果能夠做到一層一層的煩惱現前都不理它,心就能調得愈細。這是比較偏向止。然後,因為覺照的作用還有力量,你可以觀察妄念,剖析它,再用方法把它解開,慢慢地煩惱會被切斷,流轉的動力也就終止。
打坐用功時,煩惱、妄念一定會現前,是避不開的。因此,應以正確的態度去看妄念,不要太過或不及,太過、不及都不是中道。用中道的方法認清自己的煩惱、妄念,能夠轉化的轉化,不能轉化的便放下;最後,應該斷的就斷掉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