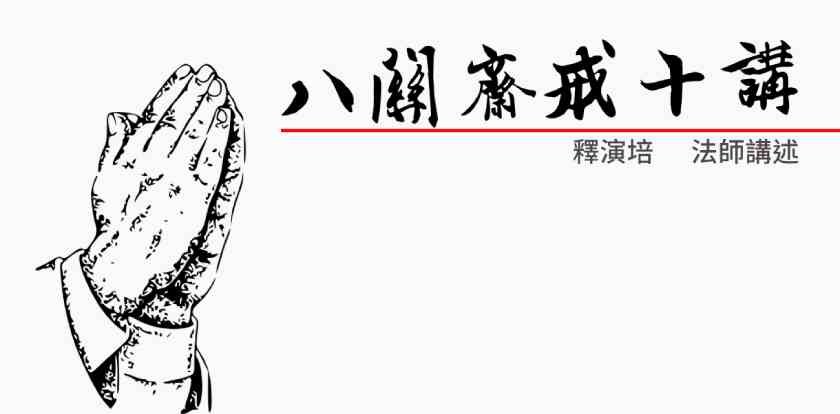
爲佛弟子所受的戒,大多有一定的數目,如在家衆的五戒,出家沙彌的十戒等。而今諸位所受的八關齋戒,從名稱聽起來,很顯然的是八支戒,似沒有什麼可說的,但從各經論所列的數目看,不能不說有着相當的出入。不唯如此,就是戒條的層次,同樣有着此前彼後的差別。再深一層的探究,還可發現開合互異,有的經中開這條戒合那條戒,有的經中開那條戒合這條戒,以致不免使人對八關齋戒的看法,感到有點凌亂。
表面儘管有着這麼多的差異,但從它們的體義推究起來,仍可發現它們的一致性,既沒有增多什麼,又沒有減少什麼,還是我們所要說的八關齋戒,問題就看我們怎樣處理其間的差異。〈毘婆沙論〉對這有很好的交代說:「由此近住具有八支;而於五增三,於十減一:合二爲一故,開一爲二故」。這是以八戒與五戒、十戒對比,說明八戒的所以成爲八戒,不過是在五戒以外加上三戒,或在十戒減去一戒而成。可見八戒與五戒、十戒有着相通性,不是與五戒、十戒完全無關的八戒,嚴格的說,離了五戒、十戒的戒條,就沒有所謂八戒。
論中所謂於五增三,意即顯示八戒不是指的另外什麼東西,那不過是在五戒之上再加三戒,就成爲八戒。所增的三戒,論中曾這樣清楚的告訴我們:以「不塗飾香鬘舞歌觀聽」,爲八戒中的第六戒;以「不眠坐高廣嚴床座」,爲八戒中的第七戒;以「不非時食」,爲八戒中的第八戒。像這樣的序說八戒的次第,明顯的是將「塗飾香鬘」與「舞歌觀聽」兩者合爲一戒來說。且這所增的三戒,實際就是沙彌十戒中的後四戒,因合六七二戒爲一,所以成爲八戒。對比沙彌十戒來看,近住律儀所缺的,只是「不捉持生像金銀寶物」的一戒。
論中所謂於十減一,意即顯示在家二衆所受的八戒,對比沙彌所受的十戒,只要減去最後的一戒即可。當知十戒之所以得名爲十戒,不過是將「不塗飾香鬘」與「舞歌觀聽」分開來,亦即論中所說的「開一爲二」,加上「不捉持生像金銀寶物」,就成爲沙彌十戒。以五塵說:舞歌觀聽,明顯的是指色聲二塵;塗佈香鬘,明顯的是指香觸二塵。對這四塵有所染著,不是易於散亂掉舉,就是易於憍奢放逸,都與修道不相應的。所以,不論已過出家的生活,或是學習出家的生活,不得不遠離這些,假定對這仍然不能忘懷,那是難以安於出家生活的。
色聲香觸的四塵,既都是障道因緣,塗飾香鬘與歌舞觀聽,爲什麼這樣的開合不定?〈婆沙論〉中對此有所交待說:「同於莊嚴處轉,故合立一支」。這兒所說的莊嚴,就是一般所說的打扮。世間所有人們,不論是男是女,不論東西各地,愛美可說是人的天性,到了相當的年齡,不要別人的教導,自然就會刻意的莊嚴自己,不但衣着方面極爲考究,就是嚴飾之具亦極認眞,穿著佩戴打扮得花枝招展不算,同時還要以各種香水、胭脂粉、塗指油、唇膏等搽在身上,以增進自己的艷麗,好讓路人爲之側目。由於各地的風俗不同,所用的莊嚴具當然有別。
一般以爲這是莊嚴,或通俗的說是漂亮,殊不知這正是罪惡的根源,世間無比的罪惡,都由此而產生的。佛陀深知這個過患非輕,不但規定出家衆要著壞色衣,就是在家二衆的修齋入寺,亦須著潔淨樸素的衣服,絕對不可著華麗的衫裙,至於現在士女所著的奇裝異服,更爲佛陀所不許可,還有什麼無上裝,迷你裙之類太過暴露的衣著,最好不要穿入修道的地方,以免影響行者的清修。胭脂花粉香水的嚴身,佛不但不讓出家者用它,就是發心學習過出家生活的信士女,亦禁止以之嚴麗自身,因這同樣是觸犯戒法的有力外緣。
歌舞觀聽,屬於眼見耳聞的色聲二塵境界。如舞蹈,是眼所見的,若歌唱,是耳所聽的。過去比較保守的歌舞,佛已禁止出家衆的觀聽,何況現在更大膽的技舞與靡靡之音的流行歌曲?當更不是佛法行者所當觀聽的。因爲這些耳目之娛,看來似乎沒有什麼,但如經常的與之接近,不但會荒廢我們的道業,而且會增進我們的欲念,使我們所有的素志,不能安住於佛法上,久而久之爲其所轉,離開佛法更爲遙遠,甚而至於使你墮落下去,沉湎於歌舞而無以自拔!所以不論已出家者或學習出家者,自己固不得歌舞倡伎,亦不得故意的到歌樓舞榭觀聽這些!
不知是時代的進步,還是僧人的思想前進,現在竟也有些出家衆,在衆目睽睽下,昂首濶步的,無所忌諱的,出入於電影院中,或大馬戲團之内,以爲這是增長見聞,無礙於個人的清修。殊不知這是故往觀聽的一種遁詞,與所應遵守的戒律絕對不相符合。因爲這些地方,畢竟是娛樂的場所,而且是庸俗不堪的娛樂,現在稍有社會道德觀念的,都認爲這是不健康的,含有戕害青年的毒素,所以佛法行者,不論提出什麼理由,爲自己的行動辯護,是都說不過去的。如諸位在此學習過出家的生活而受行八戒,外界即使有怎樣歌舞之類的玩意,都不去看是對的!
八戒的戒相,不唯塗飾香鬘與歌舞觀聽,有着或開或合的不同,亦有將歌舞觀聽與高廣大床合爲一支的,如四分律羯磨與八戒正範,就是如此而說的。經律中儘管有如是衆多的差別說明,而受八關齋戒的行者,應嚴格的遵守佛所規定的這些戒條,可說仍是無有二致。不過在說戒相時,有時將這說在這條戒中,有時將這說在那條戒中,不知者以爲有所出入,其實都是告訴我們做不得的,只要受行戒法的人,不去做這做那就行,至於應該遵守的,合併在那一條中,並不是個重要的問題。所以吾人只應重視戒律的精神,不必太過注視條文的開遮!
在此進一步要向諸位說的,就是關於高廣大床的問題。吾人終日忙個不停,到了晚上必要休息,始能恢復一日疲勞,否則的話,我們這個危脆身體,絕對是支持不下去!夜晚的睡眠休息,目的在消除疲勞,只要能够安枕,睡得甜甜就好,至於作爲臥睡的床座,似不必太過高大考究,如像俗人那樣的講究床座,豐棉厚的柔軟舒適,反而使你顛倒夢想,不能入於甜蜜夢鄉,失去睡眠本來的意義!佛陀深知這對身體健康有着很大的影響,所以特別制了「不坐高廣大床」的一戒,好讓行者於睡臥中,亦以正道爲念,不致空過光陰!
高廣大床不可用,然則佛所制的床,又是怎樣?「佛制床座,高不過如來八指(如來全身丈六,指濶二寸),合周尺一尺六寸;廣如來三肘(如來肘長一尺八寸),合周尺五尺四寸」。《阿含經》中對這明顯的說道:『足長尺六非高,濶四尺非廣,長八尺非大。』。合乎這個尺寸的,就是守持如來的禁戒,超過這個尺寸的,於如來戒就有所違犯!出家佛子的生活,總是以簡單爲向,決不可太過奢侈,才能與聖道相應,所以佛世時比丘,有的在樹下過宿,有的在塚間安眠,根本不以床座的是否舒適爲念。諸位在此臥處的簡陋,就是本於這一律制的旨意!
臥床的高低大小,不唯是就量的方面講,就是在質的方面說,亦有得而分別的。如古代中印兩國富有的人家,對於所臥的床座,非常講究其精緻,除了予以漆彩雕刻,還要飾以金銀牙角,至於床上的用具,諸如帳被墊褥等,更都是絹紗細軟的,可謂曲盡華麗之能事!如是,量的方面,雖然沒有超過佛所制定的,但因質的方面太過高貴華麗,亦不是佛子所應受用的。如果受用這些珍貴的東西,不但對此逸樂有所躭着,忘記了自己所應修的聖道,而且還會增長自己的高傲憍慢,所以佛不容許佛子如此享受。諸位現在來學習過出家的生活,對這首應有所習慣!
最後要和諸位一談的,就是關於「不非時食」的一戒。不非時食,有人認爲是八戒中最重要的一戒,其實八戒無一不重要的,不可於中分別,誰是最重要的,誰是次重要的。不過以出家佛子說,應嚴格的過「過午不食」的生活,不僅佛世時的僧團極爲重視,就是現在南傳佛教國家的比丘,亦仍大體的如法守持這條戒,設有比丘過午受用飲食,非特僧團所不許可,就是信衆亦難諒解。可是這戒在中國,一向未受到重視,別說出家人不持午,不會受到社會的批評,就是有僧發心持午,亦往往爲人勸說而開。中國僧人未能嚴持這戒,可說全是 環境之所使然!
飲食本是維持生命生存的主要動力,不論任何高級低級的生命,如果沒有飲食的受用,絕對不能長期生存下去的,所以佛在經中說「一切衆生皆依食住」。而從現實世間去觀察,亦從沒有發現有那個人,不賴飲食而生存的。世間所以發生種種問題,就是一般說的生存問題。生存必須生活,生活雖是多方面的,而食則尤爲其中最極重要者。所以世間的人,對於飲食總是要求精益求精,並且希望餐餐受用都很豐富。正因每個人的要求是如此,一旦求而不能得的時候,各種不正當的行爲,就會一一表現出來,以致形成社會的嚴重問題,甚至發生强有力的鬪爭!
我們雖然學佛,但仍是世間的人,就不得不有賴於飲食的維持生存,以期假借這個色身修學佛道。飲食的目的既是在於資身爲道,只要能够維持生命的生存,只要這個色身能够支撑下去,就算達到我們受用飲食的目的,大可不必在好壞上有所分別和選擇,更不得像俗人那樣的養成非肉食不飽的習慣。關於這,佛在《遺教經》中對出家比丘有很好的指示說:「汝等比丘,受諸飲食,當如服藥,於好於惡,勿生增減,趣得資身,以除飢渴;如蜂採花,但取其味,不損色香;比丘亦爾:受人供養,趣自除惱,無得多求,壞其善心。譬如智者,籌量牛力所堪多少,不令過分以竭其力」。在佛法看,飲食是治療飢渴之病的一種良藥,不管是好是壞,受用飲食以後,只要不感飢餓之苦就行,絕對不可如在家人那樣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終日爲食而忙,更不得見到好的就多吃一點,見到不合口胃的就少吃一點,以致忘記了自己所修的聖道。佛制比丘托鉢以乞自活,信衆供養什麼就吃什麼,那裏還容你選擇好壞?可是佛法傳到中國來,由於托鉢制的未能實行,僧尼在變相的寺廟家庭中,自飲自食,自不免在好壞方面有所選擇,甚至在各寺廟中,以齋菜做得好傲視於人,終日把時間花費在厨房裏,離開佛法當然更遠!
關於飲食,佛不特規定比丘不得在好壞方面講究,而且制定不非時食一戒,着令出家僧衆嚴格遵守。所謂不非時食,是說在規定的時間內受用飲食,當然不成問題,如果在規定的時間外受用飲食,那就有所違犯。什麼時候是比丘受用飲食之時?《毘羅三昧經》有說:「早起諸天食,日中三世諸佛食,日西畜生食,日暮鬼神食。如來欲斷六趣因令入道中,故制令同三世佛食」。這無異告訴我們,比丘只可同佛一樣的日中一食,其他都不是受用飲食之時。經中雖這麼說,但一般解釋時食與非時食:認爲早上明相出一直到日當中午,是爲食的時候;太陽影子過了日中一髮一線,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明相未出,都是非食之時。所以一般把這說爲持午,或是說爲過午不食。飲食爲人生的大欲,沒有那類衆生,會像人類這麼愛好飲食,佛爲什麼對出家衆的飲食這樣嚴格限制?要知飲食一事,看來好像是無關重要的,亦是每日所不可缺少的,但它關係我們的道業很大。俗語有說:「飽暖思淫欲」,可見飲食爲男女大欲的增上緣。佛在律中對於飲食所以多所限制,最大而又最主要的一個目的,亦可說是爲了對治人生所存的第一大欲。而這大欲是障解脫的大敵,追求解脫的佛法行者,能不予以有效的對治?而對治的最勝方便則是減輕食欲。
不非時食這條戒,不唯比丘應守持,而是出家五衆所應共同守持的,就是你們受持八關齋戒的在家衆,佛亦制定要守這條戒,可見此戒在佛教制度中的重要性。說來非常慚愧,諸位受八關戒,如以律制規定,應在終身不非時食者的師僧面前受,可是像這樣的師憎,在今日佛教中,是不可多得的,很多發心過午不食的僧衆,都是時開時持的,很難把握畢生的不非時食。以我自己來說,就未能够做到,所以雖爲諸位傳授八關齋戒,但在我的內心確是感到極大慚愧!不過爲諸位傳授後,諸位在這一日夜中,能如法的守持清淨,未嘗不是一大佳事!
八戒支數的辨別,主要是辨別後三支的開合,至於前五戒,與近事律儀是一樣的,平時講得很多,所以未去談它。後三支既有開合及層次的差別,於辨別清楚之餘,特順便的將後三支略爲解釋,讓諸位對於八戒,有個完整的認識。不過還要向諸位鄭重交代一句的,就是五戒中的不邪淫戒,在八戒中應改爲不淫戒,因爲出家律儀,定要完全斷除淫欲。諸位受八關齋戒,既是暫時學習出家生活,理當受行諸佛盡壽不淫之戒。如不能盡斷淫欲,不特出家生活,難以過得下去,就是解脫之道,亦無法踏得上,所謂了生死,自更不可能,這是我們不得不特別注意的。
從支數的辨別,可知諸位所受的近住律儀,剛好不多不少的是八支,既不可增爲九支,
又不可減爲七支。但爲什麼唯是八支?俱舍論中告訴我們:最初的四種戒支,是屬於性罪,爲防性罪的產生,所以不得不制這四支。第五飲酒戒,是屬放逸門,爲了防護失念而妄造四種性罪,所以不得不制飲酒支。最後的三戒,是爲防護憍逸的現前,所以佛制這禁約的三支。因此,頌文簡約的說:「戒、不逸、禁支,四、一、三如次,爲防諸性罪,失念及橋逸」。不但〈俱舍論〉是這樣的講,〈成實論〉也這樣的說:「是中、四是實惡,飲酒是衆惡門,餘三是放逸因緣。是人離五種惡是福因緣,離餘三是道因緣。白衣多善法劣弱,但能起道因緣,故以此八法成就乘」。八戒中的後三戒,能够捨離染緣,不爲外界的塵境所轉,所以能爲正道作殊勝因緣,三乘聖道的基礎,亦可說是完全建築於此。因而發心受八關齋戒者,對這不可有絲毫的輕忽!爲什麼?坦白的告訴諸位:最後的三支,看來很平常,但如輕忽它,不嚴格受持,出世三乘聖道,就沒有你的分,怎能不予重視?總說一句,八戒雖是在俗清信士、女所受,但成佛亦緣於八戒而來。如經說:「今我得佛道,本從是八戒起」。八戒關係修學聖道如是重大,我望諸位多多發心受行八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