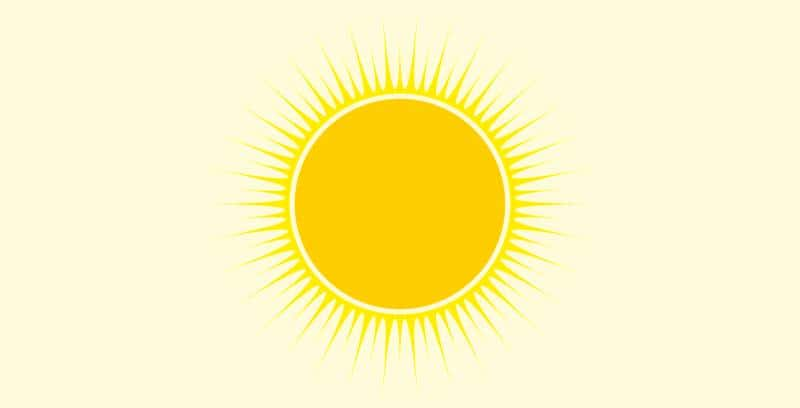
在成功嶺的時候,週末休假日,
阿兵哥們都到台中跑跑玩玩。有一
次,我坐車子無意間瞥見台中蓮社
的招牌,以後心裡就老想著這個地
方,我想我這次一定要學成,不能
再這樣拉拉扯扯了,往後每逢假日,
別人往附近的名勝區遊覽,我則跑
台中蓮社學佛。
頭一次到台中蓮社,在外面就碰到了有名的李炳南居士,我每請教他問題,他都叫我念南無阿彌陀佛,除了念南無阿彌陀佛以外不談別的,什麼禪宗、打坐,他都閉口不談,光教你念佛。不僅李炳南,包括蓮社裡的蓮友都跟你說:「別的不必看了,你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好,談其他的都是廢話。」當時,我對念南無阿彌陀佛沒什麼概念,也不知道有個西方極樂世界可以往生的事,禪宗在中國人的心裡有一定的份量,一般人的觀念裡都看重禪宗,以為佛學就是禪學,我也是先入為主的觀念,因此,叫我念南無阿彌陀佛,我就不知怎麼個念法。
回來以後,我也試著念念看,我一百一百地念,念到七、八百句便感覺口乾舌躁,極不舒服,提不起興趣再念下去,有時去蓮社共修,大家坐在一起念,也是沒辦法適應,念沒幾百句就坐不下去了,長時間下來,自然對念佛興趣缺缺。況且我原先對禪宗比較有興趣,老想學盤腿、參禪,我不能說念佛不是佛法,但我念得口乾舌躁,我聽他們宣傳要常常念南無阿彌陀佛,可是我念不下去,感覺跟這個法門不相契。因為不相契,所以也不想皈依,人做什麼事都要心誠,不是表面上敷衍敷衍,不能因為李炳南是我同鄉,就聽他的話皈依,皈依做什麼?跟著他們念南無阿彌陀佛,我可不幹!因為心裡沒信仰,後來我就光在門外看看,跟著拜拜佛、搬搬桌子而已。
十三週教育結束,部隊移防到日月潭附近,之後再到集集,也是一樣沒有學佛的門路。因為我夢到白公雞,知道會死在外面,所以一直想出家,但始終沒機緣遇到一個出家人,李炳南雖然是佛教中有名的居士,我也拖拖拉拉地親近了好幾年,但沒什麼成就,轉來轉去,找不到善的因緣。
民國四十六年,我們一個連在台中的新社鄉凡社林看守砲彈。有一天,吃過飯後沒事,我跟連長一起出去散散步,走出兩、三華里,有一座土地廟,大約像現在的寺務處這般大,我們隨興地走進去瞧瞧,看到一個三 十幾歲的年輕人正在那兒打坐。我想,打坐跟學佛有關,心裡盤算著等他起來,要請教他打坐是怎麼一回事,便逗留在土地廟裡和連長隨意聊聊。等那個青年打坐完,我即近前請教他一些打坐的問題,那青年都對答如流,而且他不僅懂得打坐,其他中國老的禪宗也都懂,了解的範圍相當廣,連台北的出家人怎麼樣都很清楚,我所能想到的問題,他都能解決,你問什麼,他談什麼,談得呱呱叫,我對他所說的內容都很感興趣,不像李炳南除了念佛之外不談別的。跟他談過話以後,我便想皈依了。
我問他皈依怎麼個皈依法?他對這個很熟悉,馬上為我詳細解說,怎樣拜師、怎樣皈依都介紹得很清楚。那時台中的靈山寺正在傳三壇大戒,智光老和尚、南亭老和尚、懺雲法師等人都在那裡傳戒,也附帶舉辦在家的皈戒,他介紹我到靈山寺皈依,我依著他的指導,請 南老做我的尊證師,正式皈依成為三寶弟子。
從民國四十三年每個星期跑台中蓮社,但對感興趣,到處亂闖,轉來轉去,一直到四十六年,才在土地廟碰到他,正式走上學佛的路,因緣是這麼奇特,時候到了,自自然然地就成了!那個青年是我學佛的轉捩點,我只記得他姓張,好像是廣東人,國、台語都會說,是空軍退役的,結過婚。前幾年我當當家的時候,他還與人結伴來過這裡,我也曾去信感謝他,但是後來我一心忙常住的事,竟然把他的名字給忘掉了。他與我是一段極善的因緣,其他在家人的話我都沒有那麼信,對他就是不一樣,他一說,我就信了,不是他,我到現在還不一定怎麼樣呢!他指導我很多,對我很有恩德,他說什麼,我就做什麼。
後來他叫我吃素,他說得斬釘截鐵:「學佛的人不能不吃素。」佛陀教我們吃素是為了長養慈悲心,但在部隊裡要吃素可沒有那麼方便,現在是因為吃素的風氣比較普遍,吃素的人可以另外開一桌,還有的一貫道去當兵,都自己煮素菜來吃,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要吃素,可是在行動上都表現得很堅定。過去吃素的人少,尤其我是連指導員,我不能自己做素菜,如果叫廚房特別幫我做,等會兒士兵來報告說:「指導員,你的素菜做好了!」那我在部隊上怎麼指導人?我就問他:「我在軍中怎麼吃素?」他答得很簡單:「可以吃肉邊菜。」我想想還是有些困難,也沒敢馬上答應他。回到部隊裡,我一直想這個問題,當時我還沒皈依,也沒有打定主意吃素,可是,很奇怪地,到了吃飯的時間,要下筷子了,碰到肉,就自然不願意動了,我想我是學佛的人,而且準備皈依了,心理作用,自然而然不願意夾肉了。從此我了解到,主要是心的問題,學佛是自己心裡想要學佛,心轉變了自然就成了。
皈依後,部隊即開往谷關做山地訓練。我由自動吃素的問題聯想到戒菸的問題,過去我在學校教書和在普訓中隊的時候,也和同事約好一起戒菸,前一、二天還好,到了第三、第四天以後就耐不住了,晚上一個人在辦公室裡無聊,踱來踱去,看見地上的菸屁股,忍不住彎下腰把它撿起來吸,戒了幾次都沒戒成。皈依以後,覺得學佛的人不應該吸菸,部隊裡發的菸,中興牌的我全給了其他士兵,只留下一包克難牌的,克難牌在當時是最好的菸,我捨不得給人,心想慢慢地戒,偶而還可以抽一支。可是當我抽完一支,再吃第二支的時候,就感覺抽菸沒什麼意思,不願意再抽了,捨不得給人的克難牌最後還是通通送人了,這是自動戒菸,心改變了,沒什麼戒不成的,自動戒菸才是功德無量。
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時,我到了台北,在松山靶場附近的松山寺認識了道安法師和當時尚未出家的傳忠法師。認識道安法師後,我想出家的心愈益迫切,那時我調營政工官,在部隊的辦公桌上供了一尊彌勒菩薩像,常常給菩薩上香,我當時對佛教的規矩都不懂,還把一串念珠掛在脖子上,營指導員與我同住一間房子,看了我的舉動,認為我學佛入迷,腦筋有問題,因此而有了不良的記錄,後來可能因為這樣的因素把我調了部屬軍官,調了部屬軍官等於宣告我可以退役了,我正高興著的想不到過沒多久,可能看我還能做點事,又把我調到第 二軍團。到了民國五十二年秋天才正式退役,我就這樣告別了十幾年的軍旅生涯。
退伍以後,我到松山寺親近道安法師,並且接編《獅子吼月刊》,可是出家因緣未具足,大約十個月後,我又辭去《獅刊》的編務,到花蓮師專特師科接受輔導會的師資訓練,預備畢業後教書。讀了一年以後,聽說師大也要招生,我們想考考看,便積極準備應考。老師看我們住了一年,捨不得我們離去,耍鬼不發佈招生的消息,等我們知道時已經錯過考期了,大家心裡都非常不平。
有一天,教育組長來上《論語》課,憑良心說,他的《論語》講得很不錯,我很喜歡聽他的課,可是這天他一上台,二話不說,就指責我們這件事情如何如何不對等等。我也要把是非曲直搞清楚,憤然站起來說:「我們今天非講個明白不可!」他說他有理,我說我有理,弄到最後誰也不讓誰,全班四、五十位同學攔著我,不讓我再講下去,但我還是非跟他辯論到底不可,到最後他氣得離開了教室。
鬧了這件事情以後,我也不想再待在學校了,我因為上學期眼睛有毛病,看書時常發乾、發澀,會有小黑點在眼前飛來飛去,找一家小診所檢查,看診的是一個女醫師,她說我得的是飛蚊症,很嚴重,要多注意、多休息,不然眼睛會瞎掉。因為我不想留在花蓮,於是請醫師幫我開了一張證明,不讀書了。我覺得在社會上勾心鬥角沒什麼前途,又老是做夢夢到下雨,覺得人生一片黑暗,實在走不下去了,便積極託人幫我介紹道場,不管那裡都好,反正我無論如何要出家就對了。
民國五十四年秋天,性梵法師介紹我到土城承天禪寺出家,我一聽到土城這個名字就不歡喜,土裡土氣的,使我想起澎湖,好像飛沙走石一般。起先我不喜歡來,可是人家介紹了,不得不來,再靜下來考慮考慮,好的地方他們不歡迎我們退伍軍人,人家歡迎的地方去不了,反正我就是要出家,不如去看看再說。
那天,法振法師、我和劉國香夫婦四個人一起來到了土城,下了車,街道破破爛爛的,我心裡更加生不出好感。我們沿路走,到了大墓公那兒,看到一條山路往上蜿蜒,咦!是要到山上去的!我略微振奮了一下,我最喜歡山水了,在澎湖當了三、四年的兵,想看山都看不到,現在往山上走了,我的心為之明朗開闊起來,愈往上走景觀愈佳,我也愈加歡喜。
循著小徑,一腳高一腳低,慢慢地爬上了承天禪寺,這時的承天禪寺是幾椽低矮的房子,茅棚、紅磚瓦房錯落在一起,在叢山環繞間顯得寧靜樸厚。剛經過齋堂便碰到傳忠法師 —— 我們以前在松山寺就認識了,他已經來承天禪寺出家,做了當家。他知道我要出家,很歡喜地引導我去拜見老人(廣欽老和尚)。傳忠法師和老人談話,講的都是我們聽不懂的方言,我們只好在旁邊坐著,我看著山色,心意慢慢地轉變,開始喜歡起這裡來。但看得出老人不太歡迎我,傳忠法師費了好大的勁才跟老人溝通好,回轉過來跟我說:「可以來了!」我得到承諾後即下山積極打點一切。
過年前,我搬著行李正式來常住,當時老人正坐在舊三聖殿門口跟信徒說話,說完看著我跟他頂禮,半句話也沒講,立即起身走入方丈室去了,表現出極度不喜歡的態度,我有點尷尬,可是想想行李都搬來了,也已經頂禮過他了,不能不留下來,我也很勉強地按捺自己住下來。我信步走到矮牆邊向遠方眺望,景色十分秀麗,當我轉頭向椰子樹那邊望去時,竟然看到樓台殿閣的境界,十年後開始承天禪寺的重建工程,我才體會出這個境界的含意。
人與人之間都是一種因緣,我到這裡出家也是因緣,老人不喜歡我,可是我偏偏轉來轉去就轉到這裡,老人不識字,而我喜歡讀書,我聽不懂他說的話,和他談不來,卻來這裡做了他的徒弟。當時我想,既然因緣轉在這裡,就隨順因緣住下來吧!過去讀書雖然沒讀出什麼文憑,但起碼讀過四書,憑這點基礎,我可以自己看看藏經,傳統的修學佛法就是看經嘛!書報雜誌上也都叫人看經,所以我單純地認為出家看經就好了。在《獅刊》擔任編輯時,道老曾叫我請了一套大正藏,於是我把藏經搬到山上,利用工作之餘研讀經典,就這樣在承天寺住下了。
當時有一個河北人想跟傳忠法師爭當家的位子,他脾氣大又喜歡唆使人,他要我幫他,我不願意,他便動手想把我打跑,我不與他爭,幾次他都得不上手,我也馬馬虎虎將就過去。以前男眾寮房(在現在三聖殿旁菜園)有個黑板,我們有時間就會在上面隨便寫寫東西,有一次他看到我寫的詩句,知道我讀過書,有點兒墨水,不跟普通退役軍人一樣,對我的態度才有改變。
隔年,也就是五十五年的臘月八日,早上老人也沒跟我提今天要幫我剃頭的事,因為已經住了一年,還沒有消息,我有點急了,下山到北投報恩小築找性梵法師,當時印順法師也住在那兒。我問性梵法師情況怎麼樣,到底何時可以出家?他也幫不上忙。沒辦法,我只好再 回承天寺來。才剛回來,傳忠法師喊我:「柳居士,你今天上哪裡去了?師父找你,大概是要剃頭的事。」結果當天給我下山一耽擱,時間已經太晚了,老人決定順延到臘月十五日再剃。
到了臘月十五日,我正式圓頂現出家相,法名普過,字號傳悔。五十六年農曆十月,我和傳奉法師、傳緣尼師以及另外兩個女眾,總共五個人到台中慈明寺受三壇大戒,當時的三師和尚 ——— 得戒和尚是印順導師,羯磨和尚是道安法師,教授和尚是演培法師。
我對戒律方面很有興趣,受過戒回來當維那,常住沒有誦戒,每逢初一、十五我就自己在大殿誦戒,因此知道自己有些不清淨的地方。有一天晚上我在佛前誦戒,抬頭仰望佛菩薩,突然血液往腦門上沖,我一下子就昏過去,經一段時間才清醒,可是無法再誦戒了,收了戒本,往山門外繞繞佛,又想到過去的一些事,心無法安定下來,索性再走回大殿,看著佛像,眼前居然下起紅色血雨,我以為是我的腦細胞出血了。後來每逢雙日課誦我都很擔心,八十八佛念到「南無普光佛」時,血就往上沖,下一念沒辦法控制,雖然不曾在課誦時昏倒,但心理壓力很大,很怕又發生失控的現象。這種自己無法自主的情形持續很久,從五十六年受戒以後,一直到五十九年左右都有這個業障出現。
出家以後,老人對我的態度即完全改變,有時他會做試驗,多方地磨鍊你。受戒回來沒多久,老人把我叫去,說要傳法給我,我愣住了,傳法?我從書本上看到的,傳法都是有開悟的人,我問:「您傳法給我做什麼?開悟沒開悟我自己知道。」老人說:「傳法有兩種人,一種是開悟的人,一種是能辦道場的人。」我聽了沒說什麼,可也沒答應,我當時覺得我還搞不清楚修行是怎麼一回事,你傳法給我有什麼用呢?老人跟我提了好幾次,最終我還是沒答應他。他又要我做當家,我怕擔這個責任,也因為當時我的重心擺在看經上面,白天做大殿香燈,到了休息的時間,我要把握來看點書,那時我對於常住的事都是應付應付,該做的做完了就沒事,總之是很被動地做,作息都是按照常住的規矩,該吃飯就吃飯,吃完了飯可以利用時間來看書,做當家事情比較多,會耽誤我看經,所以我就不肯答應。出家前,在部隊上雖然也喜歡看看書,但是心不一樣,加上身邊有幾個錢沒地方花,便喜歡往外頭跑跑,一有些頭痛、牙痛、身體發癢之類的小毛病,請假出去看醫生,順道去別的 地方跑跑玩玩是很正常的事。出家以後就不是這樣,我把時間看得很重要,不管在看經上或哪裡,我會覺得這是一件實在的事情,就算看書,也不偷懶,實實在在地在這上面用功夫。
老人都教人念南無阿彌陀佛,他也教我不要看書,要念南無阿彌陀佛,但是當時業障在,對於他的話沒辦法百分之百相信,佛號也念不下去,你別看念佛很簡單,只有六個字,但也要有多生多劫累積的善根才能安定地念下去,沒善根、為業所障,想念佛也念不了。佛念不下去,心不安定,便很容易動腦筋想到別的地方去看看,老人要我當當家,我回絕了,但我說:「我發願住在承天寺。」老人聽了不置可否,想想看,佛念不下去,不發心為常住,可能在承天寺待得下嗎?待不下的!我後來當了當家,不要命地發心做常住的事,才能在這裡住得這麼安定。
而當時心不安定,想離開承天寺找個地方專門看藏經,因緣便出現了—— 五十九年初,同是山東人的智諭法師來約我去五指山閱藏。之前智諭法師跟我說,道安法師要在五指山幫他剃頭,我同他開玩笑:「如果你去五指山出家,我陪你住。」後來他跟著道安法師在松山寺出了家,要去五指山閱藏便找上我來。我總不能說我以前是開玩笑的,現在不去了,於是答應他一同去五指山。但也很為難,當時承天寺的住眾不多,我不好說我要離開這裡,湊巧慈善寺的住持法師,住持不做了,來承天寺掛單,我藉口有人來住,趁這個因緣到五指山去了。
五指山位於竹東,海拔有一千多公尺,山上霧氣很重,常處在虛無飄渺之中,純木造的觀音禪寺正在五指的中指之下,正殿供奉觀世音菩薩。除了智諭法師和我以外,還有兩個外道共住,其中一個是青島人,都是同鄉,我們人少,一起開伙,白天就各自用功。道安法師曾經來看過我們,交給我們一萬塊的菜錢,當時智諭法師有事下山,道老是我的長輩,跟我也十分熟悉,我不好拒絕就收下了。住了沒多久,智諭法師慫恿我把大藏經請到山上,他認為大藏經搬了來,我就會安定地住在這裡,我聽了他的話,回承天寺把藏經都裝箱好,可是連續下好幾天的雨,沒辦法搬,我只得放棄,仍回五指山去。隔沒多久,反而是智諭法師不安定不想住就下山了。有一天,兩個外道都下山,整個五指山就剩我一人,到了下午二、三點,人都還沒回來,我開始害怕了,如果他們再不回來,晚上,這偏遠的千重山中就光我一個人,五指山以前曾經發生什麼鬼怪,我們也不知道,我可是個怕鬼的人!還好,傍晚時分,那個青島人回來了,讓我虛驚一場。
我在五指山前後共住了五個月,智諭法師離開了,我也不想待在這裡,便寫信去獅頭山給性梵法師,性梵法師在元光寺當住持,他答應我去住,我便收拾東西到獅頭山去,把這裡交給道老管理了,後來聽說五指山成了退休榮民帶髮修行的地方。
民國五十九年下半年,我到了獅頭山,因為沒有多餘的寮房,性梵法師便安排我住到後面的納骨塔上,骨塔的一樓放在家人的骨灰,二樓安奉出家人的骨灰,骨灰罐子並不多,另一邊是房間,裡頭很乾淨,我看了很喜歡,便住下來,兩個月後才搬去寮房。雖說是閱藏,但實際上還是做點事情,專門看經,除非在佛學院,否都在做事,你躲在房間看書,人家不歡迎你,所以我也隨緣做點事情,像敲敲法器之類的,做得不多,其他的時間就用來看經、拜經。
我對閱藏很感興趣,起初看經偏重在戒律方面,譬如說廣律,了解佛陀制戒的緣起,廣律的文字比較淺白,很容易懂,中國祖師寫的反而比較不容易看。我很用心在這上面,一邊看,一邊做筆記,看得很仔細,筆記也做得很詳盡,所以看的速度很慢,雖然看得不多,但是對於佛法的大意都能夠了解。
讀書的人多半都會想寫寫文章,這樣對於讀過的內容印象會比較深刻一點,我想大家都這樣,我不寫不好意思,否則好像自己看經沒拿出什麼成績。於是,我預計寫「聲聞乘中三大士」,介紹蓮花色比丘尼、摩訶男等人,他們是內秘菩薩行的大士,在當時以聲聞乘為主的原始佛教中,無異是閃閃發光的金砂,因此我想特別著墨一下,在獅頭山時,我完成了「蓮花色比丘尼乞食濟眾及其他」一文,並發表於《獅子吼月刊》上。另外,我又發心從律藏當中蒐集一些有關釋迦牟尼佛日常怎麼樣著衣、托缽乞食,怎樣在生活中行持的資料,準備寫一本釋迦牟尼佛傳,資料都蒐集得差不多了,可惜因緣不具足,沒有寫成。
有一次,性梵法師提起他的師父會性法師,以前住獅頭山拜《法華經》的事,我聽後很感興趣,也想拜拜看,性梵法師的一個蓮友知道了,歡喜發心請了一部供養我,總共七大冊,六萬多字,所以法華偈說「六萬餘言七軸裝」。這個版本的字很大,很適合拜經用,別人拜經用兩個銅錢在字上上下移動,以標示拜的位置,我找不到銅錢,用兩個銅板打洞權代,就這樣拜了起來。起初我不敢講我在拜經,怕拜不完讓人家笑話,後來拜得很順利,感覺也很舒服,愈拜愈有興趣,拜不完的問題也不成問題了。拜第一部經的時候,我沒閱藏,專門地拜經,依照拜經的儀軌做,拜得很仔細、很專注,一個字一拜,每天拜六百拜。有的人一天可以拜一千多拜,我最多只能拜到八百多拜,再多就不行,拜了一百天全部拜完。當時是春天,有點潮,外頭種了些花草,環境很幽雅,我索性搬到寮房的走道上睡,房間內就專門拜經。剛開始我不知道拜經會得到境界,整部經拜完之後,回到外間床舖上坐下來稍微休息一下,突然感覺身體很輕鬆,有相當清朗的境界出現,過了一會兒,我回憶起過去有些不清淨的事,那種清朗的感覺立即唰地一下消失於無形。
一部經拜下來,我對拜經產生濃厚的興趣,便接著拜第二部、第三部,但不是專門地拜了,我改晚上拜經,白天看書,因為我的眼睛有飛蚊症,夜間在燈光下看書不方便,利用來拜經剛剛好,我慢慢地拜,一年拜一部,每次拜完也都有清朗的境界出現,因有前次的經驗,我不再回想過去的事情,這種感覺便能持續二、三天的時間。
在獅頭山期間,我廣泛地試驗各種修學方法,譬如說試著洗冷水澡,可是洗沒幾天,腳開始痛起來,回承天寺洗洗熱水澡後才好,從此以後我不敢再洗冷水澡了。有段時間我也曾試著幾天不吃飯,結果搞得腿發腫,我腿腫的毛病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其實修行人不吃飯,腦力很集中,很安定,感覺很舒服,自己並沒怎麼痛苦,但是看在別人眼裡會感覺餓得很辛苦,像民國初年的弘 一大師有一陣子也實行過斷食,或是像美國萬佛聖城宣化法師那兒也實施日中一食,可是我的腿不能配合,可能我的因緣不適合這種修行方法吧!想想老人雖然光吃水果,甚至曾經幾個月未進食,但他也沒提倡不吃飯或光吃水果,我就沒有繼續在這方面下功夫了。
住在元光寺納骨塔的時候,碰到一次鬼,那天傍晚,我離開房間一下,回來時看到一個人坐在我桌前,正在翻我看的《大毘婆沙論》,我不便打擾他,先到別處繞繞,再回來時,他已經不見蹤跡了,這件事我也沒跟其他的人講,怕他們害怕,就當做一件特殊的回憶吧!
我到獅頭山基本上是善緣,去之前我做了一個夢,夢中我到了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前邊有個水池,我跳下去游泳,游了好一會兒,感覺水有點冷淒淒的,我便向對岸游去,爬上岸便醒過來了。我自己覺得這個夢很好,似乎象徵著到彼岸去,而在獅山蘭若四、五年間,拜《法華經》也算小有收穫。可惜因緣不久長,後來慧日講堂的當家普獻法師來獅頭山任住持,而原住持性梵法師則離開獅頭山,到慧日講堂當當家,普獻法師的學識很好,但我跟他不熟,我和性梵法師很早就認識了,他離開了,我的心也開始動搖,第四部《法華經》還沒拜完,我也跟著離開獅頭山了。
六十四年春天,我回承天寺住了一些時候,雖然沒有再拜《法華經》,但仍持續讀誦一段時間,也是有一點境界。
承天寺地處山坡,初期的磚瓦房多屬匆促建成,時日一久,地基陷落,牆壁龜裂,拆除重建是勢所必然,當時女眾傳喜師做當家,她開始重建的第一課 —— 改建舊三聖殿前下坡處的女眾寮房,即現在大殿下的女眾寮房。年底,後山開了一條馬路,接通運煤的便道,從此車輛可由山下直接開上來,水泥、砂石也都可以很方便地運上山,我和傳奉法師當小工,幫忙擔水泥、挑砂石灌水泥等,因為不是當家嘛,所以也沒有責任,只是幫忙性質,到晚上就休息,心也不很安定。這段期間,性梵法師曾約我一起去金山,我原先想去看看,但是做了個夢,夢見自己在爬樓梯,一直爬,一直爬,到了最頂端,上面卻是黑漆漆的一片,我直覺去金山不好,便沒答應他。
後來我動腦筋想到玄奘寺住住看,玄奘寺的住持是道安法師,當家是法振法師,道老除了玄奘寺以外,還是松山寺、善導寺的住持,因為法振法師很能幹又肯負責任,所以道老經常不在玄奘寺,把寺務完全交給法振法師處理。我如果要到玄奘寺掛單,必須先跟法振法師打交道,我聽說他回到台北,即到善導寺找他談,因緣很好,一進去便剛好碰上法振法師,我們是舊識,他當然是很歡迎我,談好了,我便找一天搬了過去。
玄奘寺位於日月潭畔,它的一樓供奉玄奘大師取經立像,二樓供觀世音菩薩,三樓安奉玄奘大師的頂骨舍利,我的寮房即在三樓。住沒多久,道老也來玄奘寺了,我和道老的因緣極善,我出家之前就曾在松山寺編輯《獅子吼》,親近道老,他什麼都懂,我一直把他當學佛的長輩、當師父看待,而道老也很喜歡我,十分照顧我。
我在玄奘寺領維那職。有一天,忽然夢見一樓的玄奘大師取經立像不見了,換成一個人坐在供桌上,我一看,咦!這不是道老嗎?我站在維那的位置,懷疑地左端詳、右端詳,看來看去確實是道老沒錯,可是道老怎麼會坐在玄奘大師的位置上呢?醒來後,我十分納悶,思維著,難道道老是玄奘大師再來?後來我寫了一詩:「昔為唐玄奘,民國釋道安。色身雖有異,靈性後即先。」做為我對這個夢境的詮釋。
其實我到了玄奘寺以後,即發現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我夢見回承天寺的路上一點一點的都是大便,表示來這裡是不對的,回去也不好,心裡便後悔了,可是事情已經如此,後悔也遲了。為什麼說我到日月潭是不對的?因為我每天都呈現東西南北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明明太陽從東邊出來,我偏偏看成從西邊出來,業障真是不講道理的。過去,我在海南島也有一次大轉向的經驗,中午煮飯的時間,我在一棵椰子樹下睡午覺,一覺醒來,方向就轉過來了。而這次一直持續一、二個月都轉不過來,我每天就看太陽從西邊出來,從東邊落下去,很不方便。我又夢見自己用插花的花器端著很大一盤的大便,直走上二樓,供在觀世音菩薩前面,這是非常不恭敬的行為,也是不好的象徵。我的心很不安定,搞到最後也真是住不下了,便下定決心回承天寺去。
回去的那天早上,我行李都綑紮好了,就等著車子來,我坐在三樓窗邊向外注意車子來了沒,卻看到一個人,不像來拜佛的,手上沒拿什麼東西,一直爬,爬上三樓,發現我在注意他,馬上掉頭走下去,我直覺反應他是個賊,於是大喊抓小偷,眾人聞聲跑出來抓小偷,他卻一溜煙跑得不知去向了。
等車的時間,我拿了《弘一大師講演錄》出來看,大約十點左右,正看到弘一大師在泉州開元寺慈兒院的開示,後半部舉釋尊因地修行,發菩提心的三則故事中的第三則時,偶然抬頭,西南方卻像起火一般一片火光,火光上層是濃厚的煙雲,好像業障很重的樣子,壓得人 透不過氣來,這似乎是好的境界,我找地圖來看,西南方?因為我大轉向,所以西南方應該就是東北方,也就是承天寺的方向,承天寺的方向出現光明,應該表示回承天寺是一件好事情吧!
當初我離開承天寺,本來就是發心不夠,常住有些事我不敢做,現在我準備回去了,因緣湊巧又看到弘一大師勸導求願往生西方的人必須發菩提心的文章,以及東方出現曙光等,感覺上這都是好的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