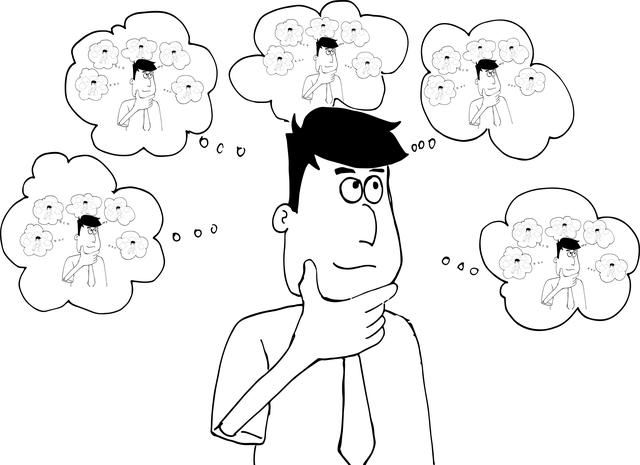
大卿 弘法師開示
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
愛、取、有、生、老死憂悲苦惱
夢醒之際,就是說這個十二緣起,是決定我們要迷?還是要覺悟的一個關鍵。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修行、要學佛?是為了要超越世間的苦海,要超脫世間苦海之前,要先瞭解造成苦海的原因。
世間的苦是有因有緣的,這個有因有緣就是十二緣起的「集」。十二緣起 ── 就是在探討世間的苦是怎麼演變來的?他的過程是怎麼形成的?也就是說苦是怎麼生起的?它是一種聚集而生的現象。
我們的生命好像一棵樹木的年輪,我們劃十二個同心圓,最中心叫「無明」,最外層叫「老死」,層層的關係,所有十二因緣的每一個外層都包括裡層。
這個年輪好比密宗所說的壇城,也叫曼陀羅,在早期佛教叫遍處,遍處的意思是一粒沙可以看到一個世界,一個東西代表一切。曼陀羅是一個「相」,一個觀想的東西,我們隨時觀察當下的心境是在十二緣起的那一層,隨時知道心在那裡,我們才能夠面對問題,解決煩惱。曼陀羅這個圖相,它可以穩定化,穩定以後你隨時可以感覺內心的引力和壓力,這個引力導向各種境界﹙欲界、色界、無色界﹚,有引力就會有恐懼和壓力,壓力釋放不當就會造業。
我們人很容易傾向於無明,常常靜不下來,卻不知靜不下來是苦。常常不知如何是好,一種莫名的不安,當我們沒有辦法很如實的面對當下的境界時,就是無明。又不知道苦是怎麼來的,也不想去瞭解,每天只想趨樂避苦,猶如煮菜煮得太鹹了,多加一點糖,以為這樣就不鹹了。卻不知世間苦不是用趨樂避苦所能解決,也不是世間任何一種追求和快樂的滿足所能解決的,世間任何種種保險,都無法保障我們不受無常、意外的衝擊。
只要這個苦你沒有真正去承擔,就不可能離苦得樂。即使你窮則變、變則通,你要適應世間種種的無常,仍然是趨樂避苦,仍然是苦海無邊。無常指無常火燒,無常真正衝來,是無法讓你思考的,根本沒有思考的空間。由無常變異苦,就會導致苦苦,貪導致愛別離苦﹙可意的得不到,或得到了又失去﹚、瞋導致怨憎會苦﹙不可意的偏偏在一起﹚、痴導致求不得苦、生老病死、五蘊熾盛﹙取執﹚、常樂我淨顛倒妄想的苦,展現為欲界眾生的愛、恨、情、仇、恩怨計較、憂悲苦惱。
當處在無明時,我們可以看到身心種種的衝動,包括呼吸的衝動、思維尋伺的衝動、各種感受、取相的衝動,這些衝動叫做身行、口行、意行。呼吸是身行的代表;我們有思維、有尋伺才有說話,叫做口行,就是說話的衝動、說話的前導;意行是由感受和取相做前導、也就是意根的衝動。
修「行」就是在修我們身、口、意種種的衝動。面對種種的衝動,我們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如何反應,不知注意力要放在那裡,就是一種無明。因為無明,又沒有去處理這個無明,就會變成一種無明行。無明行又會形成一種引力和壓力,所以,無明沒有破,又沒有修行就會造業。
我們要如何對治無明?無明不是那麼難轉、不是那麼難破,無明是注意力不當的問題。無明就是不用心去注意什麼是苦,不用心去注意苦是怎麼形成的、怎麼聚集的,不用心去注意苦滅的方法,不相信苦是可以轉、可以滅的,無明是可以破的。
世間人的注意力都是放在追求世間的快樂,佛教講的注意,是去注意世間的真理,「世間就是無常、世間就是苦、世間就是無我」,這三種世間的真理是一般人不願意去面對的,愈不願意去面對,對世間愈不瞭解,對世間的真理愈抗拒,苦就會愈來愈多。
佛經告訴我們要用「根本作意」來破無明。根本作意又叫「法印作意」,即是「諸行無常、諸行是苦、諸法無我、涅槃寂靜」。
談到作意,很多學佛的人都誤解,因為有一個作字,就以為是造作,以為造作就不好。某種程度當然是一種造作,但是,只要還沒有証,修行過程中就非得作意不可,因為只要你沒有根本作意,就一定顛倒作意,否則就是已証,証就是涅槃的意思,只要你不是在涅槃狀態,就非根本作意不可,否則就是無明。
作意就是「注意」,我們要如何注意事情?眼睛要如何看東西?看東西時要如何取角?空作意也是一種取角,佛法最高的境界是空作意,無常作意、無所有的作意、即是無所得的作意,都叫作意。只有一種人不必作意,就是阿羅漢入滅盡定﹙四禪九定的第九定﹚,否則所有的東西都要作意,沒有作意就沒有佛法可言,你也不用修了。在經典和律藏常常提到八個字「如理作意、如理精進」,這是包括阿羅漢在內的每一個修行人都要做的,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都不算是真正的佛教徒。
「作意」指的是你的第一個注意力、第一個觸,佛教講的是要「根本作意」。根本作意就是一心一意,把注意力放在適當的地方,全神貫注去認識世間的「無常、苦、無我」,連根拔除我們對世間常樂我淨的迷想和執著;徹底出離六根的繫縛,所以叫「根本作意」。
整個佛法都是在於對無常的理解,你對無常真正理解,就能理解苦;你對苦真正理解,就能理解無我;你對無我真正理解,就能知道涅槃。佛經說得很清楚,正觀無常就是正觀苦,正觀苦就是正觀無我,正觀無我就知道涅槃。它是有一定次第的,這些次第都是有它內在緣起的邏輯。
觀無常,就是在觀生滅,一切觸在生滅,六根、六塵、六識在生滅,你在每一個觸境都看到生、看到滅,看到世間就是來來去去、起起落落、生生滅滅,就是看到無常,你只有這樣的看到,你才能體會苦,才能體會每一個聚都在散、每一個生都在死,才能看到這一種生命的悲哀、這一種有生就有死、有聚就有散、有愛就有礙、有要就有不要、有依就有苦的悲哀。然後你才會看到我們所有的自卑、驕傲都是一種我慢、都是來自於好生惡死、趨樂避苦的反應,一切的「我是、我在、我能、我有」都是建立在眾生的苦難上,看不到眾生的苦,就看不到無我。
真正看到世間苦,你的身見一定要破的,因為看到世間苦,你無法分彼此。世間若沒有苦,你就沒有苦;世間若是淨土,你就沒有苦。當我們不分彼此時,就只有看到世間是無常、看到世間是苦、看到世間是無我,每一個看都是這樣,就看到涅槃寂靜。
身見破了,就沒有分別心,不會分別你的苦、我的苦,苦就是苦,不是你的、我的。苦是因為十二緣起,無明、行、識所造成的,而不是你、我、他所造成的。破身見以後,見苦就是見十二緣起,十二緣起裡面沒有「人」的問題。
無明就是不知道苦是什麼?不知道苦是怎麼來的?不知道要怎樣收攝?不知道要怎樣擔當?不知道要怎樣回心轉意?不知道注意力要放在那裡?不知道要用什麼角度來看這個世間?因為不知道,所以黑白取相,就叫顛倒妄想。
顛倒妄想就是取這個男女相、種族相、國土相、親疏相?很多的世間思維、人我對待,把苦當成樂、把無常當成常、把無我當成我、把不美的當成美、把不淨當成淨,佛教稱為顛倒作意。
顛倒作意就會產生漏,佛經用的字叫做漏,很生動喔!好像漏氣一樣。注意力有漏再和行﹙衝動﹚搭配起來,就產生無明的認識,簡單講就是無明的分別。識是一種分別,它就會分別內外、遠近、粗細、好醜、過去、現在、未來。
「識」好像一個過濾器,所有的東西進來都要經過識的過濾,過濾得乾淨就是空,過濾得乾乾淨淨就是涅槃寂靜的境界。如果過濾得不好,猶如水沒有經過好的過濾,就會有雜質、細菌、有害的重金屬一般。識也一樣,有明,有修行,我們才知道怎麼認識事情,認識就是知道如何過濾,過濾就是知道如何做事不會造惡業,形成不好的後果。
如何讓我們的識得到清淨呢?我們的方法是不斷的「正知當下」,正知為什麼要動?為什麼要聽?為什麼要看?正知當下每一個動都是為了少苦、離苦,所有與離苦、解脫無關的認識都是攀緣。識如果沒有正知當下,就無法過濾清淨,無法斬斷過去的恩恩怨怨,會變成五蘊的囤積,形成一種偏頗、不平衡的名色。
名就是心,心是無以名之的,叫心也好,叫名也好,因為無明行,造作業力的關係,它會有一種傾向、一種傾斜,就是「名」的意思。
色就是我們的色身,所有的色身都是一種礙,因為我們看一個東西時,就有一些東西我們看不見,當你在專注聽一種聲音,就無法聽到別的聲音,你有多少才華,這個才華就是一個礙,妨礙你做其他的事,所以聲音是礙、東西是礙、一切的色是礙,這叫色礙。
色也代表容易毀壞,因為所有的東西都在氧化、所有的東西都在燃燒,這是「色」的意思。名色代表容易傾斜、容易毀壞的意思。我們的身心是很危脆、很容易動搖的,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堅實,這個色身的地水火風是經不起壓縮的,我們很容易得病、我們經不起車禍、經不起撞擊,我們不能要怎樣就怎樣、不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佛經用「觀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時焰、諸行如芭蕉、諸識法如幻」來形容我們的五蘊身心。﹙這個我們在下一講「界蘊處的作意」會再詳細的講﹚。
名色簡單講就是身心,具體的講就是六入,什麼叫六入?就是六種內外進出的管道,「入」主要在強調外面的東西是怎麼進來的?比如我們看東西,注意力是怎麼進來的?眼根怎麼看?耳根怎麼聽?身根怎麼觸?意根怎麼想?也可以說是十二入,分成內六入與外六入內。內六入是眼、耳、鼻、舌、身、意;外六入是色、聲、香、味、觸、法,就是六根和六塵。
「六入」是在講六根與六塵的關係,就內六入來講,六塵只是一個相,我們對外界的認識都根據這個相,這個相只是如同攝影機取到的一個鏡頭,並不等於原來的東西,你看到一個影像,對它做一個聯想就是相的意思。一切都只是一個相,眼根看如此,耳根聽也是如此,耳根在錄音,我們的外面有很多聲音、裡面也有很多聲音,你在錄那一個聲?外面的聲和裡面的聲有什麼關係?這就是「六入」,需要心很靜的去看,才能瞭解內外的關係。
沒有六根與六塵,就沒有六識,有「根、塵、識」的對焦,才有所謂因緣合和的觸。觸一直在無常地流動、生滅變異,識也無常地流動、生滅變異,依「明」而有明的緣生,依「無明」而有無明的緣生,生與滅分別有其「前緣」。
佛陀說識是非一非異,須臾轉變、異生異滅,如獼猴抓一放一,不捨晝夜。所以說識最無常,無常就是一抓一放,一抓就是收縮,一放就是推出,遇到境界好像蝸牛,你摸它,它就往內縮,發覺沒有人摸,就又伸出來,我們每天都在做這樣的事,內縮、外推。我們眼根看,看到不對勁就縮起來,想看又推出去,我們一直在找,一直在尋尋覓覓,想找一個著力點、找一個立足點。
六根六識一直在動,因為一個剎那不能容許兩個念頭,必須一抓一放才能看到東西,不斷去體會這一抓一放的關係,一直去感受識的生滅、起落,去感受這一抓一放所產生的張力,這個張力裡面有引力、有壓力,它不斷形成我們內在一種很強烈的不安。
「觸」是一種會流,剛好碰在一起,每一個觸都是一個剛好;都需要對準焦距,沒有對準焦距的觸是模糊的;都需要用力,沒有用力就無法對焦,就看不清楚、聽不清楚;觸是現前境界的衝擊,每一個觸都是一個漩渦。
我們六根在觸、身口意在觸,走路在觸、坐著在觸、躺下在觸,所有行、住、坐、臥的觸,當下都知道叫正知。比如上廁所知道、喝水知道、吃東西知道、嚼的時候知道、吞下去知道。當你去感覺每一個觸的時候,很微妙的,你會變得很單純,你的心就開始單純了。
問題是在於我們很忙碌,忙著觸,對每一個觸卻都沒有感覺到,我們有太多的觸沒有感覺,沒有吸收、沒有消化,胡圇吞棗,我們有很多觸,卻沒有一點心得,生命很沒有新鮮感。如果你懂得注意觸的話,你的生命是很新鮮的,你不用去很遠的地方,你就可以感覺到生命很新鮮,一種清新感,這在佛教叫做喜感,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
每一個動作都有觸,你現在只要把那個觸,把那個動作慢下來,去感覺一下,你從來沒有過的感覺。去感覺那個觸,因為每一個觸都有受,你說很多觸我沒有受啊!你越不知道你觸的受啊,你會愈增加你的愚痴,那叫不苦不樂受太多了,麻木不仁啊!有觸就有安住、有所依的問題,你的觸是安住在那裡?你的所依是什麼?你是依法?還是依不如法?
有觸就有各種受,受非常的重要,我們要時常問自己:「當下的受是什麼?」如果無法分辨當下的受,就回來觀察我們的身體,去感覺我們的身體是鬆還是緊?緊的話就比較偏向苦受,鬆的話就比較偏向樂受,要盡量去感覺當下的受。
一切的貪瞋痴都來自於對受沒有如實消化,很多的樂受沒有消化會變成貪;很多的苦受沒有消化會變成瞋;不苦不樂受沒有消化會變成痴。一切的受都來自於觸,可意觸沒有消化就變成樂受;不可意觸沒有消化就變成苦受;不知可不可意觸沒有消化,就變成不苦不樂受。
面對可意觸,比如我們的眼根被拉去,我們稱做奪目,我們的眼根被奪取了、整個心被佔據了,產生很多的喜貪,那種貪是一種被奪去魂魄的感覺。我們生起「樂受」,這個樂受讓我們的心不能收攝、不能安住。樂受本身是一種緊、一種引力,它佔去你的注意力,使你無法注意別的東西。裡面又有一種怕,怕它失去,所以又形成一種壓力,壓力是苦、心不能安住更苦。
「樂受」反應著我們內心的不安,如果你的心很寂靜,你不需要樂受,也不會對樂受有所求,更不會隨著樂受而浮動。面對不可意觸,我們開始排斥,排斥也是一種引力,你不喜歡,但你還是被拉過去,因為排斥而產生壓力,產生「苦受」,苦受是一種拉扯,一種對無常、苦、無我的抗拒。
即使「不苦不樂受」,也是苦,很多時候我們的六根被拉,不知道為了什麼?毫無目的,一種閒不下來的苦,甚至因為愚癡心而覺察不到。一切受是苦,這個受是講受蘊的受,觀一切受是苦,這個苦是行蘊的苦。苦受是苦、樂受是苦、不苦不樂受也是苦,因為一切受都有黏著性、都有衝動。如果看到這種行蘊的衝動,見到一切受是苦的時候,你就會收攝,猶如口吃到黃蓮,口張開立刻收攝,不要再吃了。
我們看苦要看到心,心的感覺和口吃黃蓮的感覺是一樣的,這樣才能叫觀苦。如此對世間的黏著,自然生起收攝的力量,見苦即收,不會讓我們的衝動一直衝出去,當下即離,自然的厭離世間的輪轉,這就是出世間法。
當你用出世間法來看世間的時候,很多事情你會很超然,你不再以你的主觀來觸世間,你看到世間就是無常、世間就是苦、世間就是無我;你看到一切受是苦,你所看到的就是這樣、就是法。你看到世間,你沒有衝動,你衝動一出來就是苦,這個苦只能跟慈悲喜捨打成一片,所以,你不輕易的動、不輕易的說話、不輕易的接觸六境。
你很有選擇性的守護開閉六根、很有選擇性的說話、很有選擇性的起心動念,因為看到世間苦,你就會收攝,極大收攝的力量。所以能見苦的人,很容易入定,很容易起觀,整個關鍵都在於能否見苦。一個解脫者,非不得已,不會讓六根對六境有太多的觸,這個非不得已叫做慈悲喜捨。每一個觸,都是為了少苦、離苦,每一個觸都是慈悲喜捨。
觸就是六根與六塵的對待,六根碰到六塵如何對待?如何反應?就決定這個漩渦,一個是順轉,就是無明轉,一個是逆轉,就是明轉。我們講六根,是吸收進來;講身口意,是展現出去。六根觸境,如果用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來過濾,我們的識就轉清淨,轉化出去的慈悲喜捨力量會更大,身、口、意更有選擇,身心才能換取平衡。
再經過法印作意的洗滌,每一個觸境都用法印來與境界相應,一印下去就看到無常,什麼是無常?看到一切都在生滅、起落、變化,一切都在內拉、外推,有吸力、有斥力,一切都在收縮、膨脹,一切都在動,動就是變,所有的動都是無常,正知當下在動,就是正知無常。為什麼動?就是苦,不能滿足於當下,世間是一個互動的關係,無法滿足於無聲勝有聲。無法動到隨心所欲,就是無我。
當我們在說話、或聽人家說話的時候,我們去注意、去感受說話每一個字的聲調、音量,高低、起伏、變化,感受裡面的起落、生滅就是感受無常;感受裡面的用力,就是感受苦;感受那種詞不達意、無法隨心所欲,說了半天也無法說出真正要說的東西,就是感受無我。
比如眼根看,眼睛定在一個定點就看不見;耳根聽,耳根定在一個定點就聽不到,無常就是六根觸境,很難停在同一個境、很難停在同一個定點,六根不曾定在同一個點上,只要不在「定」中,六根就是一抓一放,極度的無常,六根的觸是不斷的在尋伺,這是第一種無常的意思。
第二種無常的意思是,在不斷的尋伺裡面,他是間斷的、是不連續的,這個間斷就是空。沒有感覺到那個「空」,就會被時間逼迫,所有的過去、現在、未來都是時間的逼迫,有時間的壓迫感,就是常。
我們看見,是因為眼睛用力,不斷按下快門所捕捉到的鏡頭,我們以為連續,是因為我們在抓。每個觸都是六根對六塵的拉扯用力,其中有對未來可意的欲求、有過去世間思維的得失,有境界生滅起落所引發的蓋障、分心、不安。
看不到無常,就看不到拉扯用力的苦,你沒有苦的深刻體驗,就無法看到苦諦,就無法看到十二緣起,看不到苦就看不到無我,看不到無我就無法體驗涅槃寂靜。看不到無常、苦、無我,就會生起無明、顛倒作意,形成很多無明的衝動,造作無量無盡的煩惱,導致苦海無邊。
我們談苦,目的是為了看到苦之邊,但你若不認真的去面對,不認真的去看,你一直要談樂,不敢探究苦海的淵源,苦海的淵源就是十二緣起,不敢面對苦海就看不到它的邊,苦海不是無邊,只要你肯渡下去,肯去面對世間的苦,就會看到苦海有邊了。在一切觸境,如果沒有根本作意,會產生無明觸,導致種種無明受,對受的反應叫做「愛」。
「愛」在佛教的意涵,指的是執著性的貪愛、渴愛、和佔有欲,如感情、物質、財富的佔有,緊抓不捨。愛包括瞋,包括因不能佔有而引起自我毀滅的行為,也屬於這種愛。這是一種很強烈的好惡,樂受想要繼續、苦受希望它趕快消失,這都是一種渴愛所引發的強「取」。
「取」就是一種緊緊的抓住,順境我們想要緊緊抓住,怕它失去,即使是驚鴻一瞥,那種一瞥你也一樣抓得很緊。逆境我們也是緊緊抓住,和它抗拒,猶如溺水的人,企圖抓住一些東西,那種感覺就叫「取」。
於是不顧因緣、不管三七二十一,強強要,因為勉強的要去執取,才會「有續」﹙讀成台語理解﹚。
「有」就是想要繼續,很無明的想要繼續下去,要繼續各種關係,要繼續當下的身、口、意,要繼續那個被過去所制約的習慣,不願放棄過去的記憶、不願放棄過去的五蘊、不願從新做人、不願歸零,他就有續了,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就繼續輪轉不已。
因為有續而有生,生了以後,我們的五蘊就開始加強、開始囤積;地水火風空識就開始調整,而這種調整都是為了鞏固我們如聚沫般的身心﹙名色﹚、鞏固我們內在那種不堅實的感覺,然而種種的企圖、迷想都是很枉然的,但就是一直往那個方向、一直堅持、一直緊抓不放。
生代表所有的煩惱,有生就有苦,生苦之意是依附,依附四大、依附各種滋養、依附空氣、水份,都要依靠外在的東西,甚至依靠細菌,才能存活下來。我們看到生就看到死,這種無法克服的矛盾就是生的苦。生了以後就常常問:我有什麼?沒有什麼?我是什麼?不是什麼?我在…我不在…要是我,我就不會這樣;如果我在,這個問題就能解決?一種我能、我是、我在的「我慢」,並且時常對自己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活著有什麼意義、什麼目的?生起種種疑惑,種種的念頭,此起彼落,就是生的煩腦。
生了以後,就開始有缺東缺西的感覺,感覺自己很孤獨、寂寞,感覺別人不瞭解我、感覺無依無靠,這種種都是老、死的感覺。很容易憂愁、煩惱、著急、生氣、失望、這都是老、死的現象,所以這個老、死範圍很廣,包括對無常的驚惶,都是老、死的煩惱。
嚴格說來,生包括老、病、死、憂悲惱苦,看到生就看到它的死亡、看到它的老、看到它的病、看到它種種喜歡不喜歡所產生的愛別離苦、怨憎會苦、以及欲望所無法滿足的求不得苦。
明就是知道怎樣注意事情,知道苦是什麼、知道苦的因緣、知道苦滅的方法、相信苦因可以滅、可以轉。我們的注意力決定了我們今天有沒有精神,例如早上醒來有沒有精神呢?為什麼從有精神變成沒有精神?為什麼從沒有精神變成有精神?比如吃東西,吃完是有精神呢?或是沒有精神?這就是「界」,看我們和什麼東西在一起,明就是知道心會和什麼境界相應、很清楚心和境界的關係。知道以後就會注意,對於各種衝動就知道怎樣轉向、怎樣收攝、省力,就是修行。有明、有修行,對事情就有正確的認識,身心就很平衡,六根就容易守護,六根守護,心與境接觸時就不會產生無明觸。
要破「無明」,必須「無間根本作意」。根本作意在實修上展現為「無時不見苦」,無時不見沒有喜樂、沒有輕安柔軟、沒有捨念清淨﹙念頭不為外境所染﹚是苦;無時不見不修行、不安住、不寂靜只會更苦,是真的見到苦的根,真的要連根拔除。如果用八正道來對應的話,就是「正見」。正見就是無時不見苦,根本作意是學習無時不見苦。真正見苦,就見到苦集,見到苦滅,見到苦滅之道。
如果第一關沒通過,就要跳到第二關-修行。修行指修身、口、意﹙身行、口行、意行﹚三種。
首先要看身心的粗重,世間沒有一件事比身心粗重更苦,身心若不覺輕安、柔軟,無論你擁有什麼都不算是快樂。所以,我們要透過識界和風界的作意來調身、調心,達到輕鬆的狀態。
識作意呼吸,叫作風作意,風作意能創造空間,令心量廣大、令識清淨。識代表我們的心量,所以,觀呼吸不但能創造心靈空間,還能調和身心,使身心輕安、柔軟,這是收攝意根最簡單、也是最重要的方法。意念安住在出入息,注意呼吸和身心柔軟的關係,就是意根收攝;在思維、尋思的作意上,用慈悲喜捨,就是意根自在。
觀呼吸是要隨時隨地,有境界、無境界都要觀的,這樣才能不心浮氣躁,安住於心﹙意根﹚的浮動攀緣,否則心不守護、六根不守護、語業不柔軟,這樣是沒完沒了的,這就是為什麼有時觀念上想通,遇到情境,情緒又起的無始輪迴。意根比較不好修,所以我們透過出入息念,安住在呼吸上,使身心更柔軟,更能如理作意,使身心更輕安喜樂,更能以慈悲喜捨來發心、轉念。
再來看身體的衝動,看每一個動作有著急嗎?行住坐臥著急嗎?要正知每一個動,都是為了離苦,如果沒有苦就不必動,也不必說話。學習放慢動作,不能放慢1/4,就放慢1/8,再不然放慢1/16、1/32…… 只要比平時放慢一點,覺知就會跑出來。一直緩衝身、口、意的衝動,常常問自己:在忙什麼?急什麼?為什麼而忙?
眼根沒事就閉著,睜眼的時候,能選擇看或不看,能選擇才叫眼根自在;能選擇慈悲喜捨的看,就叫眼根收攝。耳根也一樣,只聽「義饒益、法饒益、梵行饒益」,這叫「聽聞正法」,叫守護耳根。其他的只是噪音、雜訊,要聽懂很費力,所以聽不懂不要勉強,更不要費力去聽,作意只有「慈悲喜捨」才不費力。不管對方如何不收攝、不如法,我只管如法、收攝﹙慈悲喜捨﹚、安住﹙有選擇﹚,如果沒有選擇,你會很累!
修口行就是看自己說話的衝動,練習看看能否說一個字馬上收攝;說一句話馬上收攝;說十句話馬上收攝,說完有沒有想再說的衝動,去看說話是因為慈悲而說,不是因為衝動而說。練習放慢說話的速度、放低說話的音調,去聽說話的聲波起伏,感覺說話的用力不用力,好像一條船,坐在無常的波浪上,然後向著慈悲喜捨的方向,我們就會覺得很輕鬆。
無時不收攝說話的衝動,不戲論。正語是我們說話的五個條件:適時、實在、柔軟、慈心、有助益﹙不妄語、不惡口、不兩舌、不綺語﹚。若不符合這五個條件,都是造惡緣,會影響我們的打坐。六根觸境的時候,不斷問自己:當下的受是什麼?看我們在感受裡取了什麼相?用什麼角度在注意事情?看當下的受、想,就是在看意行的衝動。
法講起來很簡單,只是看你怎麼抓?怎麼放?整個十二緣起就是在探討怎麼用心?怎麼用力?怎麼用力就是怎麼修行?最簡單、最省力的修行就是「慈悲喜捨」。怎麼用心就是要把注意力放在看清世間的真相,世間就是無常、就是苦、就是無我,你能看清世間的真相,就會看到涅槃寂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