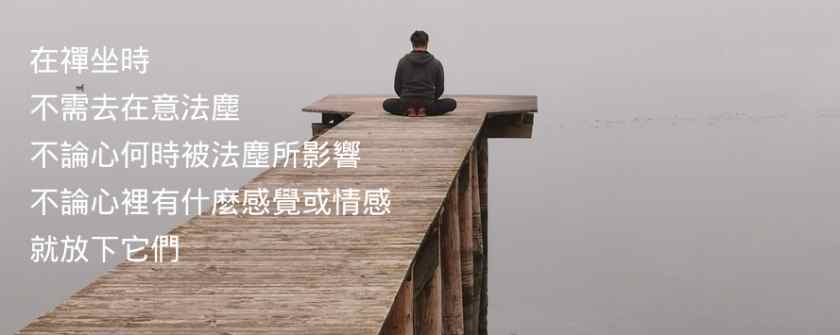
在坐各位尋善的人們,
請在平靜中聆聽。在平靜中聆聽的意思是:以「心一境性」來聆聽,注意你所聽聞到的,然後放下,這就叫作「使心平靜」。
聽聞佛法有極大的利益,在聽聞「法」時,我們被鼓勵去將身和心穩固地建立於「三摩地」之中,因爲,它是一種「法」的修行。在佛陀的時代,他們會在「三摩地」中聽聞佛法,目的是爲了要了知「法」法,於是,他的很多弟子會在他們坐著聞「法」時,實際地覺悟佛法。
這個地方是非常適合修習禪坐的。在這兒過了幾個晚上,我可以看出這兒是個重要的地方。在外在的層面上,這兒已經很安靜了,唯一剩下的,只是內在的層面 —— 你的心。因此,請大家努力地來注意。
你們爲什麼要聚集在這兒修習禪坐呢?因爲你們的心對於應該瞭解的並不瞭解,換句話說,就是不眞實地認識事物的本然或什麼是什麼。你不知道什麼是錯的和什麽是對的,是什麼帶給你痛苦和造成你疑惑。因此,首先你必須使自己平靜下來。你們到這裡來增長平靜和收攝的原因,是因爲你們的心並不平靜。你們的心不平靜、沒收攝,被疑惑和煩擾所左右;這就是今天你們來到這邊,並且現在在聽聞佛法的原因。
我希望你們專心、仔細地聽我所說的話,請你們允許我很直截了當地說,因爲我的個性就是如此。即使我以很強硬的態度說話,也請你們諒解,我這樣做是發自於慈悲的。如果我說了任何傷害到你們的話,請你們原諒我,因爲泰國的習俗和西方不一樣。事實上,口氣強一點也有好處,因爲,如此一來,有助於喚醒那些可能會昏沉或昏昏欲睡的人;寧可激起他們去聽聞佛法,也不願讓他們隨波逐流,反落於自滿之中,結果永遠一無所知。
雖然會出現很多修行的法門,但是,實際上卻只有一種。就猶如一棵果樹一樣,可以藉由剪枝的種法更迅速地收成果實,但是,樹卻沒有韌性或無法長久。另一個方法則是從一粒種子開始,就正確地培養它,這樣便能長出一株旣強且耐的樹。修行亦是如此。
當我初次開始修行時,我對這點的瞭解有問題。只要我依然不知什麼是什麼,坐禪對我而言眞是個難事,有時甚至促使我流淚。有時候,我意圖太高,有時候又太低,永遠找不到一個平衡點。要以平靜的方法來修行的意思是:將心放置在既非高也非低之處,也就是平衡點上。
我看得出這對你們而言相當困惑,你們來自不同的地方,而且與不同的老師修行不同的法門。來到這裡修行,你一定被所有的疑惑所困擾。一位老師說你必須這樣修行,另一位老師說你應該那樣修行,你想知道該用哪一種法門才對,對於修行的本質模稜兩可,結果混淆不清。有很多的老師,而且又有如此多的教導,以至沒有人知道該如何去調和自己的修行,結果是一籮筐的疑惑與不確定。
因此,你必須試圖不去想太多,如果你想,那就以覺知來想,可是,到目前爲止,你的思考都是沒有覺知的。首先,你必須使你的心平靜,有覺知的地方,就不需要思考,覺知會代而生起,而這將會成爲智慧。但是,一般的思考可不是智慧,只是無目的、無覺醒的迷惘之心罷了,無可避免地一定會造成煩擾;這不是智慧。
在這個階段,你不需去想(導致思考)在家裡你已經想很多了,不是嗎?它只會刺激心而已。你必須建立一些覺知,想得太多甚至可以你哭。去試試看,迷失在一些思路裡並不能引領你到眞理,這不是智慧。佛陀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學習了如何不去想。同樣的道理,你們在這裡修行,是爲了要去停止想,以致能達到平靜。如果你已經平靜了,就不需要去想,智慧就會生起而取代它。
禪坐,除了決定當下是訓練心的時候外,沒其他的了,你不需去想太多。別讓心左右、前後、上下遷動,我們當下此刻唯一的責任就是去修習觀呼吸。將你的注意力放在頭頂,然後往下移,經過身體到腳尖,然後再回到頭頂。將你的覺知經由身體往下移,並以智慧來觀照。我們這樣做是要得到一種對身體本然的初步的瞭解。接下來,開始禪坐,清楚知道,當下,你唯一的責任就是去觀照出入息。不要去強迫呼吸,使它比平常長或短,只,要讓它如往常般持續。別在呼吸上放置任何壓力,只要讓它均匀地流動然後,放下每一個入息和出息。
在你這樣做的同時,必須瞭解你正在放下,雖說如此,仍應該有覺醒。你必須持續這個覺醒,讓呼吸舒適地進入和離開。不需要去強迫呼吸,只要讓它輕鬆地、自然地流動。保持決心,當下你沒有其他責任或職責。關於會發生什麼事、你在禪坐時會知道或看到什麼的念頭,在你禪坐時,都會一再地生起。可是,一旦它們生起,就讓它們自己消失,不要過度地顧慮它們。
在禪坐之時,不需去在意法塵。不論心何時被法塵所影響,不論心裡有什麼感覺或情感,就放下它。不論這些情感是好的或不好的,都不重要。也不須去在意它們,只要讓它們消逝,然後回歸你的注意力到呼吸上。保持出入息的覺醒,不要因爲呼吸太長或太短而感到痛苦,只觀照著它,不要試圖以任何方法來控制或壓抑它;換句話說就是:不要執著。讓呼吸順其自然地繼續進行,心就會變得平靜。就在你繼續的時候,心會逐漸地放下事物而開始歇息。呼吸會變得愈來愈輕,乃至變得非常細微,彷彿完全消失了一般。身和心都會感到輕安且精神飽滿,唯一持續的將會只有「心一境性」。你可以說,心已經改變了,而且達到了平靜的境地。
如果心煩亂的話,提起正念,然後深深地吸一口氣,直到再也吸不進去爲止,接下來,將它毫不存留地完全吐出來。依照這個方法,再做另一次深呼吸,直到吸滿爲止,然後再吐出來。這樣子做兩、三次,然後再重新將專注力建立起來,心應該就會更平靜。假使任何法塵造成內心煩亂,每次就再重覆這個方法。這和行禪很類似:假如行禪時,心變得很煩亂,就停下來,將心安定下來,重新建立起對禪修主題(所緣境)的覺知,然後再繼續經行。坐禪和行禪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只在於身體姿勢的使用不同罷了。
有時候,也許會有疑惑,所以你必須要有「正念」,做一位「覺知者」,繼續追隨和審視任何形態下的煩亂的心,這就是有「正念」。正念觀察和照顧心,不論心呈現什麼樣的狀態,你都必須保持這個覺知,不要散亂或到處跑。
訣竅是,擁有「正念」在控制和監督心,一旦心和「正念」統一時,一種新的覺知將會現起。已經增長了平靜的心,被那個平靜所約束,就如同一隻關在籠子裏的雞……,雞無法在外面到處亂跑,可是牠仍然可以在籠子內走動。牠的來回走動不會造成麻煩,是因爲牠被籠子所約制。同樣的道理,當心擁有「念」且平靜而不會造成麻煩時,所產生的覺醒也是一樣,沒有任何念頭和情感會在平靜的心中產生,而造成傷害或干擾。
有些人完全不想要經驗任何的念頭或感覺,可是這是大錯特錯的。感覺在平靜的狀態下生起,心於是同時經驗感覺和平靜,而不被干擾。一旦有這種平靜時,就不會有有害的結果,問題都是發生在當「雞」跑出「籠子」的時候。例如,你可能在觀呼吸的進與出,然後就忘了自我,讓心離開呼吸到處亂跑,跑回家,跑到店鋪裏或其他不同的地方。也許在你突然發覺你應該修習禪坐而譴責自己不夠正念時,半個時辰已經過去了。這裡就是我們必須相當小心的地方,因爲這就是雞跑出籠子的地方 —— 心離開了它平靜的基礎。
你必須小心照料,來維持正念的覺知,並且試著去把心拉回來。雖然我用「把心拉回來」這個字,可是,事實上,心實在哪裏也沒去,只是覺知的對象改變罷了。你必須使心待在當下這裡與這時候,只要有「念」,就會有當下的心。看起來好像是你在將心拉回來,但是,它眞的哪裡都沒去,只是改變了一點而已。心好像跑到這裡、跑到那裏,可是,事實上,改變也只是發生在同一點上。當「念」重新復得時,一瞬間,不需將心帶回來,你就已經回來和心在一塊兒了。
一旦有了完全的覺知 —— 一種在每一剎那中持續且不破壞的覺醒,這就稱做當下的心。假如你的注意力從呼吸那兒溜到其他的地方,如此一來,覺知就破了。只要有呼吸的覺醒時,心就在那兒。只要與呼吸和這個均匀且持續的覺醒同在,你們就有當下的心了。
「正念」和「正知」必定是同時存在的。「正念」是憶持力,而「正知」則是自我的覺醒。當下,你清楚地覺知呼吸,這種觀呼吸的練習協助了「正念」和「正知」一起增長,它們分工合作。同時擁有「正念」和「正知」就好像擁有兩個工人拉一塊重木頭一樣。假設有兩個工人要拉起一塊重木板,可是木板卻非常重,所以他們必須非常用力,幾乎無法忍耐。後來,另一位慈悲的人看到他們,便會趕緊去幫忙。同樣的道理,有「正念」和「正知」的時候,「般若(智慧)」將會在同一個地方生起來協助。如此一來,它們三者便彼此互相支持。
有了「般若」,對法塵便會有一種瞭解。例如:在禪坐的時候,種種法塵被經驗,因而引發感覺和情緒。你或許會開始想一位朋友,可是,「般若」應該會立卽以「沒關係 」、「停止」或「忘掉它」來對治。抑或,如果 是關於明天你將去哪裏的念頭,那麼,反而應該是「我並不感興趣, 我不要 讓自己去顧慮這類的事」。也許你會開始想到別人,那麼,你應該想:「 不,我不想陷入其中 」、「放下」或「這一切都是不確定的,而且永不是確定的事物。」在禪坐中,你應該這樣來解決這些東西,視它們爲「不穩定、 不穩定」,並且持續這種的覺知。
你必須捨棄所有的念頭 —— 心裡的對話和疑惑,在禪坐中別讓這些東西束縛住。最後,只會剩下「正念 」、「正知」和「般若」最純粹的形態在心中。只要這些一微弱下來,疑惑就會生起,但是,試著去立刻丟棄它們,只留下「正念 」、「正知」和「般若」。這樣試著去增長「正念」,直到能夠 在一切時中維持不斷。如此一來你就會全然地了解「正念」、「正知」和「般若」了。
將注意力投注在這點上就會看到「正念 」、「 正知」和「般若」在一 起,不論你被外塵吸引或厭惡,都能夠告訴你自己「不一定」。這兩者都只是要掃除的障礙,直到心清淨爲止。剩下來的應該只有「正念」、「正知」和「三摩地(堅定不動搖的心)」及「般若(無上的智慧)」。這個時候, 對於禪坐主題(所緣境),我就只說這麼多。
現在,我們來談關於禪修的工具或助手 —— 你的心中應該要有慈悲(metta),換句話說,就是慷慨的本質、和藹及協助。這些都應該被保留做爲心靈清淨的基礎,例如,透過布施來除去貪(lobha)或自私自利。當人們自私自利時,他們並不快樂。自私自利會導致不快樂的感覺,然而,人們卻仍非常自私,毫無覺察到它是如何地影響我們。
你能夠在任何時間經驗到這點,特別是在你飢餓的時候。假設你有一些蘋果,並且有機會可以和一位朋友分享;你想了一下,而,當然啦!要施予的動機並沒問題,可是,你想給那顆較小的。要給大的那顆的話 ……嗯,太可惜了,要想得正確很難。你叫他們去拿一個,可是,你又接著說:「拿這顆!」…… 於是便給他們那顆較小的蘋果!這是人們通常沒覺察到的一種自私的形態。你曾如此過嗎?
你實在必須違背自己的意願來布施,縱使你眞的只想給予較小的蘋果,也必須強迫自己給較大的那顆。當然,一旦你將它給了你的朋友,內心就會感到很舒服。藉由違背自己的意願來如此訓練心,需要有自我的訓練 —— 你必須知道該如何施予和如何捨棄,不允許私欲來黏著。一旦你學會了如何施予他人,你的心將充滿歡喜;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施予,如果你還在遲疑要給哪一顆水果的話,那麼,就在你沉思之際,你就苦惱了。然而,即使你給了較大的那顆,仍會有不願意的感覺。可是,只要你堅決給與較大的,事情也就了結了。這就是以正確的方法來違背意願。
這麼做你便會成爲自己的主宰。如果你辦不到的話,你自己將是個受害者,而且還會繼續地自私自利。我們在過去都曾自私過,這是個我們必須斬除的煩惱(雜染)。在巴利聖典中,施予叫做「布施(dāna)」,意思是帶給他人快樂。這是種種修行中的一種,可以使心清淨無煩惱(雜染)。反觀這點,並且在你的修行中增長它。
你也許會認爲如此修行包括要不斷地追迫自己,可是,卻不盡然。實際上,它是在追迫貪愛與煩惱的。假如煩惱在你內心生起,就必須實際行動去對治它們。煩惱就如同一隻流浪貓,如果牠要多少食物你就給牠多少的話,牠就會時常來你左右要吃的,但是,如果你停止餵牠,幾天之後,牠就會停止再來。煩惱也是一樣,它們將不會來打擾你,讓你的心住於平靜。因此,讓煩惱害怕你,而不要你去害怕煩惱。要讓煩惱害怕你,你必須現在就在你的心中看見「法」。
「法」是在何處生起的呢?它是和我們的覺知與理解生起的。每一個人都能夠知道和瞭解「法」。「法」不是件必須在書中尋得的東西,你不需要做很多的研究才能看到它,只要當下反觀,然後,你便可以明瞭我在說什麼了。每一個人皆能看到它,因爲,它就存在我們的內心裡。每個人都有煩惱,不是嗎?如果你能夠看到它們,那麼,你就可以瞭解了。過去,你們照料和放縱你們的煩惱,可是,如今,你必須知道自己的煩惱,並且不讓它們來干擾你。
下一個修行的構成成份是「戒」。「戒」會看顧和滋養修行,就如同父母親會照顧自己小孩的道理一樣。守持戒律的意思並非只去避免傷害他人,還要協助和鼓勵他們。至少,你應該守持五戒,如下:
一、除了不殺或有意傷害他人外,同時要向一切眾生散播慈悲。
二、要誠實,自我抑制不去侵害他人的權力,換句話說,就是不偷盜。
三、知道適度的性關係:在家庭的生活中,存有家庭的組織,基本在於丈夫和妻子。知道誰是你的丈夫或妻子,知道節制,知道性活動的適當限度。有些人不知限度,一夫或一妻不夠,他們必須要有第二或第三個。依我的看法,連一位配偶都已經太多了,因此,有二或三位只是耽溺罷了。你必須使心清淨,並且訓練它知道節制;知道節制是眞實的清淨,沒有了它,你的行爲便沒有了限制。在吃味美的食物時,對它的味道如何別想太多,想你的胃口和操心它適當的需求是多少。如果吃太多,就會發生問題,所以你必須知道節制。節制是最好的方法。只要一位配偶就夠了,二或三位就是耽溺,而且只會造成問題。
四、言語要誠實 —— 這也是一個撲滅煩惱的工具。你必須誠實和正直。
五、要自制不說妄語。你必須知道要約束,並且喜於將這一切皆捨棄。人們已經對他們的家庭、親戚、朋友、物質財產、財富和等等一切說了夠多的妄語,不說妄語使事情變得更糟已經很不錯了。這些只會在心中製造黑暗,那些常說妄語的人,應該試著去逐漸減除,乃至最後一道捨棄它。也許,我應該向你們道歉,可是,我這麼說是發自於爲你們好的關心,以使你們能夠了解什麼是好的。你必須知道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東西在你們每天的生活中壓迫著你們?善行帶來善果,而惡行帶來惡果;這些都是「因」。
一旦戒行清淨,對他人就會有一種誠實和慈悲的感覺。
這將帶來快樂和從憂慮與懊悔中解脫的自在,從侵略和有害的行爲中所造成的懊悔將會消失,這就是一種快樂的形態,幾乎像天界。擁有舒適,你在戒行中生起的快樂中舒適地吃和睡。這就是結果 —— 守持戒行就是「因」。這是「法」的修習的核心,抑制惡行,以致善可以生起。如果這樣來守持戒行的話,惡會消失,而善便代之生起。這就是正修行的結果。
可是,這還不是終點。一旦人們獲得一些快樂,就會不留心,並且在修行中不再有任何進展。他們陷在快樂之中,不想要再更上一層樓,反而較喜歡「天」上的快樂。那兒雖然平靜,可是卻沒有眞實的理解。你必須保持反觀,避免被染汚,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反觀這個快樂的不圓滿。它是無常的,不能常久存在,再過不久,你就會和它隔離了。它是不一定的,一旦快樂消失之後,苦就會代而生起,於是淚水就會再次落下。卽使天界眾生到頭來也要痛苦和哭嚎。
因此,世尊教誡我們要反觀種種的存在。通常,經驗到這種快樂時,其中是沒有眞實的理解的。眞正、確實和持續的平靜被虛假的快樂所矇蔽。這種的快樂不是確實或永恆的平靜,但是,卻是個煩惱的型態,是我們所執著的細微煩惱型態。每一個人都喜歡快快樂樂的,快樂的生起是因爲我們喜歡某物,只要這個喜歡一轉變成不喜歡,苦便生起。我們必須反觀快樂,以至看見它的不確定和極限。
一旦事物有了遷變,苦便生起。這個苦也是不確定的,別認爲它是固定的或確實的。這種反觀叫做「患難觀(adinavakathā)」——反觀因緣和合世間的不圓滿和有限度。這兒的意思是反觀快樂,而不是去接受它的表面價值,視它如不穩定的,不應該去緊緊地握持它們,而應該握了它就放下,瞭解快樂的利益和傷害。要善巧地禪坐,你必須看見在快樂中的不圓滿之性質。如此地反觀:當快樂生起時,徹底地思惟它,直到這不圓滿變得顯而易見。
當你瞭解事物都是「苦」的時候,你的心將會明瞭「捨離觀(nekkhammakath)—— 反觀捨離。心將會變得不關心,而尋找解脫之道。不關心來自於看見「色」的本來面目、「味」的本來面目、「愛」與「恨」的本來面目,我們是指對事物不再有欲念要握持或執著,而從執取中退出來 —— 一個你可能舒適安住的境地,沉靜地觀照就是執著的解脫。這就是從修行中生起的平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