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各答的天使

(Mother Teresa,1892 ~ 1986)
簡 介
「在信仰上,我是一個天主教修女;就個人的期許而言,我屬於全世界;就我的心靈來說,我完全屬於耶穌基督。」德蕾莎修女是名符其實的社會工作者,她將服務人群所必需的慈愛與專業,實實在在地結合起來並發揮到極致,因而成就如此偉大的志業。更重要的是她崇高的人格,吸引了廣大的追隨者,組成了一面鏡子,讓社會大眾時時刻刻可以自我提醒:奉獻、慈悲與愛是每個人的義務及權利。
上帝的召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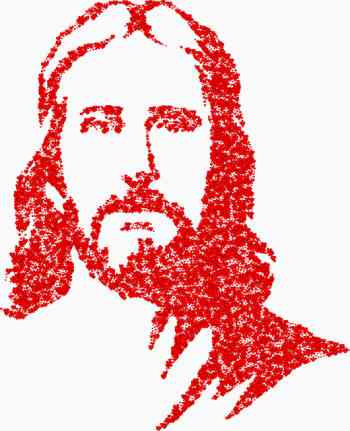
1910年8月27日,德蕾莎修女誕生於南斯拉夫的斯科普里(Skopje,現屬馬其頓共和國)。
她的父親為建築包商,經營一家小公司,因此家境尚稱小康。身為家中的老么,她有一位大她六歲的姊姊,一位大她三歲的哥哥。父親在德蕾莎修女七歲時去世了,此後由母親一肩扛起全家人的生計,做女紅來撫養三個兒女。德蕾莎修女從小在母親的堅忍之下耳濡目染,也讓她成為一個充滿韌性的女性。
十二歲時,她在一所天主教小學就讀,上帝的聲音在德蕾莎的心底開始呼喚,為主奉獻的想法也因此開始萌芽,要她今後以傳教佈道為終生職志,而主的呼聲就一直停駐在她的心靈深處,從未停息。在這段期間,她一直是學校「瑪利亞之女」社團的活躍份子。不只如此,在天主教耶穌會的教區神父鼓勵下,她也立志要前往世界各地傳教,散播福音。而她的哥哥拉薩,則在這個時期前往奧地利,就讀於一所軍事學校,並且在日後成了一位騎兵隊的軍官。
1928年的某一天,德蕾莎修女在史柯傑市的聖殿祭壇前禱告。跪在主的跟前,德蕾莎聽到一個非常清晰、明確的呼喚聲音在心裡迴盪,那個聲音對她說了什麼,沒有人知道。後來德蕾莎只說:「聖母對我指點迷津,幫我找到未來的生涯之路。
不久,德蕾莎修女在一位南斯拉夫籍的耶穌會成員的引導、協助下,順利申請到「羅利多聖母院」的入學許可,這個建立於十六世紀,具有悠久歷史的神學院,在天主教界頗負盛名,而它通常被稱為「愛爾蘭女修道院」,創辦人是瑪利亞修女。德蕾莎修女對這個修道院心有所屬的原因,是因為它有一支傳教隊伍,專職在印度傳播福音,並幫助當地的人民改善衛生與教育的問題。經過兩個月密集的英語課程訓練後,德蕾莎修女搭船前往印度,在三十七天後於1929年的6月6日抵達了加爾各答市。
1937年5月24日,德蕾莎修女在這一天宣誓成為神職人員,並立志終身為主奉獻。德蕾莎也積極地在神學的領域鑽研,對神學教育多有涉獵,後來更成為羅利多聖母院的教學部主任。當德蕾莎修女回溯一生的神職生涯時,有一段這樣的結語:「我是羅利多聖母會裡最快樂的修女,因為我將所有的心力都放在教學上,而這個工作就是在撒播天主的愛給世人,就是在盡一份使徒的真正任務。我非常、非常喜歡這樣的工作。」
加爾各答的修女

在德蕾莎抵達加爾各答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印度由來已久的貧窮問題更是雪上加霜。
1943年印度東北部的孟加拉,因為飢荒而餓死的民眾超過五百萬人,大批的難民湧進加爾各答,但大多也難逃橫屍街頭的命運。飢餓致死的人數,據說竟達二百萬人。
德蕾莎與其他修女們住在一所宏偉的修道院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很有規律。修道院的建築非常的堅固與完善,還有一個綠草如茵的花園,因此相對於加爾各答貧苦的大眾們,她們的生活是相當安定而且舒適的。
修道院四面都有高牆,修女們平日不能隨意外出,必須在修道院內過著安貧樂道且自足的生活;有時逼不得已為了看病,才會乘著汽車離開修道院,但是一當求診完畢,就得馬上回到修道院。因此她們事實上雖身處加爾各答,但是卻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與當地人民的接觸可以說是少之又少。牆內,牆外,是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
1948年某天,德蕾莎順著一個機緣外出。當她走在加爾各答的街上時,映入眼簾的盡是骨瘦如柴的貧民,又餓又病的他們,身處蚊蠅亂飛、衛生極度落後的環境。一時間,加爾各答恍如是一個被上帝遺忘的地方。正當德蕾莎被眼前的景象大大震撼的同時,路旁突然有一個乞丐,對著德蕾莎哀求道:「我很渴!我很渴!」此時德蕾莎心裡宛如出現了一道曙光,她想起耶穌基督在為世人受罪之時,同樣也對身旁的人說道:「我渴 …… 眼前的乞丐在她眼中顯現出如同耶穌的聖顏,如同上帝的召喚,於這一刻引發了她慈悲濟世的情懷。她當下決心要走出修道院,把愛送到每個需要的角落。因為她知道,光是封閉在修道院中,不能幫助貧苦大眾的生活,會讓她羞愧難過。這一念的轉變,讓德蕾莎走入貧民窟,以窮人的姿態去服務窮人,開始了她對貧苦大眾的憐愛與奉獻。
披上沙麗
1948年2月7日,德蕾莎修女寫信給羅馬的天主教教會,申請離開羅利多修女會,決心要貼近印度貧苦的人民,盡一己之力為他們服務。得到梵蒂岡的許可後,她離開了那座四面都是高牆的修道院,並且脫下了羅利多聖母會的傳統修女服飾,改披裹印度的民間服裝「沙麗」。
白棉粗布的「沙麗」,是印度階級社會中最低層的「吠舍」所穿的。但德蕾莎修女認為不應該有階級的存在,任何人都 是「主的兒女」,因此她既然要為窮人服務,就應該感同身受,和他們過一樣的生活、穿一樣的衣服。有別於一般傳統的形式,德蕾莎修女的紗麗有一道藍色的邊,象徵她嚴守貞潔,效法童女瑪利亞。她離開加爾各答,花了三個月時間在基礎護理的密集訓練課程上,然後再回到加爾各答,為當地流落街頭、又疾病纏身的貧苦大眾發揮所學,以實現她救人濟世的心願。
垂死之家的創立

有一天,德蕾莎修女搭乘火車,坐在車廂中等待火車離站,望著窗外發現遠方有一棵大樹,大樹下坐著一位衣衫襤褸、呼吸微弱的老人,從他臉上的氣色看得出來,又是一個又病又餓的可憐人。
德蕾莎修女心中的悲憐頓時湧現而出,迫不及待地想要下車去看看這位老者,然而此時火車已經緩緩開動了,德蕾莎也只能按捺住自己,想著等回到這裡時再來看看他。但是,等德蕾莎再度乘著火車回到原地時,卻發現這個老人已經在這棵樹下去世了,老人的儀容枯槁憔悴,眼睛旁更掛著兩行已乾的淚痕。此時德蕾莎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愧疚與哀傷,心中也浮現了一個想法:眼前這位過世的老人,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如果身邊有人可以陪著他、照顧他,聽聽他最後的遺言,一定可以使他比較安詳地離開。
之後有一次,德蕾莎要到巴丹醫院協商一些護理援助的事務,在車站旁的廣場發現了一位老婦人橫倒在路上,像是死了一般。德蕾莎趕忙上前視察老婦人的情況,她蹲下來一看,老婦人的一隻腳似乎受了傷,裹著破布的傷口滲出血跡,上面還爬滿了螞蟻;頭上也有一個似乎是被老鼠咬的傷口,腐爛的傷口周圍滿是蒼蠅和蛆蟲。
她馬上為老婦人測量呼吸及脈搏,發現她尚有一絲微弱的氣息。德蕾莎為她趕走蒼蠅、螞蟻,擦去血跡和蛆蟲,並為她的傷口進行消毒與包紮。德蕾莎心想:如果讓她繼續躺在那裡,這個老婦人短時間內就會去世。於是她暫時取消了去巴丹的計畫,並請人幫忙把老婦人送到附近的醫院。
院方一開始並不肯收容這個身份不明又沒有家屬的老婦人,但德蕾莎此時對醫生再三地懇求,說服他為這位可憐人治療。德蕾莎的執著感動了這位醫師,因此他為老婦人進行了檢查與醫治,並對德蕾莎說道:「她必須暫時住院,等到脫離危險期,還得再另外找個地方靜養。」
德蕾莎把病人暫時安置在醫院後,就到當地政府的健康機關尋求協助,希望能提供一個讓貧困病人休養的場所。健康機關裡的主管官員是位熱心且大方的人,聽完德蕾莎的請求後,深為她的仁慈所感動,便帶她來到加爾各答一座有名的寺院,答應將寺院後方一塊場地免費提供給德蕾莎使用。然而這樣的舉動,卻遭受寺院與許多印度教徒和地方人士的反對,理由是德蕾莎不是印度人,也不是印度教徒。
德蕾莎不畏這些強烈的阻擾,深信自己的理想是對的,決心要以行動來軟化這些障礙,讓他們知道自己雖是外國人與天主教徒,但是自己的愛卻是不分國界與宗教的。她依然積極地在街頭搶救許多疾病纏身的貧民,送到收容所來替他們清洗包紮,提供他們庇護與照顧,而其中也包括印度教的僧侶,此舉感動了許多的印度人。於是反對聲浪就漸漸地平息了,這就是「垂死之家」的開始。
垂死之家成立的第一天,就安頓了三十多個貧困痛苦的人,而那位傷痕累累的老婦人,在當天的傍晚就過世了,臨死前老婦人拉著德蕾莎的手,用孟加拉語低聲地說:「我一生活得像條狗,而我現在死得像個人,謝謝妳 ……。」
德蕾莎的作為,感動了許多人,並讓他們也紛紛加入服務的行列。垂死之家的義工有將近三十位婦女,其中有十多位立志要終身為這些患者服務,她們包括十二名的見習修女,另外幾名則是有志從事神職工作的婦女。垂死之家除了照顧貧民區中遭人遺棄的兒童、病患和奄奄一息的窮人,還投入研讀聖經和組織教會成員的工作。
光靠德蕾莎及修女們的工作,要救助每一個貧苦者是不可能的,但德蕾莎有她自己獨特的看法:她認為人類真正的不幸,並非遭遇貧困、疾病或飢餓的命運;真正的不幸,是當人們生病或貧困時沒有人伸出援手。縱使生命將走到盡頭,在臨終時也應該有尊嚴與歸宿。因此德蕾莎向垂死者傳播了主的愛,安定了這些徬徨無助的靈魂。
1960年代,垂死之家在加爾各答聲名遠播。所有迫於生活無法就醫、在街頭生病、需要幫助的貧民,都知道這個能夠讓他們安息的地方。收容所的規模開始疾速成長,因為需要更多的人力來投入垂死之家的工作,所以德蕾莎開始招募全世界有愛心的人一起來加入她的行列。一傳十,十傳百,德蕾莎的善行義舉,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極大的迴響。
1969年,英國記者馬科爾・蒙格瑞奇拍攝了一部以德蕾莎修女為題材的紀錄片〈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片中寫實、貼切地傳達了印度貧苦大眾的無奈,以及德蕾莎修女貼近人群,發願要照顧最貧困的人的精神。這部著名的紀錄片不但讓世人看見世界上的貧窮角落,更讓大家了解這位仁慈的修女,是如何憑藉著她的博愛,來感動我們心中那慈悲的深處。
生命的里程碑
1971年,教宗庇護十二世頒給德蕾莎修女,教宗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和平獎;同年的甘迺迪獎也頒發給她,此外她還獲頒了1975年的史懷哲國際獎、1985年美國總統自由勛章、1994年美國國會金牌、1996年11月16日美國名譽公民等獎項,以及許多大學的榮譽學位,足見她的影響力及受重視的程度。而最受矚目的,當然就是197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當時她拒絕出席頒獎宴會和領取獎金,她說:「我做的不算什麼,但我很高興獎金授予了我,因為這說明了人們對世界上的窮人是關心的。」
媒體問她:「我們可以做什麼來促進世界和平?」
她簡短地回答:「回家和愛您的家庭。」
回到上帝的跟前

1983年,德蕾莎修女到羅馬拜訪教皇保羅二世時,心臟病第一次發作。當1989年心臟病第二次發作時,她接受了人工心臟的安裝。
後來她於1991年從墨西哥拜訪回來之後,更因為得到肺炎,健康日趨惡化。於是她向自己的教會提出辭呈,理由是她的健康狀況已經無法負荷。然而在修會的秘密投票下,成員們都希望德蕾莎修女可以留在會中,繼續領導她們。德蕾莎也深感自己放不下世界上的貧苦大眾,因此最後仍決定留下繼續服務。
1993年4月,德蕾莎修女跌倒並傷到鎖骨,8月時她接受了心臟移植手術,但健康並沒有日漸好轉。1996年她請辭會長的職務,請求終於獲准,並在次年9月,87歲時逝世。德蕾莎修女一手創辦的團體中,留下了四千個修會的修女,超過十萬以上的義工,還有在123個國家中的610個慈善工作團體。全世界都哀悼這個偉大靈魂的凋零,印度甚至為這位聖人舉行了國葬。
德蕾莎修女在世時,常奉勸富有的人說:「要奉獻到心痛為止。」不痛不癢的奉獻只不過是施捨而已,而這「心痛」,其實也就是感動,對貧弱者的處境感同身受。世人最企盼的大愛,不也由此而生嗎?德蕾莎修女曾說過一句話:「我們都不是偉大的人,但我們可以用偉大的愛來做生活中每一件最平凡的事。」即使自身的力量有限,但若是能秉持著愛世人的精神來奉獻服務,則每個人都是偉人。
德蕾莎修女語錄
◎ 愛就像一件大衣的縫邊,那裡最容易接觸到灰塵,那裡也最容易抖落灰塵。從街頭一直抖落到街尾,因為它能夠做到,也必須做到。
◎ 用你們的雙手去做奉獻,用你們的心去愛別人。
◎ 每一個人都是天主用祂的雙手所銘刻出來的,所以,我們或多或少都知道天主愛世人。但是,不論信奉哪一種宗教,若是想要真正去愛別人,首先就得學會對任何事都能予以寬恕。
◎ 天主不曾創造貧窮,是世人把貧窮創造出來的。在天主的面前,我們都是窮人。我願意在任何時機、任何夜晚或白天,照顧任何孩童,只要我能夠認識他,我就會接納他。
◎ 在這整個世界中,我們有很多弟兄生活在貧窮中,他們分散在各地,只要我們有眼睛就可以見到。所以,你應該向四周注視,並且讓你的神智能夠保持清明。你應該把愛付給別人,就像主把愛付給你一樣。
◎ 誠心就是謙卑,而我們得以謙卑,完全是因為我們能夠接納屈辱。
◎ 彼此之間也應該善待對方。與其以不厚道手法來營造奇蹟,倒不如用謙和態度去承認自己的過失。
◎ 他們會笑、會哭,他們是人,像你我一樣。他們需要有人協助,不是只需要別人的同情。
◎ 認識自我是生命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有了這份認知,我們就會心生謙卑,就會認識天主,也因此了解到天主會製造愛來送給世人。
◎ 貧窮就是一種自在。如此,我們就會認為自己目前所擁有的絕不可能永遠屬於我的;就會認為既然自己無法永遠保存,那又何必為了這些東西向人彎腰屈膝呢?就會認為拿一部分送給別人或者全部送給別人,又有什麼捨不得呢?
◎ 我們必須確認:遺棄就是一種最可怕的貧窮,我們實在有必要去認識一些窮人中的最窮者。當我們從自己的鄰居、從自己居住的城鎮、從自己的家庭中尋覓到這些人時,才能開始去關愛他們。有了愛,我們才會受到它的驅使,進而強迫自己去為他們服務。
◎ 窮人不需要我們給予他們同情或者憐恤,他們需要的是來自於我們的幫助。
◎ 不論我們做哪些事情,即使只是幫助別人穿越道路,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把愛奉獻給耶穌。
◎ 如果我們能夠去愛世人,我們就學會了如何去服務世人。
◎ 愛的果實就是服務。愛引領我們:「我願意服務眾生。」服務的果實則是平安。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致力於個體與群體的平安。
◎良知是一面鏡子,它能夠反映我們的人性,也就是當我們自我檢視良知時,就等於在進行一項人性檢驗,我們要讓這樣的一面鏡子忠實地映照自己的人性弱點。自我檢視還可以認清自己的罪過,有助於我們的心靈復甦。
◎ 如果我們要成為有愛的人,首先就得愛自己的家人。
◎ 我們想要得到別人的寬恕,就得先學會寬恕別人。假使我們不懂得這個道理,就很難向那些造成我們傷痛的任何對象說:「我原諒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