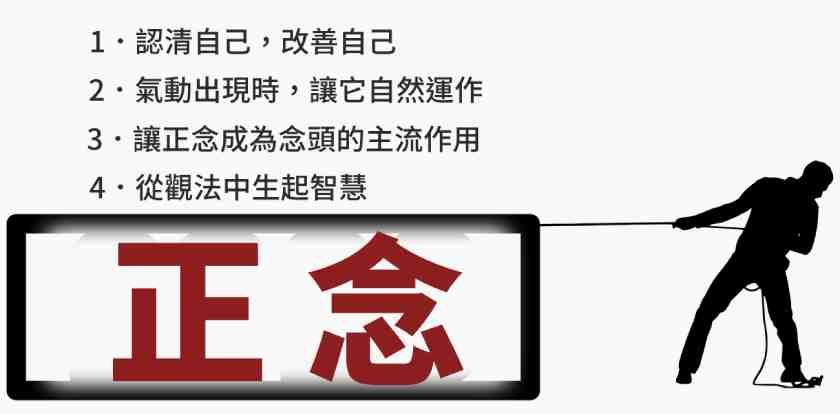
在妄念不斷生起時,會看到讓我們十分困擾的心事,或是讓我們留戀的過去。這些都會緊緊地拉住了我們用功的心。困擾的心事不斷湧現時,會起瞋心;讓人留戀的過去一直浮現時,會起貪心,甚至產生更多的幻想。挫折的念頭出現時,我們也會想用一些方法來克服。實際上這些挫折在現實生活中已經發生了,會成為妄念,是因為當時我們多半是用所謂的「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來處理,並未真正地疏通。
認清自己,改善自己
在魯迅的《阿Q正傳》小說裡,阿Q被人欺負時,可能個性比較懦弱,不敢還手,只好在心裡罵:「今天很倒楣,小子打老子。」在精神上,就覺得勝利了。很多時候,我們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時,也會編造出一套故事來,表示自己贏了,從中獲得一種平衡,說不定這也是一種精神治療的方法,至少不會因此失去生存的信心。就像阿Q在被判死刑時,他想到反正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所以被槍決時,好像還很得意,這也是一種精神上的勝利。

其實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不管是我們貪戀的或是受到挫折的,都是自己的業和報。
從現象上來看,事情已經過去了,應該從無常的角度把它放下。但是,我們不只沒有把它放下,還讓它潛伏在心裡。在用功或平日靜下來時,很自然就會從妄念中顯現出來。顯現出來以後,尤其是一些挫折,因為心裡總有許多不平,所以又編造一些故事來平衡,就這樣持續造作業力,推動相同的果報。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能做自己的導演,因為會發生什麼事不知道,根本無從準備起。但是,如果是編一個故事,主人翁是怎樣的個性,自己就可自由編寫。不過,寫小說的人會發現,寫到某個階段時,故事中的主人翁已不是他能左右的,尤其是長篇小說,寫到後來,它的結局可能不是作者所想像的角色了。
這就是一個因緣的過程,因為不同的因緣在不斷組合的過程,到了某個階段,它一定會和我們原本所計畫或想像的不一樣。如果我們讓它延續下去,就繼續再製造這個因緣、製造動力,「加油」下去,它就動了;這樣一直動下去,就會沒完沒了。因此,為了不再推動它,我們先用止的方法看著它,覺照它的作用,不要讓它再生起來;也可以將它歸類、分析一下,從中看出自己的一些問題所在。比如面對挫折時,我們就可以從中看出自己個性上的一些弱點,因為這些弱點,而不能把某些事情做好。這樣就可以看清楚自己,也看出自己比較深細的煩惱。
很多時候,我們也知道採取某些做法,可以使事情得到圓滿的解決。但是由於煩惱太重,往往顯現出來的是一種慢心,所以常常會出現一種現象,就是寧願錯到底,也不願意調整。因為如果做調整的話,可能會失掉一點面子。生活中有很多這種情況,如果能夠比較正面地看待它們,就會看到自己的弱點。也許我們沒有勇氣接受或改變這個錯誤,但是若能夠從中吸取教訓的話,說不定下次類似的事情發忽生時,就懂得將負面的能量(煩惱),轉化為正面的能量(慈悲)。這些都是我們在觀察妄念時,能夠學習到的。
認清自己、改善自己,就是修行。如果我們以為打坐到最後,忽然發生了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就開悟了,然後整個人就改變了,本來有很多煩惱,全都不見了,這是不可能的。其實修行就是要不斷地調整我們的個性,修正我們的心。我們不要怕挖掘自己的煩惱,也不要怕挖掘自己的妄想,因為挖掘出來之後,才有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另外還要有一個重要的心態,就是真正想修正。有些人可能看出了自己的問題,但是不願意改,認為反正自己用這種方式生活了幾十年,別人也習慣、接受了。這種個性就好像堅固的石頭一樣,如此,修行便只能到某個階段,之後就再也無法提昇了。
有一些經典形容人的煩惱有如金剛般堅固,只有用智慧才能破它。這就是在告訴我們,在修行的過程中,要能夠看出自己的煩惱,然後不斷地改善、調整,才能在真正見到法性時,把煩惱都斷除。
氣動出現時,讓它自然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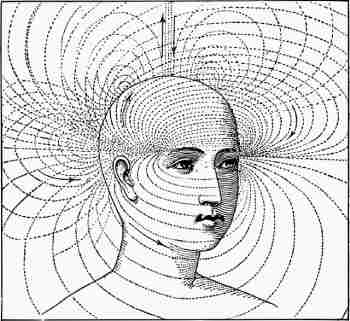
有時我們會發覺修行到了某個階段,就再也無法深入,一直停留在原點兜圈子。
這是因為我們無法將那個堅固的障礙打破,也不願意跨過。比如打坐時,每次一上座就「玩」自己的氣,這個氣又到哪裡、又到哪裡,很開心、很舒服,但是並沒有真正用到調心的工夫,只是調身而已。而且,有時這些氣動已成了慣性,不是自然現象。
我們在運用呼吸的方法時,體内的氣息會發生一定的作用,因為心要調細時,身體必須要相應地調細。當我們把全身放鬆,就會產生這種自體的內在運作,身體毛病愈多的人,可能愈明顯。氣在動時的情形,類似體内的某一種運動,會讓人很舒服,或有某種輕安的感覺。如果我們沉溺其中,而不懂得借助它來加強修行用功的條件,就會停留在這種身體的運作,無法進步。
因此,我不太鼓勵人學了氣功才來學打坐,除非身體的健康狀況真的是太差了,非用氣功治療不可。因為在練氣功之後,很多人容易一直執著於氣的功用與覺受。為什麼?因為身體的健康會改善。但這只是過程,我們要懂得借用禪定的工夫來修慧,否則會停留在調身的氣功;或是修定有成就了之後,停留在定中而忘了更遠的目標。所以在用功之前,這種心理、觀念一定要先調整好。當打坐出現氣動時,就讓它自然地運作。到了某個階段,它的力量可能會愈來愈強,強到無法制止,只能讓它發作;等到它的力量慢慢減弱時,就可以把它調回來,然後讓它過去、放下。
我們的心理調整過程也是一樣,當知道自己的煩惱或問題時,如果不願意把它捨掉,在打坐時,它就會常常冒出來。就好像我們心裡記掛著某件事,不願意放下,它可能就會在夢中不斷出現。如果每次打坐都在想這些事,兜這些圈子,兜到最後只是增加煩惱,自己並沒有改進,來來去去就是這一套。因此,在調心的過程中,要一步一步地上去,一步一步地深入,同時也要一步一步地捨 ── 走向前一步,後面的那一步就要捨掉。
在打坐時,我們常常讓妄念變成一種動力,不斷地推動它。除非覺照的作用很敏銳,專注的力量也很強,能夠守住自己的心,才不會隨著它轉而去驅動它。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我們在覺照的作用加強之後,以正念來取代妄念,比如念佛、念法。
讓正念成為念頭的主流作用

念佛是比較簡單的方法,也就是把佛號的力量不斷地提起來。佛的聖號代表佛的功德、智慧,念佛就是在念佛的功德與智慧。
在經典裡,讚佛有十號。我們在念佛的十號時,即是在憶念佛的功德和智慧,進而生起一種嚮往、皈依的心,我們可以用這個正念來取代妄念。
我們也可以提起一個自己認為比較相應的佛或菩薩的聖號,做為保持正念的方法。有時用功到某個階段,心比較細,用這種心來念佛的話,會發覺佛號很容易就貼住心。平時我們在念佛時,都是散心在念,因此佛號實際上也是妄念的其中一個。雖然它是正念,但是力量不強,所以念佛時常常會發現妄念還是很多。當佛號失去時,我們也沒有覺照,才需要用念珠或某些工具來幫助自己記住佛號。
此外,我們也可以用耳根來聽大眾念佛的聲音,讓它進入到自己的内心,不斷地熏習。打佛七時,在止靜念佛之前會先有快速的念法,也就是一個佛號接著一個佛號快速地念,加強這個佛號在我們意識裡的印象;然後突然煞板,這時會感覺到佛號還繼續在心中響起,這是把外在的聲音轉化為內在的影像。快速地念,是要讓妄念不容易打進來,能這樣用功的話,在那段時間裡便不會失去念佛的心而保持正念。
我們還可以用數的方法來不斷地提醒自己,比如念「阿彌陀佛(1),阿彌陀佛(2)」。在佛號之後把數目字念出來,目的是幫助我們能一直守住佛號。當發覺只有阿彌陀佛,沒有一、二、三時,就表示覺照作用已經被拉走了,心便不容易再專注。這時要再提起來,慢慢地會和數呼吸的方法一樣,數到一個階段非常清楚了,就會一個佛號接著一個佛號;或即使不是故意把它念得很緊,妄念也無法在佛號與佛號之間插進來。一旦數目字放下,就能夠一心地念佛。
我們一開始念佛時,心很容易被拉走,所以還是要靠外在的聲音來守住自己的心。比如和大眾一起共修時,要念出聲音,或是常常聽聞佛號。現在比較方便了,有特別念佛用的機器、卡帶或光碟,可以幫助我們念佛,以後可能還會有更好的方法,這就是從耳根入。在修行的過程中,從耳根入是有作用的,因為我們開始用功時都是緣外緣 ── 通過眼根、耳根、身根;直到覺照的作用加強了之後,才轉化為內所緣。
念佛的方法還有很多,再舉觀佛像。所觀的佛像要非常莊嚴,能讓自己生起歡喜心,看著它,慢慢地將佛像映入到意識裡面。如果能做到閉上眼睛時,佛像就在內心現前的程度,就是「般舟三昧」,也即是所謂的「佛立三昧」,就是佛立在前面,清清楚楚地看到,這是一種定的工夫。但是如停留在那邊,就還不是慧,還需要再進一步。修定可以用這種方法,這是將眼根所緣的外塵,慢慢地轉化為我們內在的影像。
以上這些,都是運用正念的方法念佛。這個正念的方法加強了之後,妄念中那些虛妄、惡念或是煩惱的作用,會慢慢地減弱,因為正念愈來愈凝聚,它的力量也就愈來愈強。那麼在生活中,它就是正念現前,煩惱現前的作用小,正念成為念頭中的主流作用,也就是心的一種主流作用,包括我們的思想、觀念都依它而建立。
從觀法中生起智慧

念法就比較複雜一點,因為佛法中談到各種修觀的方法,其中一些是對治作用,像不淨觀。
它是以外在的不淨相做為觀想對象,甚至有時要去看屍體;慢慢地把這個外相 變成是自己的相,一入定就觀自己的身體腐爛了、蟲出來了、血塗 …… 之類,這可以對治我們的貪欲。如果對自己的身體執著很深,這種觀法有對治的作用。
不過,不淨觀的對治作用有時會偏差。例如有某一種毛病,就對治它;當這個毛病好了,如果這個對治作用不斷加強,它反而會偏到一邊去了。就好像人在生病時吃藥,病好了就不要再吃它了;繼續吃的話,就變成一種病態了。所以在不淨觀的應用過程中,到了某個階段就要調整,比如觀白骨是白的,但不觀它毀滅,而是從白骨轉成淨觀個理是正確的。這種觀法如果能繼續深入,並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話,對因果的信心會愈來愈堅定,所作所為就會符合因果,我們的智慧就會從緣起觀生起來,顯發它的作用。
但是我們在用這些觀法時,最好先將自己的心安住下來,才能發揮它們的作用。因為如果心不能專注,看到身體腐爛的現象,一方面會恐懼,另一方面可能會想厭離、排斥它。有這種心態的話,它就映不進去。因此,要用一種比較中性的態度來觀它,心要能夠攝住,然後用眼根看,把它映入,才能從過程中起不淨相。這便是假想觀。慈悲觀也是假想觀。用這個觀法時,是觀我們的父母或最親愛的人,觀到他們歡樂的相而生起慈心。
觀想就是運用佛法所提供的種種方法,以加強心凝聚的作用。等它的作用強到能夠把正念提起來時,妄念或煩惱的念頭就會慢慢地減少,力量也會減弱。這些觀法從起修到平衡都有一套系統,它們多是讓我們生起厭離的念頭,幫助我們把執著自己的色身或世間的種種欲望,都能捨下。
在佛法裡面,最主要的觀想是因緣觀。對不明事理的人來講,它是很好的對治方法。從妄念中,可以看到它的因緣。我們常常見不到妄念的因緣,是因為逃避不敢去面對。如果真正去面對的話,會發現所有出現的妄念,一定都是自己的因果、業報,也就建立了正確的因緣觀。
佛法要我們正見善惡、正見業報、正見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的流轉,這些因果或緣起的道理,從妄念中就可以看到;或是從理分析妄念的實際内容是什麼,這就是因緣觀。觀緣起時,實際上就是要幫助我們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觀念,以正確的觀念來看待生活。
從妄念中看到因果,明白了緣起的道理,就知道假如要改變它,必須先從哪一方面下手。所以修行到某個階段,見到了自己的缺點和煩惱時,如果願意調整的話,就能製造改變的因緣。剛開始調整時,進展會比較緩慢,或效果不是很明顯。但是,當這個作用不斷地加強時,調心所產生的效果,就會在生活中漸漸地顯現出來。如果內心有調整,這個就是因果,也是一種緣起觀。不過這種緣起觀是現觀,它的背後需要有理做為基礎、依據。
現觀妄念,是從妄念中印證所了解的理,或依所了解的理來分析妄念,從中知道這 個理是正確的。這種觀法如果能繼續深入,並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話,對因果的信心會愈來愈堅定,所作所為就會符合因果,我們的智慧就會從緣起觀生起來,顯發它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