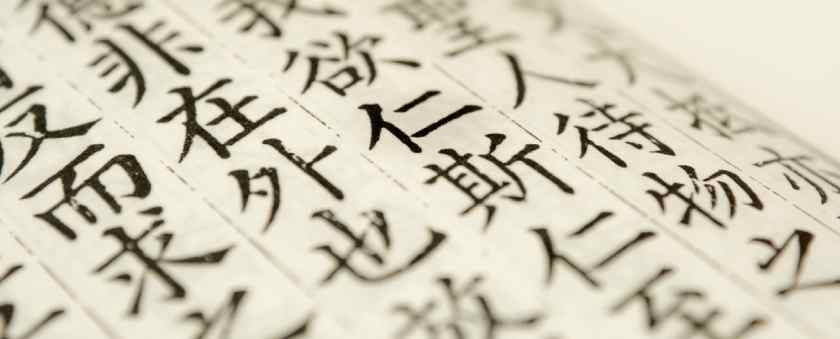
蒲基維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資深國文教師
教育部國文學科中心核心種子教師
「教育是不斷刺激創意與開發,而不是箝制思考與縮限人生。」如果在這點上有共識,文言豈止是文言呢?第一線教育工作者如何教導文言文?蒲基維老師認為,高中國文老師們承擔的,不是化解文言文的政治辯論,而是如何將千百年前的古文精髓,與當代學子做出連結,並且讓文言文成為生活的素材。
每年考季,高中課綱文言文的比例問題,總時不時在新聞媒體上熱議;在政治、教育、文化領域中,也常陷入不同立場的激辯。有人會說,學習文言文,孩子的國文能力就提升了嗎?有人也說,以前默背課本覺得很痛苦。不過,這些疑問,似乎模糊了學習文言文這件事情的重點。
身在教育現場最前線、與「文言文」這個議題最切身相關的高中國文老師,又是抱持著怎樣的看法或觀點呢?
傳世經典的普世價值
我是一個教學超過二十年的高中國文老師。對我而言,文言文教學(或說教材)比例從來不是問題。如果這篇文章是經典,禁得起時空的考驗,不只文言文,即便五四時期的很多白話文,比如說朱自清的〈背影〉,它是公認的經典,只要是經典的文章,我們有什麼理由不教?
千百年來,經過戰爭、經過時空變遷、經過很多政治、很多威權的打
壓,很多經典仍在中華文化裡光采輝耀,它們依然可以流傳到現在,不是只有臺灣,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甚至於馬來西亞的語文教材裡面,都有〈赤壁賦>、<岳陽樓記>、<師說>等經典文章。
這些文章之所以會被列為經典,是因為它早已經是整個中華文化圈的普遍共識。臺灣的教育改革已經經歷了二十幾年,現在的國文老師,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中文專業;但是,在教改的過程當中,臺灣教育反映了某些社會的價值觀。國文屬於語文、文史類科,相較於數學、物理、化學甚至於英文,在實用性上感覺相對是比較弱的。所以,在高中的教學現場,有些數理老師,有時候在話語當中,可明顯看出一絲絲瞧不起國文老師的意味!
我的職涯規劃,除了教書之外,也很希望能夠繼續進修;也因為這種有形、無形的刺激,讓我提早實踐攻讀博士的想望。所以,在教書第二年,我就考取了臺灣師大的博士班;我的碩士論文是研究古典散文,博士論文我持續地往章法風格學去研究。
探討風格,難免會涉及到「陰陽剛柔」的變化;而所謂「陰陽剛柔」則可以上溯到中國古代關於《周易》的陰陽變化,以及《老子》的「守柔」哲學。在《周易・易傳》提到了「太極生兩儀(陰、陽),兩儀生四象(太陰、少陰、少陽、太陽),四象生八卦(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卦生萬物」;相傳,周文王後來又將最初的八卦推演為六十四卦。
八卦、陰陽與螺旋
據《易傳.序卦傳》所言,六十四卦代表天地萬物發展的順序。六十四卦裡的第六十三卦是「既濟」;所謂的「既濟」就是,事物到達很圓滿、很完整的狀態。可是,到最終第六十四卦,卻又叫「未濟」,意思就是尚未圓滿。宇宙萬物的事物,就像這樣從圓滿到不圓滿,我們可以在很多自然現象中找到例子,我們常看到的月圓、月缺即是如此。
這種循環的概念在《老子》裡面也有。據說,《老子》談到的「無」的概念,比《周易》的太極要更早、更原始。在宋代的理學裡面,周敦頤也講到了;《周易》談到了太極,可是在太極之前應該還有一個「無極」,所以周敦頤講到「無極而生太極」。這「無極」的概念,應該就是從《老子》而來的。
《老子》的語言是很弔詭的,「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事實上,「無」跟「有」的概念就是一體的兩面;「無」代表的是一種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有」則是我們所看到的現象界。
《老子》談到宇宙萬物的運行,「萬物負陰而抱陽」—— 萬事萬物的生長,通常就是從陰生長到陽,它傳達的就是陰先於陽的概念。所以,《老子》其實是一種「守柔」的哲學。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所謂的道,其實就是包含著無、有的概念。「一」,其實跟《周易》的太極很像,就是萬物終歸於一。「二」,其實就是《周易》講過的陰陽。
所謂的「三」,其實就包含了純陰、純陽,跟陰陽所調和出來的 「和」,所以《老子》原文才會接著說:「沖氣以為和。」這個「三」其實就是「陰、陽、和」三種狀態,因為這三種狀態的比例不同,所以產生出了萬事萬物。
宇宙萬物,難道說在「三生萬物」之後,就無限擴大、無限擴張嗎?其實不然,《老子》還含有「物極必反」的哲學。我們看宇宙萬物的運行,好像是在循環,但它其實是一個極其緩慢的循環,是一種向上提升的狀態;這種狀態不該稱「循環」,而應稱之為「螺旋」。
有趣的是,大自然裡也有許多「螺旋」。例如,美國科學家便在一九五二年發現 DNA的雙螺旋結構。我們常看到的颱風,它也是一個螺旋。甚至於宇宙當中的太陽系,也可以看到這種螺旋現象。
儒家的人際觀
由此來看人類理解宇宙的方式,大概有兩種途徑,一種是求同,另外一種就是求異。一般而言,中國古代以及東方哲學比較注重「求同」,也就是注重統整跟貫通,比如以陰陽、八卦說明宇宙萬象;而西方科學注重分析,就是「求異」的科學,注重於實證。
然而,臺灣目前有太多現象是陷入了求異的輪迴,例如:政治觀點不一樣 —— 我是藍的,你是綠的;文言文跟白話文不一樣,不要文言,只要白話 …… 可是,事實上真是這樣嗎?
其實,文言、白話在演變的過程中,只是口語跟書面語的差別。我們講話有時會夾雜「啊、這樣、那麼、這麼、那個」等字眼,但並不會把這些都寫入文章當中。對比口語,書面文字是相對簡練的;我們的老祖宗以前文字量少,當然用字會更形精煉。可是,即便文字少,但它涵蓋的思想哲理是非常大的。
到語言文字發展到一定成熟度,從宋代開始,白話文就在持續發展。唐宋時期的語言系統,跟元明清以至於現在我們講的國語,語言系統是不一樣的,但我們都統稱為白話,這也是某種「求同」。
怎樣把這個「求同」的模式落實在國文教學上?這是我個人幾經思索的。譬如,我們常聽到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也就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四部經典。要如何帶著學生讀這些文化教材?我想到的是,國文老師要避免自己講得很心虛;所以,首先必須要從經典中尋求道德生命的實踐,不能講一套做一套。一直到現在,我都還很努力地在追求道德生命;我認為的道德,我認為的正派,必須要實踐在我的生命當中,才能說服我的學生。
我對孔子的思想做過統整,從《論語》原文裡去找。孔子對曾子說過:「吾道一以貫之。」又問:「你懂嗎?」曾子就說:「我懂啊,老師我懂。」老師一走開,其他的同學就問曾子:「你懂什麼?老師到底在講什麼?」
曾子就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就兩個字,「忠」跟「恕」。他進一步解釋什麼叫作「忠」:「忠」就是盡己,盡一己之力,努力地做好一切;所以,我們可以忠於自己、忠於朋友、忠於社會、忠於國家,盡一己之力把自己做好。
「恕」又是什麼?「恕」其實是會意字(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組成一個新字,並具新的意義),也就是「如+心」,亦即推己及人。
忠恕之道,其實就在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我們常講,孔子的思想最終會歸結到一個「仁」字;這個「仁」,其實就是「二人」。儒家的思想,就是在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歸納為朋友、夫婦、父子、君臣(國、民)、兄弟,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五倫」。整個儒家體系的思想,就是在建構人與人之間、也就是人際之間重要的倫理關係,這樣社會才會平和。
如何鑑賞文章
同樣地,我們也能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讀懂文章想要告訴我們什麼。
每次教高一新生時,我都會問他們:「你們國中的國文課都在學什麼?」很多學生都說背解釋,還有很多國學常識、詩詞……總之就是「老師要我們背一堆、讀一堆文章」,好像念國文就是要學、要背好多東西。那麼,究竟什麼是「國文」呢?
國文,顧名思義就是「本國語文」;當它用於教學,就是以文章為核心。當我們挑了好幾篇的經典文章 —— 不管是文言還是白話,因為文章是核心,而文章是人做的,所以我們就必須知道這個作者的時空背景,透過時代背景了解作者個人的際遇,就會延伸出很多「國學常識」。我們常講知人論其實,我們要通讀文章,就不能不了解作者其人。
此外,可藉由文章的字形、字音、字義來理解文義;文言文因為時空的差距,更必須要讓學生知道,某個字詞的古今不同。事實上,現在的高中國文課本編得非常清楚明白,不管是註釋還是翻譯,其實學生自學就可以了,國文老師也愈來愈少花時間專注於字音、字形、字義的解釋教學。
取而代之的是,我們要跟學生談的,比較屬於是文章的意象、文章的遣詞造句、甚至於文章的謀篇布局,以及文章的內容主旨是什麼?它要告訴我們什麼?
文章,其實透顯出一種文學藝術。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風格的鑑賞去評斷、去分析這篇文章,它的藝術價值在哪裡?所以,在高一新生的第一堂國文課,我通常至少會花半節課時間跟學生分享,希望學生去摸索、掌握這種風格鑑賞的態度,用這個態度來學國文,你至少不會迷失;要不然分量這麼多,最終若像背英文單字一樣,恐怕會覺得索然而無所適從。
我的博士論文是寫章法風格。何謂章法?一篇文章涵蓋了形象思維跟邏輯思維;所謂的形象思維,是屬於比較主觀成分的想法,而邏輯則是屬於客觀的。主觀的成分包含了意象、詞彙跟修辭;客觀的邏輯,包含語言的邏輯叫「文法」,篇章的邏輯就是「章法」。
章法風格是「辭章學」的一部分,辭章學的研究早就把章法風格系統化了。在辭章學體系裡,便可整理為形象與邏輯思維的架構,然後用來分析「文章」—— 可以是一首詩、一篇白話文或文言文。
用文章穿越古今
例如,記得我在國中時背過杜甫的詩〈旅夜書懷>,這首詩是他在五十七歲流浪夔州時所做。為躲避安史之亂的兵禍,杜甫帶著一家人從四川逃難出來,逃到湖北的夔州。那時候住在船上,住在岸邊,流離失所;所以當他看到了「細草」,看到了「孤舟危檣」,看到了「星垂」,看到了「月亮」,他的心中有了想法,就把這些景物聯繫起來,勾勒出前四句詩: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
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這些景物的描寫,每一樣都是有具體意象,都是有情感寄託的。所謂「詞彙」,就是用文字符號去表達意象。從篇章結構來看,前面四句是寫景,後面四句則是抒發自己的感覺: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在這裡,他用了一個激問句,這個激問句就是修辭。而且他用了一個譬喻,在詩的最後兩句:「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形容自己像沙鷗一樣到處流浪。這種譬喻、這種取材都非常傳神。
由景而情的這種結構,在唐代的律詩裡面是很常見的。閱讀跟寫作,是一個順向跟逆向的關係,彼此之間是互動的,這是辭章學的統整。
除了統整之外,求同的觀念或模式很注重貫通。以《詩經・蒹葭》為例:「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這個景致(或說意象)多美啊!這種對於愛情的追求,相信古人跟現代人是毫無二致的。
再舉一個例子:〈赤壁賦〉。蘇軾當年寫〈赤壁賦〉的時候正被貶官到黃州,在中元節過後乘舟遊赤壁,他自抒懷抱,提出了一個變與不變的道理:人在困頓的局勢當中,該怎麼自處?要怎麼轉念?
所以,透過詩詞文章,你可以跟古人暢談,可以向古人叩問人生的問題,就看你用什麼方式親近經典。
以古今人物為伯樂
據統計,有八成以上的老師,正嘗試或已嫻熟運用翻轉教學、學習共同體或分組合作學習;現今的教學方法,已經與以往大不相同。每次參與教師甄試,我總會對應試的新進老師提問:「你會怎麼樣把古文延伸到現代?」我以為,這對學生是非常重要的。
我到大學兼過課,開的是「史記」這門課。為了教學而重新細讀《史記》時,發覺特別喜歡一個人 —— 秦穆公,因為跟我高中時讀的〈燭之武退秦師〉相呼應;透過這篇文章,讓我重新認識他是一個怎樣的國君。
秦穆公二十歲就登基了,一心想要入主中原、稱霸中原,他要學齊桓公;可是,在西方的秦國又被晉國給擋著。當時晉國其實是一片內亂,於是他想盡辦法干預晉國的內政,扶植了晉惠公,又扶植了公子重耳 —— 就是後來的晉文公。
沒想到,晉文公主理晉國之後,兩年之内就稱霸中原了,這讓秦穆公心裡很不是滋味。在整個過程中,秦穆公不斷地動用資源想要染指中原;可是,終其一生,他只能夠面對西方的戎狄,稱霸西戎。
看到這裡,可能你會心想,這秦穆公就是個失敗角色,為什麼有人會欣賞他?但我是從他「能知人」這一面去理解、欣賞他。
我在二〇〇四年取得博士學位,曾經投過很多履歷,想去大學任教,可是這個夢想一直未實現;漸漸地,這個在大學執教鞭的夢好像也不再那麼非得實現。我後來把自己這段生命歷程,融進秦穆公的歷史故事,寫成了一篇文章,也設計了一個作文題目:「以古今人物為伯樂」,就是希望同學們,古人也好、現代人也罷,從中去尋找你人生當中的伯樂。
你的伯樂給予你什麼樣的啟示?我用二千八百多字的文章,在課堂上用二十分鐘,一字一句慢慢地朗讀給學生聽。我描述秦穆公在看到晉文公稱霸中原之後,心中有一種無處訴說的糾葛,我試著透過文章去梳理面對這種人生際遇的心情;後來發覺,古人心中的糾葛,似乎跟我當年現實生活中的際遇,有一點點契合。
以文章、以人物為師
記得我當時在課堂上說著秦穆公的故事,心中其實也隱隱作痛;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某些作為、某些想法,就跟我這高中老師夢想到大學任教結果受到阻礙的心底糾結一樣,其中似乎有著相契之處。
當學生聽完之後,大概有將近三十秒的時間,課堂上鴉雀無聲;隨著時間悄悄過去,不久後響起了一片掌聲,學生們還紛紛舉手發問。
透過這樣的引導,我希望學生去找到人生的伯樂;而這個人生的伯樂,就在文章當中,就在今古文人當中。學生也因此在寫作上,有了滿強烈的回饋與回響。
有一個男生是以吳寶春為伯樂。他原本是一個很沒有自信的人;讀了吳寶春的自傳之後認為,吳寶春儘管學歷不高,仍創造出不凡的成就,因而從中找到了自我與自信。
有一個同學是以賴東進(《乞丐囝仔》的作者)為伯樂。這位同學是個嬌嬌女,她的父親是職業軍人,叛逆期的她經常不服管教;在讀完賴東進的故事後,對比於書中主角悲慘的生命遭遇,她覺得自己實在無比幸福,應該要好好定下心,改變自己的性格。
另外有一個同學,原本母女的關係不好,在讀了龍應台的《親愛的安德烈》後,開始懂得梳理心情思緒,並省思該怎麼樣跟母親對話。還有一位同學是以補教名師高偉為伯樂,因為高偉的故事讓他認為,補教名師有些是滿拚命燃燒教學熱誠的。
課堂上,同學們各自找到不同的人生伯樂,在寫下自己心裡的話時,可以更加深刻。
大塊假我以文章
每到畢業季時,我也將文言文結合了生活。幫學生簽畢業紀念冊,最常見就是「鵬程萬里」、「一帆風順」;可能國文老師多背一點書,頂多也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或者「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之類;坦白講,都是些舊調。
我就告訴畢業班同學,我送給每個人一副對聯,用對聯式的題詞,將他們的名字鑲嵌在對聯當中。例如,有位女生叫「羿慈」,我送她的是:「羿撼縱橫氣,慈擁天地心」。這個女生平時大剌剌的,長得很漂亮,現在當空姐;我當時寫這幅對聯,是期盼她有縱橫天下的豪氣,但也要有擁抱天地的仁慈心。
還有一位外籍生Rachel,她的中文名是睿琪,媽媽是臺灣人,爸爸是美國人;她在臺灣待了一年,我教了她一年的華語。她的中文程度非常好,當時送給她的對聯是:「睿氣虛懷知天地,琪心盈袖識古今」。
這些與學生的互動設計,結合了國文的對聯題詞教學,都變成我的教材,剖析古人對生命的觀照,也延伸到現代的人性關懷。透過經典文章,看古人情意感受,也觀照到宇宙的運會生滅。我們帶讀章回小說或小品文的時候,也會給學生經驗到更高、更深的美學鑑賞。
文言文是我生命蛻變的橋梁。作為高中國文老師,所要承擔的並不是如何化解文言文的政治討論,而是如何讓千百年前的古文精髓,與當代孩子做出連結,並且讓文言文成為生活上的素材。
時代在變,教法也在變;或許,啟發孩子在生命、生活中學習,才是真正有效的學習方式。教育是不斷地刺激創意與開發,而不是箝制思考與縮限人生;如果在這點上有共識,文言豈止是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