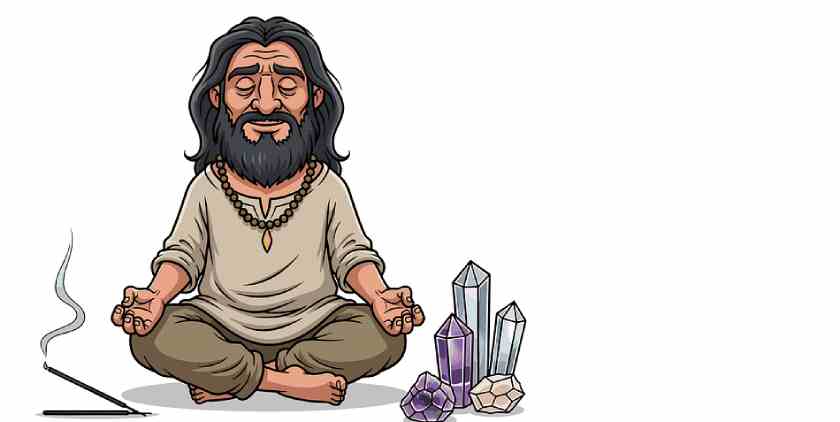
大卿 弘法師開示
我們在觀呼吸的時候,就是在找觀呼吸的著力點,最省力的點,最能由衷呼吸的那個是什麼?去尋伺、體會,體會以後再尋伺,慢慢的尋伺體會就越來越細,呼吸也會越來越細,心就越來越靜,心很靜就會有歡喜心生起,那種喜是一種開心,心會開,那種喜好像起雞皮疙瘩一般,心開以後,就有一種很平靜的樂,一種無所求,無欲念,世間不過如此的滿足感,有喜有樂,心就很定,跑不進一絲雜念,就叫一心。
常常保持這個狀態,有尋、伺、喜、樂、一心,無論行、住、坐、臥,都保持這種正知正念,常常保持禪緣。雖然不一定要進入初禪,但是常常都有初禪的品質,這樣就很容易進入剎那定。
剎那定的特色是「空」,是根境離繫,根境猶如脫鍊。本來六根與六境像鏈條般連在一起,現在根、境間有空,如鏈條鬆掉了,那個鬆掉的感覺叫「空」。那個感覺是,你在看東西,眼睛是眼睛,東西是東西,眼睛雖然看到,耳朵雖然聽到,但不會被拉,就不會產生引力和壓力,所以,那裡面有很大的空間,一種近在眼前,遠在天邊的距離感,空間很大很大,空間很大的意思就是「無礙」。
色境本身是我們去尋伺才有的東西,我們若沒有尋伺,沒有用力,有看到也等於沒有看到。不是眼睛在看,是心在看,看到而不能不看叫被拉去,叫做「結」。我們如果沒有結,就是沒有被拉,因為我們的心很靜,都在一心裡面,知道心的注意力要放在那裡,眼睛不會亂看,耳根也不會亂聽,六根收攝得很好,雖然一切色境,近在眼前卻無礙,好像我們看著天上的星星一樣。若不在剎那定中,有可能感覺東西很礙眼,會生出一種棄嫌心來,若在剎那定的狀態,則不但沒有棄嫌的感覺,而且還能欣賞,猶如欣賞天上的星星,那一種遠在天邊,心與境沒有關係,沒有照應,心量非常開闊的一種空的感覺。
比如我們的手去摸到一個東西,你對那個東西沒有愛著、也沒有礙著,雖然是手摸到,心卻是有無量的空間,你不是摸到東西,而是摸到空。所以,聽到聲音,聲音是空,看到東西,東西也是空,那就是剎那定。未到地定是在講有尋有伺,有喜有樂,有一心,有些時候沒有具足五項,或是沒有很熟練,也可以算是未到地定。
(一) 色界定
初禪必需要五禪支具足,而且要在這五項裡面轉向自在,隨時能進入尋、伺、喜、樂、一心。比如現在開始尋,就是尋,不會丟掉,伺就是伺,然後很快就能進入喜樂一心。入初禪後,必須能夠要入定就入定,要出定就出定,在五項功德裡轉向自在,但不是跳來跳去,而是進入時由尋、伺、喜、樂、一心進去,叫入定自在,出來時是一心、樂、喜、伺、尋,這樣出來叫出定自在。能在這五項裡轉來轉去,你能作意喜就是喜,作意樂就是樂,然後很清楚的感覺什麼是喜,什麼是樂,什麼是尋,什麼是伺,什麼是心一境性,叫轉向自在。而且還要能夠看到尋、伺、喜、樂、一心的缺點,叫反觀自在。並且初禪能有持久性叫在定自在。有這五種自在才叫得初禪定,才叫得定。
得定以後,再來修二禪,二禪是看到尋伺的麻煩。因為喜是尋伺而生,到最後,喜不用尋伺而產生,但那個喜更強。二禪的喜比初禪的喜更強,感覺尋伺也是一種用力。當熟練之後,會感覺這個尋伺的用力是多餘的,自然放下尋伺,放下以後,喜樂再度湧上來,喜樂、一心很強,這叫二禪。
在二禪裡面,整個世間的感覺都好靜,那個靜的感覺,不一定是外面無聲,而是聲音完全無礙,那種感覺不只是遠在天邊,在聲音中卻感覺到萬籟俱寂。一般人如果突然進入二禪,會嚇到,以為自己耳聾聽不到聲音,那不只是外面無聲,連裡面也是無聲,內外無聲、萬籟俱寂,那就是二禪。所以喜心很強,心開的感覺,越進去就越強。
甚至於初禪本身有好幾個層次,不只是一個層次。二禪本身也有好幾個層次,雖然特性品質是一樣,但層次卻不同,強度也不同。所以不是每一個人的初禪、二禪都一樣,不是每一個人的三禪都一樣,那裡面又有強度的不同。
三禪就是說,他感覺喜也是一種不安,連心開也是一種不安,他看到這裡面也帶有某種程度的興奮,他看到這也是一種礙,是多餘的用力,所以他連喜都放下,樂的感覺就更強,這是就二禪和三禪來比較,三禪的樂比二禪的樂更強,三禪有更不同的安樂感。這個樂是安樂,不是快樂,快樂有一種緊張在裡面,安樂卻是沒有緊張在裡面,這是出世間、出欲界的一種樂,不是欲界樂,欲界樂有緊的性質在裡面,出欲界的樂,是一種安樂、滿足的感覺,感到「就是這樣」那種無欲無求的滿足感。
有了這個安樂的感覺,你的心就不會丟掉,你會感覺不是你離開欲望,而是欲望離開你,即使你想要有欲望,你也感到欲望離你遠遠的,心寂靜到根本沒有雜念。
四禪就是連樂都沒有去感受,進入一心,息住脈停。在四禪的一心裡面,看到所有的境界只不過是一面鏡子而已。你有取相,才有境界,你若沒有取相,就沒有境界。因為我們所有的境界都不過是一個相而已,只是我們的取相、取角,我們從那一個角度去看,就成什麼境界。
從初禪到四禪的好處,就是我們的心已經很柔軟。很柔軟的意思是它能靈活取角,它要取什麼相,就取什麼相。他看色界,色界不過是我們的取相,它也是空,並沒有境界,如佛陀所言:觀色如聚沬,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時焰,諸行如芭蕉,諸識法如幻。看到五蘊是空,他看五蘊的時候是無礙。
他看到五蘊是一種引力,他把這引力當作一種提醒,把所有的苦,無常都當作一種提醒,所以,他看到無常的時候,他不會抗拒,看到颱風、地震時,他不會覺得意外。他看到五蘊是一種引力,他會接受這引力,看到而不去抓,這樣就不會形成引力之後的壓力。
你去抓境界,是因為你被那個引力拉去,你去抓色蘊的某一個層面,某一個相;去抓受蘊的某一層面,你要樂受而不要苦受,你有愛著就有礙著。所以如果你不去抓,就不會被引力拉去。被引力拉去就是魔,佛陀用魔這個字來比喻。包括六根去取一些顛倒相,這個取相就是著魔。著魔不一定是你遇到了魔魅才是著魔。嚴格的定義裡面,六根取顛倒夢想就是著魔,著魔就是不能自在,不得自在就是著魔。
所以,我們若能看到色界只不過是種種蘊,是種種引力與壓力的合成,所有的界只不過是這些東西,沒有境界可言。為什麼我們會感覺裡面有東西,因為我們有欲望,所以我們感覺那裡面有東西。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把它看得透透徹徹,就會感覺那裡面實在是沒有東西,這樣就會進入無礙的世界,即是空無邊處定,看到境界只不過是一個相而已,看到境界裡面無相可取,根本沒有境界可取。
(二) 無色界定
進入空無邊處定,走過鏡子前面,你沒有看到人影,因為你不取人相、我相,所以你就變成隱身。在無色界的空無邊處定,你會真正看到自己消失。為什麼會無相?因為你不取任何相,不想要自己像什麼,成為什麼,你不認為自己是什麼,有什麼。
講我能、我是、我在、我有…… 一種我慢,那個我慢還要自我膨脹才能夠繼續下去,這個相很有限量,是一種束縛,是一種苦。我們若看不到相是一種苦,就會不斷的取相,認為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你把我當做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們每一個人對自己都有很大的身見,對別人也有很大的身見,我們都無法「空」。「空」在世間所展現的,就是慈悲喜捨,人家講你什麼,都不要緊,因為你什麼都不是,所以你就什麼都是。我們能夠真正無相,好輕鬆,沒有負擔。有相就有負擔;有身見就有負擔;身見越深負擔就越大。
我們要做一個新的人,把自己的過去全部歸零,對世間毫無成見,真真正正把世間看成零。我不認識你,你不認識我,永遠都是一個新的人,一切重新看待,從現在起,我只要對人好,不對人不好,這就是一個新的人。
如果進入空無邊處定,就會看到這個空,看到這個空也只是我們識的認識,看到空無邊處也是一種夢想,一種取相,這樣就進入識無邊處定,這都很快的,除非你去黏著,若沒有黏著,它馬上就過境,這就是識無邊處。在識無邊處看到識也沒有什麼東西,就進入無所有處。
由空無邊處,進入識無邊處,再進入無所有處,看到無所有處也只是一種相而已,還是有分別,就進入非想非非想處。進入非想非非處,就是無色界的取相很靈活,靈活以後那個很微細的我沒有出來,就會進入受想滅定,這就是四禪九定的第九定─受想滅定。這是真正的心行處滅,真正念頭的止息。
禪宗所講的「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嚴格來說心行處滅,就是受想滅定。但禪宗所說的心行處滅,只是剎那定,不是真正受想滅定。這四禪九定的第九定,如果還有「我」的感覺是不能進去的,有微細的「我是」或「我進入」,有這個微細的「我」是不能進去的。進入受想滅定,是出來以後才知道自己進入受想滅定。這個不知道,不是說真的不知道,而是沒有那個我進入受想滅定的念頭,進去就只是進去,知道進去,但沒有我進去那個「我」的感覺,沒有我在第九定裡那個「我」的感覺,但是知道自己在那裡,卻沒有「我是」「我在」的感覺。
那個我是、我在,是一個很微細的想,受想滅定最主要在講「想」。無色界的定是在講「相」。初禪到四禪是在訓練心意一個一個放下。無色界是取相,把相舉起來的意思。一個是舉,一個是放下﹙止﹚、一個是捨,這是修行必須要有三個基本的相。
捨是一心,萬緣放下,超越一切,我們若能一心就會收攝,有收攝就有擔當。擔當在無色界來說是把相再舉起來,由一心進入空無邊處,去看到色想、看到色界的相是一種礙,進入無色界就是看到色界有空,所以它所用的方法就是不去取相。
所以有舉有止,才能舉止得宜,舉止得宜要以捨作基礎,我們遇到境界,我們對世間的態度是由這裡出去的。出去就是承擔,若有困難,就再收攝、再捨,捨了以後又再收攝、再承擔。這是一個人生過程:承擔、收攝、捨;捨、收攝、承擔,來來去去,沒來沒去、「沒代誌」﹙台語﹚。
附錄:安息日
外國人把禮拜天翻譯成安息日,很有意思的,用一個息字,息就是呼吸,好好安住自己的呼吸,安息日。佛教講的布薩日,布薩日就是一日禪,也就是現在流行的一日禪。西方宗教講禮拜天就是安息日。安息日在回教是禮拜五,猶太教是禮拜六,基督教天主教是禮拜天。
安息日是人神溝通日,這一天絕對不做生意才叫安息日。不但不上班,全部的商店,全部的百貨店都關門。五十年前歐洲的安息日做得很好,你在禮拜天出去買東西是買不到的,但你可以去猶太教的店買。禮拜六猶太教放假,猶太教的店一定是關門的。現在你去阿拉伯國家,禮拜五一定關門不做生意,禮拜五是買不到東西的。
安息日真的是人神溝通日,這一天是真的放假。放假很重要的是不生產,不生產很重要的意思是不破壞,因為有生產就有破壞。譬如說,你種田,種田本身是生產,但是破壞土地,所有的生產都隱含破壞,對人類來講是生產,對世間大地來講是破壞。安息日重要的意思,譬如說以前農耕,種了七年,要休耕一年。如大學教授有Sabbadical,做了七年教授,就要休息一年。一個人勞動七年,也要像大地一樣休息一年,人是很需要休息的。
離境也是一種休息,不要逼得自己喘不過氣來。布薩日原來一個月有四次,後來改成一個月二次,布薩日跟安息日意思一樣,等於這一天是休息日不上班、不做生意。如果全世界都有安息日的話,這個世界會不一樣。真的只是這一天就能改變世界。你可以想像,有一天,人們都待在家裡,人神溝通,很安靜,去感覺這樣的世界。
我們看看現在的社會,三百六十五天車輛到處都是,為什麼不肯休息?我們真的需要這麼忙嗎?真的沒有能力七天休息一天嗎?真的非這樣賺嗎?做牛做馬,真的非這樣子嗎?佛洛姆寫過一本書,呼籲全世界要恢復這一天,他非常提倡安息日,但沒有人在聽。
佛教也要提倡恢復布薩日,但是幾個人在聽?只有從自己做起。你就是世間,你就代表世間,要別人做不如從自己做起。所以,依遠離界,我們要想到布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