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因緣.別因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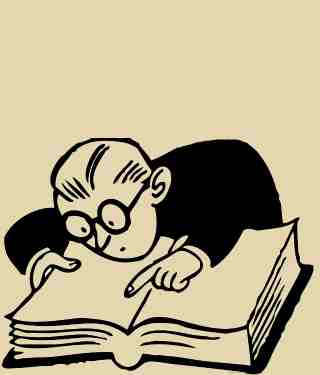
甲初 總釋名題
甲二 起教因緣
甲三 藏乘攝屬
甲四 歷明傳譯
甲五 別解文義
佛教中有一句話說:「法不孤起,起必有由。」世間一切事物的發生,都有其因緣,更何況是至高無上的佛法。世尊講經說法,有其總的因緣與別的因緣。
總因緣 總因緣是佛的一代時教,四十九年中,講經說法的緣起。世尊的講經說法,無論是說小乘法、大乘法、漸教法、頓教法,無非是為了闡明佛法,度化眾生,而所闡明的道理,就是佛的知見。因為眾生迷不自知,所以世尊就乘機應世,為眾生「開示」,使眾生能夠「悟入」佛的知見。《法華經》說:「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如來是為了度化眾生的這一大事因緣,而出現於世間的。茲將「開示悟入」略釋於后。
一、世尊是為「開」眾生佛之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開」是打開,就是世尊為了要開啟眾生本所具足的佛之知見,使眾生能夠得到清淨,因此出現於世間。佛的知見就是眾生六根中本所具足的見、聞、嗅、嚐、覺、知之性,這六根中性就是佛性,是人人本自具足的。但是很可惜的,卻被埋沒於塵勞、煩惱染污之中,因此雖是本來具足,卻是迷而不自知。所謂開,就好像一間倉庫,藏有珍寶,可是卻被一層一層的門深鎖著,唯有把一層一層的門打開,才能看到金銀財寶,這就是「開」的意思。世尊為了開啟眾生本具佛性,使眾生遠離垢染而得清淨,所以出現於世間;這就是世尊出現於世間的第一種總因緣。
二、世尊是為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示」是指示,就是世尊為了要指示眾生本所具足的佛之知見,所以出現於世間。在迷惑中的眾生,都以為佛性是唯有佛才有的,眾生沒有份,而不知人人都有佛性,因此世尊便先說出每個人都有佛性的道理。更進一步的指示出,佛性就在眼根見色、耳根聞聲,乃至意根能夠了知法塵的見、聞、嗅、嚐、覺、知的六根之中,見、聞、覺、知,無一不是佛的知見。「知見」二字,雖然只是把最後意根的「知」,和最前面眼根的「見」合起來,叫做知見,其實是包括六根中性。臨濟祖師說:「有一無位真人,在汝諸人六根門頭,放光動地。」這是說明佛性在六根中的妙用。
這部《楞嚴經》,是從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提示佛的知見,就是告訴我們,在六根門頭具有佛性。我們眼睛所看,耳朵所聽,都是佛性的作用,既然是這樣,為什麼我們仍然淪為眾生呢?因為六根中性雖然就是佛性,但是這佛性卻被一層層的煩惱覆蓋住了,所以不能發揮它的作用,也就是因為佛性的功能透過煩惱妄想,所以不能發出清淨了知的作用,反而成為染污分別的作用。這就好比一個正常人的眼睛,看黃色是黃色,看白色是白色,如果拿一副綠色的眼鏡給他戴上,這時他所看到的白紙,就會變成綠色的,可是這一張紙真的是綠色的嗎?當然不是,乃是因為戴上了有色的眼鏡所使然。
眾生在看一切事物時,之所以會錯誤顛倒,就是因為帶著有色的眼鏡。因為眾生有妄想、煩惱、分別的緣故,就是我們都以意識分別心 ── 主觀的觀念,看待一切事物,所以所看到的不是事物的真相。因此,世尊在這一部《楞嚴經》中,明白的指示我們,見、聞、嗅、嚐、覺、知六根中性,就是佛性。而這也就是《法華經》中所說的,世尊為了要「指示」眾生本來具有佛之知見,所以出現在世間;這就是世尊到世間教化眾生的第二種總因緣。
三、世尊是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世尊為了要使眾生了悟佛的知見,所以出現於世間。眾生在經過世尊的開示後,就應該依照世尊所開示的,以智慧觀照自心,也要依著世尊所闡明的道理來修行。要提起迴光返照的工夫,在二六時中,對所看的色塵、所聽到的音聲,乃至意根所了知的法塵,向內迴光返照,要提起疑情:到底是誰在看、在聽、在分別?如此日積月累的用功修行,有朝一日就能豁然了悟本來具有不生不滅的佛性,了悟本來就是佛,而確實的相信聖人和凡夫是無二差別,眾生和佛是平等的。這種迴光返照的工夫,在這部《楞嚴經》是採用耳根圓通法門,就是返聞聞自性,是從耳朵下手的工夫。當耳朵聽到外面音聲的時候,不去分別外面的音聲,而是反過來向內追究:是什麼人在聽,會聽音聲的到底是誰?這就是迴光返照,向裡面去尋找耳根的聞性。
如果有一天被你找到了,就是開悟了;而不管是從眼根修、耳根修、鼻根修,乃至用意根修,都能夠照了自性而開悟。禪宗的參話頭,是從意根迴光返照,如參念佛者是誰?就是從內心發起念佛的心來念佛,念了幾句「南無阿彌陀佛」之後,便向裡面尋找到底是誰在念佛,而不是分別所念的佛,或生起阿彌陀佛很莊嚴,我要去西方極樂世界等種種的分別念頭,乃是向裡面迴光返照;念佛的人一旦被你找到了,也同樣的是了悟眾生本具的佛性。
在宋朝的時候,溫州雁山能仁寺,有位枯木祖元禪師。他在雲門庵親近大慧宗杲禪師的時候,有一天晚上在禪堂坐禪,香燈師看到佛前的琉璃燈火,燈心已經快燒完,火快要熄滅了,於是就用夾子把燈心剔起來。就在香燈師剔起燈心的時候,祖元禪師聽到啪一聲就開悟了。他照了本具的佛性,於是便做了一首偈:「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
第一句「剔起燈來是火」,從外表看來,是剔起燈心就有火了,但所說的是智慧火,所以前二句「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是說明從內心提起智慧火,而智慧之火一起,就把無始劫以來的無明煩惱照破。第三句「歸堂撞見聖僧」,「聖僧」是指眾生本具的佛性,回過頭來撞見一位聖僧,就是迴光返照了悟自性。而最後一句「幾乎當面蹉過」,是因為以前不認識本自具足的佛性,因此差一點就當面錯過了。這一首偈的意思是,用迴光返照的功夫,提起智慧,把無明打破,而照了自性,也就是悟佛之知見。
這就是世尊出現於世間的第三種總因緣。
四、世尊為欲令眾生「入」佛知見故,出現於世。眾生的心都是習慣向外起分別,所以叫做「出」;我們如果能夠時時迴光返照,向裡面照了,照到一心本源,就是照到一真如心的本源,就稱為「入」。如果能向裡面照了,就是始覺的智慧,照到本覺的理體,照到煩惱淨盡了,智慧都圓滿了,便能夠轉八識成四智,也就是入佛之知見了。前面所說的「悟」是了悟,此處的「入」是證入,這是有前後的次序及深淺之別的。悟在前,證在後;悟較淺,證較深,所以要把它分開來說,是先有悟才起修,修後才能有深入的體證。世尊之所以出現於世間,就是要開示眾生,指示出佛性在那裡,更進一步的教導如何了悟,如何證入佛性,就是要我們轉凡成聖,成就最究竟的佛果,而這就是世尊出現於世間的第四種總因緣。
別因緣 別因緣是說明本經的說法因緣。依據《楞嚴經正脈疏》交光法師所說的別因緣有十種,而現在是依據《楞嚴經講義》,圓瑛大法師所說的有六種因緣。第一是恃多聞忽定力,第二是警狂慧破邪思,第三是指真心顯根性,第四是示性定勸實證,第五是銷倒想除細惑,第六是明二門利今後。
一、恃多聞忽定力。「恃」是依恃、依靠,就是依恃著多聞佛法,而忽略了定力的修持。凡是上根利智的人,大都喜好多聞佛法,而不勤修禪定,對於聞、思、修三慧,只是偏重聞慧,而缺少思慧及修慧,這就像一個人只是在那裡談論美味珍饈,而沒有吃進肚子裡,就畢竟不能飽一樣。阿難尊者一向喜好多聞,並未盡全力於定力的修持,因此才會誤墮婬室,受摩登伽女的災難,也因此才發起了世尊講這一部《楞嚴經》的因緣。
約大乘教法的眼光來看,阿難尊者是大權示現,意思是說阿難尊者是一位偉大的菩薩,只是用這種權巧的方便示現,藉著誤墮婬室的因緣,世尊才有機會講這部《楞嚴經》。因為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世尊要講一部經,要有發起的因緣。阿難尊者假作只是一位多聽聞佛法,不修禪定的小乘人,因此而誤墮婬室,於是才開啟了《楞嚴經》的起教因緣。
阿難尊者受到摩登伽女的災難後,回到世尊的座下,就向世尊頂禮傷心的哭泣,自述非常悔恨無始以來,一向多聞,未全心全意的修禪定,以增長自己的道業,所以虔誠懇切的請求世尊開示,十方一切如來,得成菩提所修的方法。由此可見只是多聞對修行並無幫助,不如真正好好的實修。在經文中,世尊呵責阿難尊者:「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秘密妙嚴,不如一日,修無漏業,遠離世間,憎愛二苦。」又說:「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這都是說明了世尊是為了恃多聞忽定力者而說這部《楞嚴經》。
二、警狂慧破邪思。「警」是警告;「狂慧」是雖有智慧,卻是偏差的智慧,也就是說,世尊是為了要糾正思想不正確的人,為了要破除偏邪的思想,所以才講這部經。
世間上有一些聰明利根的人,所了知的道理雖然很深,卻是以為既然本具有佛性的話,我現在就是佛,何必修證?因此,就不肯下功夫真實的修行。雖然知道道理,由於無明妄惑未除,不免落入邪思,難出愛網,更沒有辦法了脫生死輪迴的痛苦。就如阿難尊者,雖然心中很明白,但卻力不從心,兩隻腳不聽使喚的走到摩登伽的家裡去,就在快要毀掉戒體的時候,幸賴世尊的楞嚴神咒才得以解脫。阿難尊者被文殊菩薩解救回來之後,便說出了出家的因緣,是因為見佛相好,認為世尊的莊嚴相好,絕非一般欲愛所生,因為心生敬仰,才發心出家。而這也正是說明了阿難尊者的錯誤,因為他是以意識妄想心,分別莊嚴或不莊嚴,這就是意識妄想心用事,而不是根性無分別的妙用。
阿難尊者的遭墮,是顯示婬愛是修禪定法門的大賊,而楞嚴大定是破除愛欲的將軍,它能夠破除眾生的愛欲煩惱。經文中說:「欲漏不先除,畜聞成過誤。」就是說,欲漏如果不事先把它除掉,縱使把所聽聞的佛法記在內心,也會變成過失和錯誤。世尊為了要警告狂慧學者,使其不落邪思,所以說了這部《楞嚴經》。
三、指真心顯根性。世間的眾生都認為,我們的心臟就是心,這是錯誤的想法!心臟是在我們的身體裡面,它的形狀就好像倒掛的蓮花一般,是完全沒有知覺作用的肉團心。或許有人聽到這些話,會認為不對,會覺得這顆心是能夠知道事情,能夠思慮、分別事情,怎麼說是完全沒有作用呢?一般人把肉體的心臟當做是心,這是一種錯誤;而又誤認妄想心的功能就是肉團心的功能,這又是加一層的錯誤!心臟雖是動物類很重要的器官,但我們的了知、思惟及分別的作用,並不是心臟,假使心臟有知覺作用的話,一個人剛死亡時,心臟還沒有壞,應該會有知覺才對,可是事實並非如此,由此可知,知覺性並不是心臟的作用。
一般人對於肉團心不是真心的道理,是較容易了解的,可是,對於妄想心不是真心的道理,就不容易破除了!眾生的迷執很深,迷根難拔,不但是一般凡夫眾生如此,就是權教小乘人,也都是如此,以為第六意識妄想就是心。所以當阿難尊者請求世尊開示諸佛所修大定的時候,世尊一開口就對阿難尊者說:「一切眾生,從無始來,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因此,才有二次徵心、三番破識、十番顯見的開闡。這就是世尊希望要修持首楞嚴大定的人,必須要以真心做為本修因,也是顯示真心就是首楞嚴大定的全體。
在這一部《楞嚴經》第一卷中,世尊問阿難尊者:「當初發心,於我法中,見何勝相,頓捨世間,深重恩愛?」阿難尊者回答說:「由目觀見,如來勝相,心生愛樂,故我發心,願捨生死。」世尊就徵問阿難尊者:「唯心與目,今何所在?」這是世尊第一次徵心。
雖然世尊是問心與目,但是主要是在問「心」在那裡,目不過是兼帶而已。阿難尊者回答了七個地方,結果都被世尊一一斥破,這就是「三番破識」中的「破妄識無處」。阿難尊者轉計七處,不知真心之所在,因此,世尊為直指真心,使阿難尊者當下領悟,就舉手握拳,看看阿難尊者能不能體會,這就是禪宗直指人心,不落語言文字的教法。世尊怕阿難尊者不能體會,還特別的提示他:「汝今見否?」阿難尊者回答:「看見了。」世尊又問阿難尊者:「你看到什麼?」阿難尊者回答:「我見如來,舉臂屈指,為
光明拳,耀我心目。」
世尊又問:「你是用什麼看的呢?」阿難尊者回答:「我和大眾,都是用眼睛看的。」在這一段問答中,阿難尊者真是辜負世尊的一番苦心!世尊將把手抬高,舉出拳頭給阿難尊者看,目的是要他看拳頭的時候,能夠藉此迴光返照,照了自己的見性,也就是要他能找到看拳頭的是誰?世尊問阿難尊者:「你有沒有看到?」就是在問他:你有沒有看到本具的自性?但是阿難尊者不是看到自己的本性,而是看到佛的拳頭,這是向外的意識分別,所以,世尊就追問阿難尊者:「你眼睛能夠看到,到底那個是你的心啊?」這是第二次的徵心。
阿難尊者當時很漏氣,因為他實在沒有體會世尊所開示的意思,因此,阿難尊者回答世尊說:「如來你現在問我心的所在,而我用心想來想去,我以為我能想的作用,就是我的心。」這就是阿難尊者被佛所逼問,把自己錯誤的見解說出來,這分明是把意識妄想當做是真心。世尊聽了阿難尊者的這段話後,就呵斥他:「阿難!這不是你的心。」這一段文就是「三番破識」中的「破妄識非心」。
阿難尊者聽了世尊說「這不是你的心」的話,嚇了一大跳,於是請問世尊說:「如果這不是我的心,叫做什麼?」世尊告訴阿難尊者:「這只是前塵虛妄相想,迷惑顛倒你的真性。」阿難尊者聽了世尊說妄識非心的話之後,生起恐怖心,認為這樣我不就沒有心了!這個時候,世尊就為阿難尊者開示真心是離塵有體的,也就是要阿難尊者自己去勘驗,如果離開外面的塵境有體,那就是你的真心;如果是離塵無體的話,這只是塵境分別影事,也就是說,離塵無體的話,就只是你對前塵境界分別的作用而已,這是「三番
破識」中的「破妄識無體」。
「三番破識」不但說明了我們的心臟沒有作用,不是真心,就是第六意識妄想的分別心,也不是真心,這個妄想心雖有五種勝善功能,仍是不足以採用。
眾生的意識妄想,有五種的勝善功能,現在簡略的說明如下。第一是見佛相好:阿難尊者說,他是看見了如來的莊嚴相好,才發心出家修行的。因為阿難尊者見佛的相好莊嚴,就是用意識分別心思惟,認為佛的莊嚴相,絕非一般欲愛所生,是出世修行的人才有的,這就是意識五種勝善功能之一。第二是聽聞佛的音聲言教,能夠記得如來所說的深奧道理,永久不忘失。第三是聽到佛法能夠瞭解、了悟妙明心,元所圓滿、常住心地。第四是能夠制止散亂心而進入寂靜的禪定;不過縱使滅掉一切的見聞覺知,使心保持在清淨的幽閑境界,不向外起心動念,這也是一種意識的分別,是不可取的。第五是界外取證;就是以意識用功修行了生死,能夠跳出三界,得到滅盡定而成就阿羅漢果。
以上這五種都是意識的勝善功能,凡夫眾生和二乘人都很難把它捨棄!而世尊在這部《楞嚴經》中,要我們欲修楞嚴大定的人,務必把意識的一切作用都剷除,因為這不是菩提的正因,而是生死輪迴的根本。
在這部《楞嚴經》,世尊判別真妄二種根本時,告訴阿難尊者說:「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用攀緣心,為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為什麼有許多修行人無法得成無上菩提,卻變成聲聞、緣覺,或成為諸天魔王及其眷屬呢?都是由於不知兩種根本而錯亂修行的緣故,這就好像煮沙而想使它變成香噴噴的飯一樣,縱使經過微塵劫,終究不可得。
兩種根本,第一是無始生死根本:這「生死根本」,是眾生所用的意識妄想攀緣心,因為把它當做是清淨的自性,所以從無始劫來,意識妄想用事而生死輪迴不休,所以意識妄想是生死的根本因。第二是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這是眾生的識精元明,就是六根中性,而這六根中性是能生諸緣,卻是緣所遺者。在這一部《楞嚴經》中,世尊很清楚的說明了修行的真本與妄本,真本是無始菩提涅槃的元清淨體,妄本是無始的生死根本 ── 眾生的意識妄想。只因眾生執妄為真,多依妄本而修,所以現前雖成九次第定,終究無法得成究竟的實果。
在本經第一卷中的「三番破識」,就是要把妄識破除清淨,到這個時候,阿難尊者才肯捨去妄識而追求真心,於是懇求世尊開示寂常心性的道理,希望世尊「發妙明心、開我道眼」。「妙明心」是根性的真本,「開道眼」是啟開圓解的智慧眼。世尊應阿難尊者的請求,於是十番顯示見性,也就是指出根性就是真心,所以過去的大德說:「顯見即所以顯心」。
「十番顯見」,是從見性顯示真心,第一「顯見是心」,第二「顯見不動」,第三「顯見不滅」,第四「顯見不失」,第五「顯見無還」,第六「顯見不雜」,第七「顯見無礙」,第八「顯見不分」,第九「顯見超情」,第十「顯見離見」。在「十番顯見」後,世尊就剖妄出真,剖開根中所帶之妄,顯示純真無妄的自性。
阿難尊者請求世尊開示真心,可是要在眾生的身上指出純真無妄的真心,是不可能的,因此,世尊只好先帶妄顯真,再剖妄出真。對於這道理,交光法師提出了很微妙的譬喻來說明:「阿難尊者認識為心,如愚人執石為玉,不肯放棄,佛為帶妄顯真,指見是心,如指璞說玉,璞雖是玉,尚有石皮未破,其玉不純,故又為破同分、別業二種妄見,如剖璞出玉,光瑩煥發矣。」
續讀下文按這裡↙,再點收起
續讀下文按這裡↙,再點收起
在這一部《楞嚴經》中,世尊為了要從根性顯示真心,就在「十番顯見」之處,在眾生身上先找出帶妄之真,再由帶妄之真的見性,更進一步的剖析真妄,而指出純真無妄的真性。因此可知,世尊是為了指真心、顯根性,也就是開示如來密因的道理,才說了這部《楞嚴經》。
四、示性定勸實證。「性定」是自性本定。一般凡夫、外道、小乘、權教菩薩等的修行,都各有其禪定,但卻都不是究竟的禪定。因為凡夫、外道、小乘、權教菩薩,雖然他們也都欣慕真理而修習禪定,但是他們並不瞭解真的根本,所以用意識心錯亂修習。如本經說:「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這是指出不知真本的修行者,縱然是滅盡所有的見、聞、覺、知,對外界的動塵之境都已捨離,但卻反過來執著於內心的靜塵之境,這也同樣是意識分別的境界。因此,好樂修習禪定的凡夫,如未能了解真妄兩種根本,所修的四禪八定,仍舊是無法超出執守幽閑的境界。
本經說:「一切世間,諸修行人,現前雖成九次第定,不得漏盡,成阿羅漢,皆由執此生死妄想,誤為真實。」由此處可知,小乘行人所用的心,不是真實心,所以世尊呵斥阿難尊者,就是要破除他的妄想心。而阿難尊者卻生起疑惑,請問世尊:「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同諸土木。兼此大眾,無不疑惑!」阿難尊者被世尊呵斥所用非心之後,疑惑惶恐的請問世尊,認為如果所用的心,不是心的話,我就沒有心,既然沒有心的話,和土石草木又有何差別?對於意識不是心的道理,不但小乘行者無法理解,就是權教菩薩,也同樣疑惑不解,因為權教菩薩也是用第六意識,修我、法二空觀,因此,他們所修的禪定,也都有入定、住定與出定,而這都不是究竟堅固的性定。
如上所述,外道、小乘行人與權教菩薩所修的禪定,都無法達到究竟的佛果。凡夫、外道所修的禪定,一旦定力消失時,就會「降德貶墮,散入諸趣」。有的甚至從外道的無想天,墮落到三惡道;或者因為毀謗三寶,所以就從非想非非想處天,直接墮入地獄之中;小乘行人,雖然不會墮入三途,但是因為以意識心修行,所以沒有成佛的分;至於權教菩薩,雖然有成佛的希望,但卻仍離佛的境界很遠。追溯其病源,都是因為以生滅心為本修因,所以就沒有辦法發明不生滅性。
本經第四卷說:「若棄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念銷落。」乃至「云何不成無上知覺?」這就是說,把生滅的妄識去除,修習真常的根性,這樣的話,就能常光現前,根、塵、識心就能應著「守真常、棄生滅」的這一念心而銷落,而能成就無上菩提。
在本經第五卷偈云:「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三摩提」是指耳根圓通法門,這是幻化的修行,因為煩惱是幻化虛妄的作用,並沒有實體,所以我們就要幻化修、幻化證。果能如此,彈指間就能夠超脫於無學。這都是在指示凡夫、外道、小乘行人及權教菩薩,應該修習真常的性定,才能得證圓通的道理。
本經第六卷中,世尊命令文殊菩薩選擇圓通法門,文殊菩薩回答世尊說:「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又說:「此是微塵佛,一路涅槃門。」乃至最後的結語:「但以此根修,圓通超餘者,真實心如是。」以上所說的道理,都是曲開巧修之門,就是以方便啟開巧妙修行的法門,來指示性定。在本經第八卷中,如來詳細列舉出菩薩歷位修證的階位,都是希望能夠引導修習耳根圓通法門者,漸次深入境界,證得無上佛果。由上可知,世尊是為了示性定勸實證,才講這部《楞嚴經》,這就是講這一部《楞嚴經》的第四種別因緣。
五、銷倒想除細惑。「倒想」是顛倒想;「細惑」是微細的無明煩惱。眾生自從無始劫以來,背覺合塵,迷惑顛倒,所以迷執心是在身體裡面,並認為法 ── 一切事相,是在心的外面;或是固執因緣,而停滯在小乘權教;或執著於自然,成為外道,這都是「顛倒想」。這種「顛倒想」是會障礙真修的。在本經「十番顯見」的第九「顯見超情」,正是遣除因緣和自然兩種妄計情執。
因緣和自然都是妄情的分別,在這一部《楞嚴經》中說得很清楚。本來佛教也是權巧方便說因緣的,但在這一部《楞嚴經》,以如來藏「不變」之義,否定因緣的道理;以如來藏「隨緣」之義,否定自然的道理。世尊在顯根性是真心後,就會四科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就是闡明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一一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既不是因緣也不是自然;在融七大之處,說明地水火風空見識的七大,一一都是周徧於法界而無礙的。
銷除顛倒想之後,如果微細的煩惱沒有消除乾淨的話,雖然是深信一切唯心的道理,仍然還沒有徹底的體悟真心的本源,因此縱使知道五大是圓融的,卻沒有辦法更進一步明瞭為什麼五大是圓融的?而不瞭解五大圓融甚深的道理,就會障礙自性本定。在銷除顛倒想之後,阿難尊者希望能更進一步的審除微細的迷惑,早日得到妙覺果位,因此懇求世尊開示。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提出二種疑問:第一是疑萬法生續之因。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請教世尊說:「假如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等,都是如來藏清淨本然,為什麼會忽然生出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終而復始?」第二是疑五大圓融之故。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請問世尊說:「『地、水、火、風、空,本性圓融,周徧法界,湛然常住。』世尊!如果地性周徧,怎麼能夠容納水呢?又如果水性是周徧的話,火就不生了,為什麼說水火二性,都是徧滿於虛空,不相陵滅呢?世尊!地性是障礙,空性是虛通的,這二種怎麼能夠說它們是徧滿法界呢?」由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請問世尊的這些話,就可知道,這都是屬於微細的迷惑。
對於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所提出的二種問題, 世尊就先說「不空如來藏」,以顯示萬法生續之因。因為性覺之體,本來是清明的,如果妄加明的作用,就是在本來清淨光明的覺體,加上一個「明」,這就是無端在光明覺體,加上分別作用,於是變成妄覺。由這種過失,生起三細相及六麤相,所以有世界、眾生、業果三種相續。這種萬法相續之相,最初是忽然而生,之後就相續不斷,這就像一個人的眼睛本來是好好的,但用手搓揉之後,虛妄看出空花亂墮一樣。
「不空如來藏」是在說明法性理體雖然是真空,卻具有功德相,就是說真理的本體雖然是超然於物質的存在,卻具有一切性功德,所以能隨緣顯現一切諸法。從它的相來說,如來藏是不空的,因為含有一切性功德,所以能夠出生一切法;世尊據於這種道理,先說不空如來藏以示萬法生續之因。
世尊開示了萬法生續之因後,接著說明「空不空如來藏」以顯示五大圓融的緣故。「空不空如來藏」,是在說明如來藏的體雖然是空的,可是從它的相來說,是不空的,如來藏包含了「空」與「不空」,也就是如來藏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的中道實相,是性相無礙的。在經文中說:「譬如虛空,體非群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五大一一相妄性真,亦復如是。」相妄,是說一切事物的相是虛妄不實的,因為相既是虛妄就沒有所謂的生滅,沒有生滅也就沒有傾奪之事,既然沒有傾奪,又怎會有阻礙呢?性真,是說事物的本性是真實不虛的。其體非五大,所以能夠和融。
世尊說明了「不空如來藏」與「空不空如來藏」的道理,就能夠消除微細迷惑。而富樓那彌多羅尼子為了更進一步知道妄念的根源,於是請問世尊:「眾生有一念不覺,這一念不覺到底因何而有?這妄念的根本是甚麼呢?」世尊告訴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既然是虛妄,就沒有原因,也沒有根本。」對於妄念本來無因的道理,是不容易了解的,因此,世尊就提出了演若達多迷頭認影的譬喻,加以說明。演若達多迷頭認影而驚怖狂走,那裡有個原因呢?演若達多突然發狂驚怖自己的頭不見了,後來發覺自己的頭並沒有失去。這是在說明,他的頭並非從外面得來的,縱然他的狂性沒有停止,他的頭也沒有遺失,所以世尊說「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在你內心狂性停止的地方,就是得到菩提;殊勝清淨本明之心,本來就是周徧法界的。
從世尊這一段演若達多的巧妙譬喻,就能夠了解,既然一念不覺是虛妄的,就沒有任何原因,只可說它是無端生起。不只是最初的一念不覺是沒有原因,就是現在沉迷的我們,也常會無緣無故的生起煩惱來。等煩惱過後,才會自覺到剛才為什麼無緣無故的生起煩惱呢?
阿難尊者聽到世尊的開示之後,又執著在因緣上,世尊為了要消除阿難尊者這種深執,就說明了本來不是因緣,也不是自然,又說明了本然非本然、和合非和合、合然俱離、離合俱非的道理。這道理很深奧,遣了又遣,遣到無可遣,才是實實在在的沒有戲論法。
顛倒想、微細惑,是眾生的我執與法執,我執比較粗,而法執比較微細,我執比較容易破除,法執就不容易破除了。但是世尊總有他的權巧方便,在經過世尊種種的方便開示之後,阿難尊者終於消除細惑,了悟實相。世尊在顯見性就是真心之後,就開示「不空如來藏」與「空不空如來藏」的道理,就是要藉由這道理,消除眾生的顛倒想,斷除眾生的微細煩惱。由此可知,世尊是為了銷倒想除細惑,所以說了這一部《楞嚴經》。
六、明二門利今後。「二門」是平等門與方便門,唯有圓教、實教,才能二門都具足。第一平等門: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同時一心和萬法,也是本無差別,是平等一相的。心為一切萬法的本體,無論是世間或出世間、凡夫或聖人、染污或清淨、依報正報、因果等,無不是從心所建立、以心為體,若離開心,就無一法可得,就是說一切法不能離心而存在。如本經所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這段經文說明了一切諸法之所生,乃是唯心所現,其中包含了所有的因果,乃至世界微塵,都是由心所成,所以心是一切因果、世界微塵的本體。
「心」與「法」是二種不同的名稱,這裡所說的「心」是一真如心,是約體而說;「法」是世間萬法,是約相而言,雖然一邊是體,一邊是相,其實是平等無差別的。譬如用金子製作金的裝飾品,無論那一種金的裝飾品都是金,金的裝飾品雖然是各種不同,但既然都是由金所製成的,所以離開了金,就沒有金的裝飾品可得。心生起一切萬法,一切萬法都是由心所成的道理,也是和原金與金的裝飾品的情形一樣,唯有一真如心是真實的,由心所現的所有虛妄相,是空無自性的,所以一切凡聖、染淨、依正、因果的差別之相,都是了不可得。這是圓實教中所說「知真本有、達妄本空」的道理,並不是撥無因果的邪見。
第二方便門:就是揀擇真妄。在一切諸法中,分別真、妄,對於妄法就把它破除,對於真心就啟發使其顯現,因此就有迷、悟、修、證的差別。真心雖是眾生本自具足的,但眾生長久以來迷失了真心,如果不用方法,把真心開顯出來,就終究無法見到真心。妄法雖是本來空,但是眾生對於這虛妄法的執著已經很久了,所以若不用方法把它破除,眾生就無法得到覺悟;而縱使能令眾生有所覺悟,並能了了分明,若不藉著方便的修行方法,捨妄歸真,仍然是無法契入一真平等的道理。我們雖然從這部《楞嚴經》圓融真實之教,了知迷悟無二,聖人與凡夫沒有差別,還須先藉由方便門揀擇真妄,進而捨妄歸真,使修行的功夫能夠漸次深入,能夠融會一門平等的真理,到達「知真本有,達妄本空」的境界,這種道理絕不同於權教小乘之說,乃是真妄條理分明,迷悟迥然不同。
阿難尊者啟請世尊的開示,就包含了平等門與方便門這二門的道理。阿難尊者遭受摩登伽女災難,回到世尊座下之後,向世尊請示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禪那,最初方便。若約二門而言,是屬於平等門。但是了解平等門的道理之後,如果不藉由修行,也就無法證入,因此阿難尊者便請求世尊開示,要如何下手用功,才能證入平等門,這就是請示方便門。
世尊開示了平等門的道理之後,阿難尊者向世尊說:「世尊您向我開示如此微妙的道理,我已經了解眾生本具有佛性,這佛性就是宇宙萬有的本體。舉例來說,好比一位天王賜予我一棟華屋,但是這位天王卻沒有告訴我進入這棟華屋的門在那裡,所以我也就沒有辦法進入這棟華屋了。」這就是表示雖然了解平等門的道理,如果不了解方便門的修行方法,也是修證無門。於是世尊就為阿難尊者開示妙三摩的修行法門。
在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禪那的開示之中,有平等門與方便門二者併用的,也有二門各別運用的,都在這部經的經文中分明看得出來。在妙奢摩他中,是先用方便門來抉擇真妄,對妄識則三番破其虛妄 ── 破妄識無處、妄識非心、妄識無體 ── 直到阿難尊者決定把妄識捨去;在見性方面,是十番顯其真實,使阿難尊者決定採取見性以為修行的根本。其中所說的是方便門,而非平等門的道理。阿難尊者既然肯捨妄歸真,如果把這真體只局限在六根中,而不與萬法普徧圓融的話,怎麼能夠說是了知圓融的道理,成就奢摩他微密的觀照呢?
世尊破妄識顯真性的時候,只是說明了六根中性是眾生本具的佛性,但如果以為佛性只是局限在我們的六根中,就不能算是了解圓融妙理的人。所以世尊教阿難尊者捨妄歸真,是用平等門,也就是會四科即性常住,融七大即性周徧。世尊告訴阿難尊者: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一一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而地、水、火、風、空、見、識,這七大的體性乃是周徧圓融的,並說明了眾生、世界、業果三種生續,是不出一心的,這三者之所以會周而復始連續不斷,乃是由於眾生的迷妄,但是它的本體是一真如心。
世尊在說明五大是圓融的,其體為法界的本體時,闡明了空如來藏、不空如來藏、空不空如來藏的道理,而這道理正是真正奧妙、徹底之所在。因為是說明「離即離非、是即非即」的道理,所以是屬於平等門。
阿難尊者在未聽過這部《楞嚴經》之前,是居於小乘初果,對道理了解的還不夠深入,假如不用方便門來指示出識心是虛妄,顯示見性就是真心,就會造成真妄混淆不清,就不能夠把妄識捨去,而見到真心本體了;但若只是用方便門來捨妄歸真,而沒有用平等門的道理來融會,就真妄永遠隔離,無法了悟、無法證入圓滿妙理,所以,世尊在開示自性本定時,是方便門與平等門同時運用。
世尊開示妙三摩,是專用方便門,就是要阿難尊者選擇耳根圓通法門修行。在經文中,世尊對阿難尊者說:「阿難!汝今欲令見、聞、覺、知,遠契如來常、樂、我、淨,應當先擇生死根本,依不生滅,圓湛性成,乃至圓成果地修證。」又說:「但於一門深入,入一無妄,彼六知根,一時清淨。」而且在說明解六結的地方,直指六根;在選擇圓通法門時,更專指耳根法門修行,這可以說是揀擇分明,都是屬於方便門。
世尊在說妙禪那時,是完全用平等門,其目的是要使學佛修行者,能夠趣向於圓融的極果。在卷八的三漸次文中說:「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明月,身心快然,妙圓平等,獲大安隱。」在十信位的開始,是以所悟的真理,啟發無分別的智慧,從中道實相之中流入;到了十迴向以後,都是法法圓融,全歸平等。
以上所說是世尊所開示的平等門與方便門的道理,世尊雙用二門,目的就是要我們了解道理雖然是平等的,但仍必須依著方便門修行,才能夠完成究竟的佛果。
這部《楞嚴經》,不但是對於當時與會聖眾有所助益,也對未來末世的眾生有極大的利益。在卷二破除二種顛倒分別見妄之前,世尊說:「吾當為汝,分別開示,亦令將來,諸有漏者,獲菩提果。」在開示七大之前,世尊又說:「吾當為汝,分別開示,亦令將來,修大乘者,通達實相。」在經文裡有很多地方都能夠看到類似這樣的話,由於末法眾生業障深重,因此世尊悲念之情就更加深切。文殊菩薩選擇耳根圓通法門時說:「堪以教阿難,及末劫沉淪。」世尊在辨別五十陰魔的地方也說:「汝等必須,將如來語,傳示末法。」可見這部《楞嚴經》,不但是為了利益當時與會的大眾,也是要利益未來的眾生,可知世尊是為了明二門利今後,所以說了這部《楞嚴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