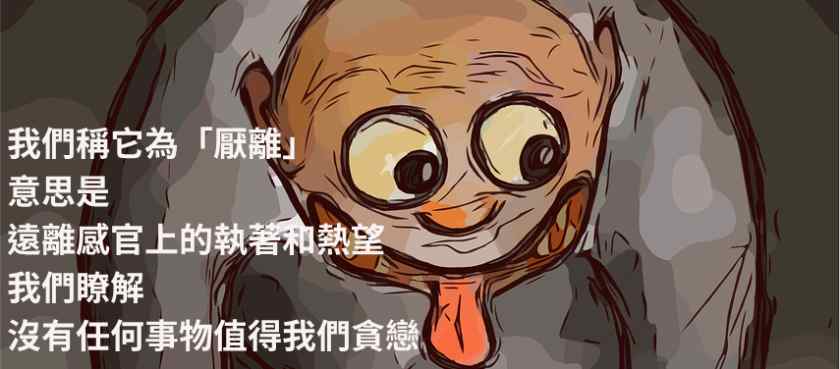
我們修行的方法是:
(一九七八年雨期安居期間,傍晚課誦後,對一群剛出家僧侶的開示。)
我們修行的方法是:仔細地觀看事物並且弄清楚它們;我們繼續而不斷,可是並不慌忙或匆促,但也不會太緩慢。那是逐漸摸索出我們的方向,然後將它歸集的一樁事。不管如何,所有這歸集在一起,是朝向某個目標 —— 我們的修行有一個目標。
對於我們大部分人來說,當我們一開始修行時,除了欲望外,什麼也沒有。緣於需求,我們開始修行。在這個階段裡,我們的需求是錯誤的需求,那就是說,它是迷惑無知的,是雜有錯誤知見的需求。
假如需求中沒有摻雜錯誤知見,我們說,那是帶有般若智慧(註)的需求,不是無知的 —— 那是具有正見的需求。像這種情形,我們說是由於一個人的殊勝或過去的積聚,並不是人人都是這樣。
有些人不想要有欲望,或是希望沒有欲望,因爲他們認爲修行是指向無欲的。然而,如果沒有欲望,那就沒有修行的方法了。
註:般若(Panna)智慧:從一般普通的觀念到知識的理解,到深入的洞察佛法,意思包含很廣。雖然每次用這個字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但蘊藏在它們所有之中的,是一種愈來愈多對法的瞭解,最後終於有了深的洞察力和覺悟。
我們可以自己看清這一點。佛陀和他所有的弟子們爲了止息煩惱去修行,我們必然希望去修行且必然希望止息煩惱,我們必然希望擁有心的平靜且不想要有迷惑。然而,如果這個需求是摻雜了錯誤知見的話,結果便只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困擾。
每個人,包括佛陀在內,都是帶著欲望開始去修行的 —— 希望擁有心靈的寧靜且希望沒有迷惑和痛苦。這兩種的欲望具有完全相同的意義。假使對這不瞭解的話,那麼,想要脫離迷惑和不想要有痛苦兩者,都會是煩惱的;這些都成了愚行 —— 沒有智慧的希求、欲望。
在我們的修行中,可以看到這個欲望,若不是感官耽著,便是自我苦行,那是非常衝突的。我們的導師佛陀,就是在這種左右爲難的矛盾情況下被困住的;他依循了許多的修行法門,結果都離不開這兩個極端。而今天我們也完全相同,仍然被這兩個極端所苦,也因爲這,我們不斷偏離正道。
然而,這就是我們爲什麼必得要起步的原因。開始時,我們是凡夫俗子,有著作爲人的煩惱,有著缺乏智慧的需求和沒有正見的欲望;如果我們缺少適當的瞭解,那麼,兩種欲望所行便會違逆我們。無論那是希求或是不希求,都仍然是愛執。如果我們仍然不瞭解這兩樁事,那麼,當它們生起時,我們便會不知如何去處理它們。我們會覺得往前走不對,往後走不對,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停下來。無論我們做什麼,只會發現更多的需求,這都是因爲缺乏智慧和有愛執的緣故。
就在希求和不希求的當下,我們能瞭解到佛法。我們正追尋的佛法,就存在當下,但我們卻看不到,反而堅持努力去停止希求。我們希望事情是某一個樣子而不是其他的樣子,或是,我們希望它們不是某一個樣子而是其他的樣子;其實這兩樁事是一樣的,它們同是兩種極端的一部份。
或許我們可能不知道佛陀和他所有的弟子們有這種的希求,然而,佛陀瞭解希求和不希求。他明瞭它們單純地只是心的活動,就像事情只是瞬間的出現而後消失。這類的欲望一直都持續著。當有智慧時,我們不會認同它們 —— 我們除去了執著,得到了自由。無論那是希求或不希求,我們單純地如此瞭解它;事實上,它只是自然的心的活動罷了。當我們仔細去觀察,我們清楚地瞭解,這就是它的本然。
*每天經驗的智慧
因此,在這裡,我們「定」的修習將引導我們去瞭解,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吧!譬如一位漁夫,正在收拉有條大魚的網。你能想像他收網的心情嗎?如果他害怕這魚逃脫,就會匆忙且開始努力地把網硬扯強拉,在他覺察之前,大魚早已逃之夭夭,因爲他太過使勁了。
從前他們會這樣子說,他們會教導我們應該逐步漸進地來,小心地收網,以免讓魚兒逃脫。我們的修行也正是如此,用它逐漸地摸索出自己的方向,小心地匯集,別漏失了它。有時,我們會覺得不想做它;也許不想看,也許不想知道,但是我們卻要繼續做下去,不停地摸索下去。這就是修行:如果我們想做,就去做;如果不想做,我們也一樣要去做,我們就是要持之以恆。
如果我們對修行熱心,那麼,信仰的力量會給我們當下所做的事帶來精力;不過,在這階段,我們仍然沒有智慧。縱使我們精力充沛,仍然不能從修行中得到益處。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而且,我們無法找到正道的感覺會生起。我們可能會覺得無法得到平靜安寧,或是沒有足夠的裝備來修行,或是覺得「道」是不可能的事,於是我們便放棄了。
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非常、非常小心,我們要用很大的耐心和毅力,正如網起大魚一般 —— 我們逐漸地摸索出我們的方向。我們小心地收拉魚網,這努力將不會太困難,因此,不停下來,我們繼續地收網;終於,一段時間後,魚兒會累得停止掙扎,而我們便能輕而易舉地捕獲牠了。通常它就是這樣發生的,我們逐漸地修行,將它匯集在一起。
依著這種方式我們作我們的思惟觀想,如果我們沒有任何特殊的知識或在教理方面的學習,我們仍可以依據每天的經驗觀想。我們利用我們早已有的知識 —— 這知識得自於我們每天的經驗。這種知識對心來說是自然的;事實上,不管我們學習與否,當下我們早已具備了心的實相。不管我們有沒有去探討它,心就是心。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說,不管佛陀出世與否,每件事物就是那個樣子;每件事物早已依著它自己的本然存在了。這種自然的情況不會改變,也不會到任何地方,它就是那個樣子,這叫做「眞實法」。然而,假如我們不瞭解這個「眞實法」,我們便無法辨識到它了。
所以,我們就以這種方式來修習「觀想」吧!如果對經典並不特別專精,就拿「心」本身來學習和瞭解。我們繼續不斷地觀照(按字義是與我們自己對話),對心之本然的瞭解將會逐漸生起,我們便不須要去強迫任何事物了。
*持續不斷地精進
除非我們能停下我們的心,除非我們達到寧靜,否則心將持續不斷一如從前。也就因爲這個緣故,導師佛陀說道:「只要繼續地做,繼續地修行!」或許我們會想:「如果我還不懂,怎麼能做呢?」一直要到我們能如法地修行,否則智慧是不會生起的;所以我們說,只要繼續地修行。如果我們不停地修行,我們便會開始去想到我們所做的事,我們會開始去思索我們的修行。
沒有什麼事是立即可成的,因此一開始,我們不能從我們的修行中看到任何的結果,這就像我常告訴你們,有人試圖磨擦兩根木棍取火的比喻。他對自己說:「他們說這裡有火。」於是他開始使勁地磨擦。他很性急,不斷地磨擦又磨擦,卻總是沒有耐心。他想要有火,不斷想要有火,然而火卻沒來,於是他感到氣餒,便停下來休息一會兒。後來他又重新開始,但進展很慢,所以他又停下來休息;到後來熱量全沒了,因爲它持續的時間不夠久。他就這樣磨擦又磨擦,直到疲倦,整個停了下來;這也不單只是疲倦而已,而是他變得愈來愈灰心,以致完全地放棄。「這裡根本沒有火!」事實上,他一直在做,但是卻沒有足夠的熱量可以引發火;火一直都在那兒,只是他並沒有堅持到底。
這類的經驗造成禪修者在修行中氣餒,因而使他不斷地改變修行的方法。這類經驗,也非常類似於我們自己的修行,對每個人來說都相同;爲什麼呢?因爲我們仍被煩惱所黏著。佛陀也有煩惱,但他在這方面卻有足夠的智慧。佛陀和阿羅漢仍是凡夫的時候,也同於我們;只要我們仍是凡夫,便無法正確地思惟。因此,當希求生起時,我們見不到它;當不想希求生起時,我們也見不到它。有時候,我們覺得有波動,有時候又覺得平靜。當我們沒有希求時,會有一種滿足感,但卻仍然有一種迷惑;當我們有所希求時,那會是滿足與另外一種的迷惑。就是這樣地混雜在一起!
*知道自己和知道他人
佛陀教我們要觀想自己的身體,譬如:頭髮、體毛、指甲、牙齒、皮膚,這全都是身體。看吧!他告訴我們,就在當下去觀察,假使我們沒有清楚地看到我們自己身上這些東西它們真實的樣子,我們便無法瞭解到其他的人;我們不能清楚地看到別人,也就無法看清我們自己。而如果我們瞭解並且看清自己身體的本然,那麼,對於別人的疑惑和猜疑也都會消失。這是因爲,每個人的身和心都是相同,而既然都一樣,便不須要前去檢視這世上所有人的身體 —— 我們和他們相同。如果我們有了這種理解,負荷便會變輕;沒有這種理解,我們所做的一切便只是增加另一種更重的負擔。如果爲了去了知其他的人,我們必須去檢視整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那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很快便會變得沮喪。
我們的戒律也類似於此,當我們在看戒律(出家僧人的戒條)時,會覺得很困難;因爲我們必須持每一條戒,研究每一條戒,用每一條戒來檢視我們的修行。只要一想到這,心中便會叫道:「啊!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們研讀了許多戒條所有的字義,若只是依文解義,便會認定要持好所有的戒條,是能力所不能及的。任何對戒律存有這種看法的人,都會有同樣的感受 —— 戒條眞多啊!
經典告訴我們,要用每一條戒審視我們自己,同時要完全嚴格地持好它們;我們必須知道所有的戒條,並且完全地遵守它們。這正等同於要瞭解他人,我們必須確實前去檢視每一個人。這是非常難做到的,會變成這樣,那是因爲我們照著字面解釋,如果我們只知道死守原文,我們便只得照著這種方式去做。有些老師以這種方法教導 —— 嚴格遵守教本所說,然而,這是行不通的(註)。
註:在另一個場合裡,阿姜 查以下列的說法來完成了類似的談話:「如果我們知道如何守護自己的心,就如同受持了數目極多的全部戒條。」
事實上,如果我們這樣子研究理論,修行將全然不會增長,甚至信心都會喪失,對正道的信念也將會破滅;這都是因爲我們還沒有瞭解之故。如果我們有智慧,將會明瞭整個世上所有的人正好等於這一個人,他們和這一個人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我們觀察和思惟我們自己的身和心。由於看清和瞭解我們自己身心的本然,也就會瞭解每個人的身和心,如此一來,依著這種方式,我們修行的負擔便會變得較輕。
佛陀曾說要教導自我 —— 沒有任何人可以爲我們做。當我們研習和瞭解我們自己存在的本然時,就會瞭解一切存在的本然;每一個人其實都是相同的。我們都是同一個「牌子」,也都來自於同一家公司,只不過外形不同罷了!就像「波海」和「東洽」都是止痛葯,都是爲了止痛,只是一種叫「波海」,一個叫「東洽」;其實它們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當你逐漸把這一切歸納起來時,你將發現,瞭解事物的這種方式,會變得愈來愈容易,我們稱這爲「摸索出方向」,而我們就是這樣開始修行的。我們會變得非常熟練於做這樁事。我們繼續持之以恒,直到我們有了理解,而當理解生起時,我們便能清楚地看清眞相。
*理論與實踐
因此,我們持續修行直到對它有所感受。一段時間之後,依靠我們自己的特殊性向和能力,一種新的體悟就會生起;我們稱這爲「擇法」,而七覺支就是這樣在心中生起的。「擇法」是七覺支之一,其他六種是:念、精進、喜、輕安(猗)、定和捨。
假使我們研究這「七覺支」,那我們會知道書中所說的;但卻還沒有看到真正的七覺支。眞正的七覺支是由心中生起的,因此佛陀帶給我們所有各種不同的教導。所有的覺悟者都有離苦之道的教導,他們教法的記錄,我們稱爲理論上的教導。這個理論本源自於修行,但卻成了僅僅是書本上的研讀或文字了。
因爲我們不知道七覺支就在我們自己内心裏,我們沒有看到它們就在我們心中,於是七覺支消失了。如果它們生起,它們會從修行中生起;如果它們從修行中生起,那麼它們會是導向悟道的因素。而且我們可以利用它們的生起,當作一種指標,使我們的修行正確。如果我們沒有正確地修行,這種事情是不會出現的。
如果我們依著正確的方式修行,便能見到「法」,因此我們說要繼續地修行,逐漸摸索出自己的方向,並且不斷地觀察。除了當下這裡,別認爲你現在尋找的,可以在其他的地方被找到。
我的一個資深弟子,在來此之前,曾在一所寺院裏學習巴利文。他學習得並不很成功,於是他認爲,既然修禪僧人只要坐著,就能看清並了知一切,他也想來試一試。他懷著坐著禪坐就能夠翻譯巴利文經典的意圖,來到巴蓬寺;他對修行持有這種見解。於是,我向他解釋我們的方法;他是完全地誤解了。他原以爲,只是坐著並且弄清楚每樁事物是件容易的事。
假如我們談到有關佛法的瞭解,學問僧和修行僧用的都是相同的字眼,然而事實上,從研究理論得來的瞭解,與從修行中得來的瞭解,是不十分相同的。或許看起來相同,但其中一個是深奧多了,比另一個還要深入。從修行中得來的這一種瞭解,會導致捨離、放棄。我們不斷地堅持下去,直到有了完全的捨離 —— 我們在我們的内觀中繼續努力。如果慾望、忿怒或憎惡在心中生起,別不在意它們;我們不要只是棄它們於後,而是要抓取它們,並且觀察,看它們如何生起、從何而來。假若如此這般的情緒早已在我們的心中,那麼我們就要思惟,看看它們是如何運作違抗我們的。我們清楚地看到它們,並且瞭解,我們自己造成的困境是由於相信、順從它們。而這種瞭解,除了在自己純淨的心中,是不能在其他地方被找到的。
緣於這一點,理論研習者和禪修者,彼此便有誤解。強調研習理論的人,通常會這樣說:「只修習禪定的僧人,光會照著他們自己的看法;在他們的教法中他們沒有根據。」事實上,從某種意義說來,研習與修行這兩種方式,完全是同一件事。如果我們把它想成手心和手背,可能比較容易瞭解。假設我們把手伸出來,這手背好像不見了,事實上我們的手背並沒有消失,只不過是藏到下面了;當我們說看不見它時,並不表示它完全消失了,而是藏到了下面。當我們把手翻過來時,同樣的情形發生在手心上,手心哪裏都沒去,只不過是藏在下面罷了。
當我們想到修行時,我們應該牢記這一點。假使我們認爲它已經消失了,就會改變心意而去做研究,希望在研究中得到結果。但不管你下了多少功夫去研究佛法,你將永遠不會瞭解,因爲你並沒有依循眞理來瞭解它。假若我們懂得佛法的眞實自然,就會放下;這便是捨離 —— 除去執著,再也沒有執著。就算仍有執著,也會變得愈來愈少。研究與修行之間,就有這種的差異。
當我們談到研究時,我們可以這麼來理解:我們的眼睛是研究的對象,耳朵是研究的對象,每件事物都是研究的對象。我們可以知道外形是像這樣、像那樣,但是卻會執著於外形,而不知如何從中解脫出來。我們能夠分辨聲音,但是,隨後卻去執著它。外形、聲音、氣味、味道、身體的感覺以及心裏的印象,都像陷阱一般,捕捉了一切的眾生。
去觀察這些事物是我們修習佛法的方法。當有些感覺生起時,我們應用我們的理解去分辨它。如果我們對理論有豐富的知識,就會立刻求助於理論,看爲什麼會這樣,爲什麼事情會這樣發生,而後又變成那樣 ……等等。如果我們還沒有依這種方式來學習理論,那麼我們就只有自然狀態的心可用了;這就是我們的佛法。假如我們擁有智慧,那便能夠檢視我們的這顆自然的心,並且利用這個做爲研究的對象。這完全是相同的事,我們自然的心便是理論。佛陀曾說過,捉住一切生起的思想和感覺,並觀察它們。運用我們自然心的這個眞實當做我們的理論,我們依靠這個眞實!
*毗婆舍那(觀)的禪修
如果你有信心,無論有沒有學習理論都無所謂;如果我們的信念引導我們增長修行,引導我們去不斷增長活力和耐心,那麼,有沒有學習理論都沒關係。我們有正念當作我們修行的一個基礎,在身體的所有姿勢上,無論是行、住、坐臥,都保持正念。而且,如果有了正念,就會有正知(清晰的了悟)來伴隨它。正念和正知會一起生起,它們生起得很快,致使我們無法分別它們;但是,有正念的時候,也將會有正知。
當我們的心穩固、堅定時,正念會迅速、容易地生起,而這也就是我們擁有智慧的地方。但是有時智慧會不足,或在該生起時沒有生起。雖然可能有正念和正知,但單是這兩項是不足以控制情況的。一般說來,如果正念和正知是心的基礎,那麼,智慧將會有所助益。我們必須不斷地透過內觀禪修來增長智慧,這意思是說,所有在心中生起的事物,都可以成爲正念和正知的對象;但是,我們必須依據無常、苦、無我來觀照。「無常」是基礎,「苦」是指不滿足的性質,而「無我」是沒有個別的實體;我們看那只是一種生起了的感覺,它沒有自我,沒有實體,它會自行消失,如此而已!無明的人、沒有智慧的人,會錯失這個機會,他無法利用這些事情來得到益處。
只要智慧現前,正念和正知將會立即與它同在,不過,在這個初階,智慧也許並不完全地清晰,因而正念和正知不能抓住每一個目標,但是,智慧會前來幫助。智慧能看見有什麼樣的正念特質,和什麼樣的感覺已經生起了,或者,從最廣義的方面來說,無論有什麼正念或有什麼感覺,全都是佛法。
佛陀以內觀禪修作爲他的基礎。他看到這個正念和正知都是不確定、不穩固的。任何不穩固的事物,我們卻希望它們穩固,就會造成我們受苦。我們希望事物符合我們自己的欲求,但我們必然會受苦,因爲事物並不是那樣的。這就是一顆不清淨的心的影響,一顆缺乏智慧的心的影響。
我們在修行時,會變得希望修行很容易,希望它如我們所要的那樣;對於這種心態,我們不必想太遠就能瞭解。只要看看這個身體!它眞的是我們希望的那樣了嗎?這一分鐘,我們希望它這樣子,下一分鐘,我們又希望它是另一種樣子;我們是不是眞有過它是我們喜愛的樣子了呢?關於這件事,我們身和心的本然是完全相同的,它就是它那個樣子。
這一點,在我們的修行中很容易被漏失。通常,無論什麼,我們感覺與我們不合我們便否決掉;無論什麼,我們不喜歡,我們便甩掉。我們沒有停下來想一想,到底我們對事物喜歡或不喜歡的方式是否正確。我們只是認爲,我們覺得討厭的事物必然就是錯的,而那些我們覺得可意的必然便是對的。
這正是愛執的來源。當我們經由眼、耳、鼻、舌、身領受到刺激時,喜歡或不喜歡的感覺就會生起,這表示我們的心是充滿了執著的。因此,佛陀給了我們這無常的教導。他給我們一個方法去思惟事物,如果我們執著於一件不是「常」的事物,那麼,我們將會經驗到苦。我們並沒有理由要求這些事物符合我們的喜歡和不喜歡,我們要使事物哪樣是不可能的,我們並沒有那種權威或勢力。不管怎樣,無論我們想要事物如何,一切事物早已是它那樣了。像這樣的欲求,並不是離苦之道。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心是如何以一種方式的理解被迷惑的,心又是如何以另一種方式的理解沒有被迷惑的。例如:當這心依著智慧,接收某些感覺時,它會視它如不能去執著或認同的東西,這就表示有智慧。假如沒有絲毫的智慧,那麼我們便只會順隨自己的愚癡;愚痴是見不著無常、苦和無我的。我們所喜歡的便認爲好、對,我們厭惡的,便認爲不好;這樣我們是達不到佛法的 —— 智慧不能生起。如果我們能看到這一點,那麼,智慧便會現前。
佛陀在他的心中穩固地建立起了內觀的禪修,並利用它來觀察所有各類的法塵,無論任何法塵在心中生起,他都這樣觀察:縱使我們喜愛它,它卻是不穩定的。那是苦,因爲這些不斷地生與滅的事物並不受我們心的影響。這一切事物都不是眾生或自我,它們並不屬於我們;佛陀教我們要看清它們的本然面目。這就是我們修行的根本原則。
接著,我們會瞭解,我們無法只讓我們想要的種種情緒來,好的和壞的心情都會前來;有些有益,有些卻不然。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地瞭解這些事情,那便無法正確地判斷,反而會隨著愛執跑,隨著我們的欲望跑。
有時,我們覺得快樂,有時,我們覺得悲傷,但這是自然的。有時我們會覺得很高興,有時候卻是沮喪的;自己喜愛的就認定是好,厭惡的便認定是壞,這樣一來,我們和佛法就相隔愈來愈遠,愈來愈遠了。一旦這種情形發生,我們就無法瞭解或辨識佛法;於是,我們便困惑了,因爲我們的内心除了無明之外無他,欲望便愈來愈熾盛了。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心。那不須要我們老遠地去尋求瞭解;我們單純地只要看清這些心的狀態都不是常,我們看清它們都是苦,都不是一個有常性的自我。假如我們依著這種方式繼續來增長修行,我們便稱它是「毘婆奢那」或「內觀禪修」,我們稱那是認知到我們心的內涵,而在這種方法下,我們增長智慧。
*奢摩他(止)的禪修
我們「奢摩他(止)」的修行是這樣的:例如,我們建立觀呼吸(在出入息上保持正念)的修行,作爲一種控制心的基礎或方法,藉由心隨著呼吸的流動,心變得穩定、平靜、靜止;這種平靜心的修行,稱作奢摩他(止)的禪修。這種修行有必要多下功夫,因爲心充滿了各種紛擾,是非常混亂的,我們說不上來有多少年或多少世它已經是這樣了。如果我們坐下來思惟,會看到很多的事物不能帶來平靜與安寧,很多的事物只會導致混亂。
基於這個理由,佛陀教導我們,必須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特殊根性的禪修主題,一個適合個性的修行方法。例如,反覆觀照身體的各部分:頭髮、體毛、指甲、牙齒和皮膚,能使我們很寧靜。透過這種修行,心會變得非常平靜。如果思惟這五種東西能導致寧靜,那是因爲,依據我們的性向,它們是很適合的思惟主體。只要是適合這樣子的,都可以考慮用來修行,並且利用 它來對治煩惱。
另一個範例是觀想死亡。對於那些仍有很多貪、瞋、痴並且發覺它們很難控制的人來說,取個人的死亡當禪修的主題是很有用的。我們將會瞭解,無論貧或富,每個人都會死;我們會知道,好人、壞人都會死,每個人都必得死!開展這種修行,我們可以找到一種厭離的感覺。我們愈修行,我們的禪坐就愈容易產生平靜,這是因爲,對於我們來說,那是一種適合、適當的修行。假使這種奢摩他(止)的修行和我們的根性不相符,那就不會產生這種厭離的心境了。相對的,如果這主題眞的適合我們,那麼,我們將發現 它會不太困難地經常生起,而且我們會發現,我們自己會經常想到它。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中,看到一個實例。當在家人托著許多盛了各式各樣不同食物的盤子來供養比丘時,我們遍嚐每一樣,看哪一樣是我們喜歡的。當我們嚐過了每一道菜,便能說出哪一道是最適合我們的。這正是一個例子:我們會吃我們覺得適合我們口味的,我們找最對胃口的,我們不會去碰其他各類的食物。
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出入息上的修行,是個適合我們所有人打坐的例子。似乎當我們到處嘗試各種不同的修行方法時,都覺得不是很好,但是,只要我們一坐下來觀呼吸,便會有好的感覺,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們可以利用靠近我們的事物而無須遠求,這樣對我們會較有利。只要觀照呼吸,呼吸出去又進來,出又進 —— 我們就這樣地觀照。我們長時間保持觀照呼吸的進與出後,慢慢地,心便會安定下來。這時,其他的活動仍然會生 起,但是我們會覺得,它們好像和我們相隔很遠似地。那種感覺就猶如我們彼此分開來住而不再那麼親近一般,我們不再有同於以往緊密的連繫,也或許完全沒有了連繫。
當我們對於這種觀呼吸的修行有所感受時,會變得更容易。如果依著這種修行繼續下去,我們累積經驗,便會變得精於知曉呼吸的本然。我們將知道,氣長的時候會是什麼樣子,氣短的時候又會是什麼樣子。
從某種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呼吸好像是食糧。坐著或走著時我們呼吸,睡覺時我們呼吸,走路時我們呼吸;如果我們不呼吸,那就會死亡。如果我們想一想,就會明白,我們的生存是靠著食物的幫助;如果十分鐘、一小時,甚至一天沒有吃一般的食物,是無所謂的,因爲這些都是屬於一種粗糙的食物,然而,即使只是短短的時間我們沒有呼吸,我們就會死亡。如果五至十分鐘不呼吸,我們必然會死;不信就試試看吧!
正在修習觀呼吸的人,應該要有這種的瞭解。從這種修持中得來的知識,的確是美妙的。如果我們不去思惟的話,就不會視呼吸爲食糧;然事實上,我們無時無刻都在「吃著」空氣,隨時都在進、出、進、出……。另外,你們會發現,愈是用這種方式思惟,愈會有大的利益從修行中而來,且呼吸會變得愈來愈微細,有時或許還會停止呢!就好像完全沒有了呼吸一樣;實際上,呼吸是由皮膚的毛細孔通過的,這就叫做「微息」。當我們的心完全平靜時,正常的呼吸會以這種方式停止,我們一點兒也不必吃驚或害 怕。如果沒有了呼吸,我們該怎麼辦呢?只要知道它,知道沒有呼吸!那就夠了。這便是正確的修行。
此刻,我們談到奢摩他(止)修行的方法 —— 增長平靜的修行。如果我們正在使用的主體是正確而適合我們的話,它會導致這種的經驗。這只是個起頭,但卻足夠依著這個修行,引導我們一路前去,或者至少到達我們能夠清楚地看清且不斷增強信心的地步。假使我們持續以這種方法思惟觀照,精力就會到來,這就好似缸裡的水。我們把水倒入缸内,而且保持水滿;我們不斷以水注滿水缸,如此住在水裡的孑孓就不會死。努力精進並做好我們每日的修行就像這樣。一切都回歸到修行,我們便會感到美好且平靜 。
這種平靜,來自於我們的「心住一境」,不過,這「心住一境」也會很困惱人,因爲我們並不希望有其他的心境來干擾我們。實際上,其他心境會前來,而且,如果我們想一想,在它本身也可以是「心住一境」。那就如同當我們看到各類的男女時,卻不會有像看到我們父母時相同的感覺一般。事實上,所有的男人和我們的父親一樣都是男性,而所有的女人也和我們的母親一樣都是女性,但是我們對他們卻沒有相同的感覺;我們會覺得自己的雙親比較重要,對我們來說他們有更大的意義。
這就是爲什麼對於「心住一境」應該是這樣子了。我們應該要有像對待自己母親和父親一樣的心態去對待「心住一境」。對所有其他生起的心的活動,我們以相同於像我們對待一般男女的感覺的方式去認知;我們不要停止看它們,我們單純地承認它們的存在卻不賦予他們和我們雙親同等的價值。
*解結
當我們奢摩他(止)的修習達到平靜時,心會是清澄、光明的;心的活動會變得愈來愈少,各種生起的法塵將會更少。當這種境界發生時,寧靜和愉悅會生起,而我們可能會執著那份愉悅。我們應該觀照那份愉悅是不穩定的,我們也應該觀照不快樂是不穩定和無常的。我們會瞭解,所有各類感覺都是不持久、不能被執著的。因爲有智慧,所以我們以這種方式瞭解事物;我們將瞭解,事物會如此這般都是依據它們的本然。
如果我們有這種的見解,就好像持握繩結的一端。若是以正確的方向拉它,這結便會變鬆而開始解開,結就不再那麼緊了。這就同於去瞭解到事物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這之前,我們覺得一切事物必然就是它們那樣,也因而,繩結只會愈拉愈緊;這種緊,便是痛苦。那種方式的生活是非常緊張的,所以我們把結鬆開一些,輕鬆一下。我們爲什麼要鬆開它呢?因爲太緊了!如果我們不執著它,便能鬆開它;那並不是一種必須經常是那樣的恒常狀態。
我們利用無常的教導作爲基礎,明白快樂與不快樂都不是恒常,瞭解它們都是不可靠的,世間絕無恒常的事物。有了這種的理解,我們會逐漸不再相信在心中生起的各種情緒和感覺;我們愈是不相信,錯誤的知見便會相對地減少,這就是解開結的意思。錯誤的知見繼續變得愈來愈「鬆」,執著也就會逐漸地根除。
*厭離
當我們前去瞭解在這個世界上、這個身心上的無常、苦、無我時,將發現有一種厭倦會生起,這並不是日常生活中那種厭倦,那種讓我們覺得什麼都不想知、不想看、不想說,或是不想和任何人有任何關聯的厭倦;這並不是真正的厭倦,它依舊有執著。我們仍然沒有瞭解,仍然有嫉妒、瞋恨的感覺,仍然執著會引起我們痛苦的事物。
佛陀所說的這種厭倦,是無貪、無瞋的狀況,它是由看清一切事物皆無常而生起的。當快樂的感覺在心中生起時,我們瞭解那並不是長久的,這就是厭倦;我們稱它爲「厭離」,意思是遠離感官上的渴望與熱愛,我們瞭解沒有任何事物值得我們貪戀。無論事物是否符合我們的喜惡,都無關緊要,我們不認同它們,我們不賦予它們任何特殊的價值。
這樣子修行,我們不讓事事物物有理由來造成我們困擾。我們已經瞭解苦,已經瞭解隨著情緒流轉並不能引起任何真正的快樂,那只會使我們執著於快樂和不快樂,執著於喜歡和憎惡,而這些本身正是苦的根源。當我們仍然如此執著時,便不會有一種平和的心態去對待事物。有些心境我們喜歡,有些我們不喜歡。假使我們仍有喜、惡,那麼快樂與不快樂兩者都是苦;而那引起痛苦的,就是這種執著。佛陀教導,無論什麼會導致我們痛苦,都緣於它自身的苦。
*四聖諦
因此,我們明白,佛陀的教導是去知道苦,去知道造成苦的原因。更進一步地,我們應該知道從苦中求解脫,以及導向解脫的修行方法,他教導我們就去認知這四樁事。當我們瞭解了這四事,苦生起時我們便能領悟到它,並且知道它有一個原因,知道它不是從天而降的!當我們希望能從這苦中解脫時,便能夠去去除它的起因了。
我們爲什麼會有痛苦和不滿足的感覺呢?我們將瞭解那是因爲我們執著於各類的喜和惡。我們前去明白,我們苦,是緣於自己的行爲;我們苦,是因爲我們賦予事物以價值。因此,我們說,知苦、知苦的原因、知從苦中解脫以及知道滅苦的方法。一旦我們認清了苦,就要去解開結,但我們必須要確定是以正確的方向拉而解開它,那就是說,我們必須明白事物的本然就是如此,這樣 “執著” 才能根除。這就是使我們息苦的修行
知道苦、知道苦因、知道從苦中得解脫以及導致離苦的方法,這是「道」,也就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當我們對這些有了正確的見解,便會有「道」。這些事項能止息痛苦,引導我們到達戒、定、慧。
我們必須清楚地瞭解這四樁事,我們必須想去瞭解,我們必須想要以眞實的方式去看清這些事。當我們看清了這四樁事之後,我們稱之爲「眞實法」。那麼,無論我們向內、向前、向左、向右看,眼裏看到的全都是「眞實法」,我們單純地看到一切事物本來的樣子。對於一位得到佛法的人,眞正體悟佛法的人來說,無論他到那裡,一切事物都將是佛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