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正文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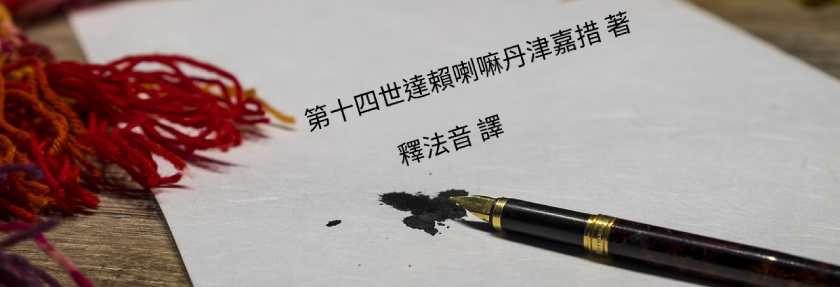
造論禮讚與造論誓言
敬禮般若波羅蜜多。
無緣大悲護羣生,智慧行業雖圓具,
唯由心名假安立,恭敬頂戴如幻佛。
佛所善說甘露藏,空與緣起雙運理,
普為新學開廣智,詞義集攝而略說。
第二章 正文
無疑的,我們每個人都一致地欣求安樂、厭離痛苦,但安樂的成辦與痛苦的去除,卻取決於每個人的身口意三業;身口兩種業行,追根究底,又取決於意業,因此,善植意業修治心續著實有其必要。
修治心續的方式說有多種,最根本的,正是在於如何讓錯謬的心的品類不生,如何讓善良的心的品類生增廣大。
此中,所謂心的善與惡,是如何界定、如何安立的呢?如果任何一種心識的現行,令人感到不安—本來起初自心尚頗為安寧祥和,忽爾之間或顯焦躁,或覺迷矇,由是呼吸急促不順、感得病痛因緣 …… 等,漸漸地並現起身口種種惡作,以現行、非現行及間接的方式使令他人亦感難忍不樂,所有這一類,都名之為惡心;與此相反,凡能給予自他有情現前或究竟的安祥樂果的心的品類,都安立為善心。
要使令錯謬的心識不生,或腦脈開刀,或服用藥物,或迷睡如醉、記憶不清,或沉酣睡去、無諸憶念 …… 凡此方便自有可能獲致少許的短暫益處,但長遠看來,卻是利少弊多。
因此,使令趨向善良的修治之理,應是先思維惡心品類的過患,通達彼心的本質,善予釐清識知;繼而了知善心品類—常常思維善心優點、及其為具量依伴之理,進而趨行串習。若依待著串習之力、依待著其乃具足理量、亦為內心種種功德的所依 …… 等等理由而得使善心品類的力量愈趨增廣的話,則另一方具諸缺失的惡心品類的力量遂必愈趨衰減—這原是法爾本性;若干時候,心即可彰顯出確切堅實的善良徵相了。
針對心續的修治,世上有很多偉大的教主、導師,基於各各不同地區、時節因緣,符順著各自所教化眾生的心量所展示的方便可說頗為繁多,其中,許多佛教經典關於調心的修治方便也多所垂示;諸多的調心方便中,我今僅就空性正見的內涵略作述說。
大體言之,佛教區分為小乘、大乘,大乘又分顯乘與密乘;無論是那一種法乘,無不垂示了無我之見。行持上,內外道的分際在於皈依的有無;見地上的區分,則在於以認許不認許「四法印」為判。「四法印」是:
諸行無常;有漏皆苦;
諸法無我;涅槃寂靜。
如所述,「諸法無我」乃是所有佛教徒共所認許的。
關於無我的意趣,有部、經部、唯識及中觀四個宗派所一致認許的補特伽羅無我,是指沒有獨立自取的補特伽羅;而唯識派以二取體空為法無我,中觀派則以實有空為法無我。
事實上,上下部宗派的見地主張,粗分與細分的差別很大;儘管如此,若得善巧了知下下部的主張,則無疑是徹底了解上上部宗派見地的必要方便,實益頗大。此中,所闡述的,是中觀派的意趣,而且在中觀自續派與應成派中,又是依循著中觀應成派的主張而作述說的。
問:上述各宗派的種種異同是佛薄伽梵金口宣說的嗎?如果是,則當依循那一部經典以為衡準呢?宗派的優劣、粗細深淺的差別也必須要依循著經典以為衡準嗎?
答:四個宗派見地的種種異同,其實是佛薄伽梵觀待隨順著所教化眾生的心量大、中、小不同程度而宣說的。如果佛垂示無我之理,有可能導致一類所教化眾生墮入斷見或生起邪信的危險,佛在部份經典裡就特為揭示「有我」;如果佛回答有我無我時,都有可能讓另一類所教化眾生墮入斷見或常見,佛對於有我無我的問題就一概不作答說,唯安住於平等捨中,一如「十四種無記見」。至於無我,如此中所略述的,佛在經典中也是異名多門地枚舉宣說了許多無我的道理。
那麼,應依循哪一部經典以為衡準呢?就各宗派的觀點而言,有部、經部主要依循的是初轉法輪的經典—《四諦經》等,唯識派主要依循的是三轉法輪的經典—《解深密經》等,中觀派則主要依循二轉法輪的經典—《十萬頌般若經》等;而且依次地三轉法輪,也是基於各各不同地區、命題、時節因緣及所教化中生的根器而安立的。
問:如果必須依循著經典判分出各宗派見地的優劣、深淺及異同的話,各各經典卻都自以為自所展示的命題內涵最為超勝,則到底要認許那一部經典的說法為真實呢?如果認許一類經典的說法為真實,那麼與彼不相隨順的經典的說法就變得不真實了,到底應該如何分辨呢?
而且,如果以為一類經典的說法為真實,另一類經典的說法就為不真實,這一點又唯一必須經由經典本身以為佐證認定的話,那顯然就有無窮推延的缺失了。
答:確實如此,然而論及宗派見地的優劣,實則必須依循著正理智力以為區分。大聖經典中提到,對於佛的教誡必須區分了義與不了義,基於此,經上說:
凡諸比丘與智者,
當如燒鍛冶煉金,
於我教誡善觀擇,
非唯敬故而取信。
針對這個意思,慈氏在《莊嚴經論》中善予疏導闡釋而宣說了「四依」。「四依」是:不依說法者,當依於法或宗義;不依藻詞和雅,當依於義—此中所謂義是指了義,即:了義不僅必須不具有其他密意本懷、需要及不會現行損害及其他了義之義,而且,即使是佛如實語,如果彼義並不是究竟徹底的實義,尚且必須經由其他法義的導出證成的,是為不了義,對於這樣的不了義不當依止,當依於毋須經由他義導出證成的了義;而在了義中,亦不依分別能所二現的分別識,當依於無分別智。
不但如此,要證得以甚深空性為所緣的無分別智,也必須先行修習以甚深空性為所緣的分別比量;如果於此所修品類的意趣得以明晰彰顯,終可證得無分別智。不過,分別智的新予生起卻必須依恃於正確清靜的理由始得安立。—所以究實說來,這一切取決於正理;此諸正理的最初起源又必須追溯到自他的經驗之量,因此,正理的最終歸結原是取決於現量本身—這是「正理自在」陳那、法稱兩位論師的意思。
問:另心趨向善良,有謂必須具有了知量及見地理則的分別智力,這有什麼意義、有什麼作用呢?修行人需要的是梵行清淨、心地善良,博學者才需要智力吧!
答:令心趨向善良的次第與作法其實很多,雖然有些委實可以不須觀察任何理由,僅僅一心修習信心即可,但是,僅僅如此卻是無法生起強猛的力量的。特別是欲令無窮無盡的趨向善良,就不能僅僅是串習於所修法義而已;所修法義固然必須具足正理—僅僅具足正理仍然不足—行者必須了知彼義旨趣,獲得堅固定解。由此看來,一個很好的修行者是不能不具足正智慧力的。
僅管如此,如果於博學與梵行不能不兩者擇一的話,則梵行誠然較為重要,原因是,行者任具多少梵行功德即可獲得多少益處﹔反過來説,由於僅僅是博學多聞而不善調心—自心本可獲致安樂,但有可能取而代之的,是由較己為高者生起嫉妒,於朋輩同儕心生競逐,於較己為低者發為驕慢與輕蔑……等,這樣反而使令自他悉不安樂的惡心增盛,就有如藥成毒的危險了。因此,博學應該不壞不礙梵行,梵行應該不壞不礙博學;博學、梵行、善良三者兼備,是非常重要的。
此中,要於無我空性的旨意獲得定解,對於所謂「空」其之所空的真正內涵確切予以了之,實屬必要。寂天菩薩説得好:
未知所觀事,非能取事無。
如所述,若於任所空的所遮品義不能得到定解,是無法證得空性義的。那麼所空的是什麼呢?
所空的所遮品並不是本有質礙有可觸及而後使予空無去除,像空無的彩虹,也不是像虛空,色法俱空的空無,而是安立為自性實有,是於此自性實有的所遮品予以空無去除的意思。
此外,所遮品也不是前現為有而後再予泯除。—譬如昨日有一大片森林,今日為烈火燒焚盡淨,地上再沒有森林—所空的所遮品不是像這樣,而是所遮品無始以來根本就未曾有過,所空的正是這樣的所遮品。同時,遮破所遮品的方式也不是像桌子上花被移走了花沒有了一樣,是所遮處本來就沒有自性實有的所遮品的意思。這裏所顯示的要點是:如果於任所空的所遮品義,或境上自有自成的量未能尋求定解,不知是此非此之意,僅僅是歸諸於一無所有完全的空無,這都不是空性的旨趣。
問:那麼,已然明了此所遮品必然為無的理量或意義了,卻又必須確切觀擇此所遮品必然為無,何需如此煩擾冗瑣呢?
答:事實不然,就像認定一種世間共許為不真實的情事,因執為真實而蒙受迷騙損失一樣,諸法本無自性,卻執為自性實有,亦勢必蒙受損失。姑且以以我為所緣的心為喻。由於以我為所緣而滋生貪瞋我慢等,彼時的執我心態,與貪等煩惱尚未現行,心頗寬寧時執我心態,比較起來兩者的差異頗大。再如,商店中有一件商品,未採購前自己對此商品的心態與採購後自己對此商品執著貪愛的心態,前後也顯然不同。就以商品為所緣的心來說,所緣境一樣,現起商品為自性實有的情況也沒有什麼不同,但是,是否執著商品為真實的或為獨立自有的貪執心態,卻有極大的差別的。
再者,如見到十個人,乍見時,固然會齊現十人境上自有自成的覺受,但卻不一定會生起對此十人的實執貪著﹔而後,或以相似理由或以正確理由,對於十人中的其中一人,或視為極好或極壞—當非理作意的尋伺分別有力地運作時,心其實已經增益了超越事實的善惡好壞從而生起貪瞋愛憎了,那時,從內心深處不僅深深覺得境為真真實實的實有,也貪執境為真真實實的實有。
因此,無論是那一種惡心的現起,必然是有其前行導趨牽引者,有其同具的許多惡心所,甚或是以實執為其助伴﹔如果沒有實執的無明;貪瞋愛憎等煩惱是無以生起的。從另一個角度看,所遮品無始以來本來就是空的;本來就未曾有過的所遮品—根本為無—之所以必須了知其根本為無得到堅固定解的理由是什麼呢?理由是:在所遮品根本為無的情況下,卻現為實有而起貪執,致使非理作意的尋伺分別心就像大海水紋得無永盡—乃是為了斷除這一個過患的緣故,才須對此所遮品堅固了知尋求定解的。
龍樹菩薩《根本智論》〈第十八品〉有兩個偈頌:
若於內外法,盡除我我所,
即滅彼近取,彼盡生亦盡,
業惑盡解脫,業惑從分別,
分別依戲論,空性遮遣彼。
因為所謂的自性實有無始以來未曾有過,所以萬法在實質上絕無所謂的自由自主,都只不過是唯空緣起罷了。進一步説,正因唯空緣起,故可合宜地成立一切損益、作用及感受﹔又因唯緣起而有的緣故,任所顯現的一切輪迴萬法的自性本來空寂,在不脫越法界空性或自性無的範疇之上,得以顯現、成立各式各樣的緣起有法。因此,一切所知品都具有兩種本質,一是現前的顯象的本質,另一是究竟的實相的本質;兩種本質即分別是所謂的世俗諦與勝義諦。
聖者龍樹在《根本智論》上說:
諸佛說正法,正依於二諦﹔
世間世俗諦,真實勝義諦。
吉祥月稱菩薩的《入中論》也提到:
由彼諸法見真妄,
故得諸法兩種體﹔
說見真境即真諦,
所見虛妄名俗諦。
關於勝義諦的區分下當略說。至言世俗諦,觀待於世間所知內含,可區分為正世俗與邪世俗,月稱菩薩對此有清楚的界說:
妄見亦許有兩種,
謂明根與損患根,
損患諸根所生識,
待善根識許為倒;
無患六根所取義,
是即世間之所知,
由彼世間許為實,
餘則世間許為倒。
一如所述。
要言之,必須明了二諦理則的理由是:與各種善惡好壞的顯象既然必須建立關係,則對於任所建立關係的對象現前的、究竟的體性應該是要有一番了解。譬如,自己恒常即須與一個慧黠多思城府深沉的鄰居建立往來關係,如果率然根據對這鄰人的外在印象而迭相往來的話,自己不免要遭受一番損失;這倒不是因為與這鄰人建立往來關係的緣故,而是與這鄰人建立往來關係的方式不夠正確善巧所致,換句話說,由於對這鄰人的內在性情不善了知無法掌握才失算吃虧的。如果於其外在所現印象與其內在本有性情兩者全盤了解善巧抉擇,不僅根據其內在本有性情的處世作法,也根據其外在印象能力等而符順合宜地建立彼此往來關係,自己應該就不致於蒙受損失了。所述說的意趣與此一譬喻是一樣的。
確切的說,如果在諸法的表相或現前的顯象之外,已別無一種究竟的實相,印象與實相完全吻合一致的話,則任所顯現的名言印象就都可以視為真實具量,都可以執為真實具量。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雖然外在顯象顯現為實實在在的實有,但究竟的實相上卻絕非實有。因此,萬法既不是實有或自性有,也不是完全的沒有或無 —— 這就是「中道」;如實了知此一內涵的見地,就是「中道之見」。
那麼,所遮品自性有為無或所遮品「我」為無的內涵是什麼呢?此不妨略作思惟。事實上,此際我們的眼根等任是如何見色等,心任是如何了知、覺受等,以及對境的印象任是如何顯現,都不外乎是顯現所遮處 —— 境 —— 及彼所遮品為自性實有、自主實有,或者顯現境本身自有自成,離諸觀待,這一點顯示了什麼呢?顯示了除了親證空性的智慧外,所有心識都是錯謬之識,這是含遍的。
問:如果於色等諸法安立為名言有的心是不具量的,或者唯由錯謬的心所顛倒認定為有的有法就可以視為有的話,這樣的有法難道不可能變為沒有嗎?
答:由於現境為實有的緣故,所以是錯謬之識,這一點與於自境顯現為具量無欺彼此是不相違的。譬如,取色的眼識雖現境為實有,是一種錯謬之識,但是,眼識對此色執為色而不執色為實有,這對眼識來說是為量,而且,取色的眼識於彼色的顯現與現色為實有亦為量,因為凡能知境的,謂識;基於識極具現起彼境的形相的能力,故謂識即是能現起境的形相的光明與能知,因此才說任何一種能夠分別能取所取的識於自所顯現的,皆為現量,這是含遍的。
此外,唯由任何一種錯謬心識顛倒認定為有的,不必然為有。譬如,眩翳者的眼識現見毛髮披垂相,雖然現起這樣的顯象就彼眼識而言是為現量,但其實彼顯象在顯象處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毛髮披垂相,只不過是心為境欺矇罷了。也因為如此,基於會為一個與其執持方式截然相違的心識之量所遮遣的理由,才認定、安立這的心為邪識,由彼心所視為有的,那裏可以必然就是有的呢?
要之,佛說,固無一法非由心所安立,但任由心所安立的,是不必然就是有的。
由此看來,當萬法現為實有之際,如果如所顯現的即為真實實有,則什麼是實有的內涵予以深細抉擇的話,所顯現的實有的本質必當愈趨明晰。譬如,世間共許為真實的,或者實際上為真實的事物,任於彼施以多少尋辨觀察,彼義自當愈趨明晰,內涵自當愈趨明確堅實,予以尋求的話,必可尋得;反之,若是虛假的,觀察彼義一番尋求的話,即愈顯不明,最後竟變得無法存在安立了。龍樹菩薩的《寶鬘論》有個很好的譬喻:
若於遠處所見色,
趨近必得明晰見;
若謂陽焰即為水,
趨近而觀何無見?
如於諸遠處所見,
世間亦見為真實,
如斯趨近而觀見,
無見無相如陽陷。
舉例來說,人類都一致倡言需求安樂,不妨讓這樣一個所謂需求安樂的人的影像在內心獨一無遺地顯現出來,並且思維;為了獲致人類的安樂,身體方面必須成辦衣食、居處、醫療、交通 …… 等獲得身體安樂的順緣,心靈方面郥必須成辦知識、道德、溫和、善良、安祥 …… 等獲得心靈安樂的順緣。—— 至為明顯,是經由身心兩種安樂的成辦始得獲致人類的安樂的。因此,人的實質是什麼,尋求時發現:固然人的身體、人的心靈都並不是人,但捨除身心外,另有所謂的人,也是沒有的。
再者,比如我認識一個人名叫「扎西」,相遇時,我說:「我見到札西。」我說:「札西變瘦了。」「札西變胖了。」等等,不觀察不簡擇的時候,我根據見到札西的身體、根據札西的身體變瘦了、札西的身體變胖了…… 而說見到札西這個人,…… 諸如此類頗多可說。事實上,不觀察不簡擇時如此如此執持如此如此認定的心並非邪識,此諸言說亦非妄語,但是,若予觀擇,就發現到,原來是尋不到具此身軀的真正的札西的,所言胖與瘦更是無法簡擇。另外,根據札西的心腸好壞,亦得安立扎西為好人、壞人的名言,所以扎西的心並不是扎西。要之,僅僅是依據著扎西的身心二聚的聚合、及彼續流與各各支分即謂之為扎西,是不能成立的;所謂扎西,充其量也不過是依據著扎西的身心二聚而假予安立而已。此如龍樹菩薩在《寶鬘論》上說:
士夫非地亦非水,
非火非風非虛空,
非識亦非彼總攝,
斯此而外無士夫。
另外,所謂見到扎西的身體,也是如此。身體由許多皮、肉、骨骼等部份組成。一般而言,僅僅見到外皮即可說見到身體,雖見不到血、骨骼等也不能說見不到身體,換句話說,見到身體並不需要見到全身,僅僅見到身體的少許部分即可說見到身體。—— 不過有時也有如世間共許的說法,以為若未能見到整體的大部分,就不能說見到身體。
就像把身體的部分 —— 手、足等一一予以分解去除,找不到身體一樣,手足由指頭等組成,指頭由關節組成,關節由上部位關節及下部位關節組成,上下部位關節又各由其微塵組成,將這些一一予以分解去除的話,組合體一概是找不到的;即使是最最微細的微塵,一一予以分解去除其組成部分,亦尋求不得。此外,最最微細的微塵也並不是無方分的極微;如果,最最微細的微塵為無方分的極微的話,則任此最最微細的微塵如何積疊聚累,終究是不可能聚壘成堆的。
至於有謂扎西的心快不快樂而說扎西快不快樂,快不快樂的安立處 —— 心,實質上又是怎樣的呢?
這樣的心的特質是:非由任何色法組成、離諸質礙觸受、堪能顯現任何境界、對象、並且極具唯知的本質。如果不予觀擇,情況正是如此;觀擇的話,就找不到了。當說「扎西心感到快樂」時,觀察一下彼心的本質,發現把心的每一剎那一一予以分解去除,即根本沒有許多前後剎那心所集攝的聚合體。後後剎那時已遮去了前前剎那,過去剎那已逝去無存,已非心識的本質,而未來的未生,現在心識也沒有 —— 為什麼現在心識也沒有呢?
那是因為所謂當下的一剎那心識的內涵不外乎是當下一剎那心識的已生與未生,不會超越這兩種範疇,但對此予以觀察的話,發現現在心識是無法安立的。因此,所謂心感到快樂,根本就尋求不到心感到快樂的安立處;要之,心的快不快樂都不過是依著各自前後剎那的心識的聚合而予以安立罷了。此外,就是「最極短瞬剎那」,也是依著自身的部分而安立,因為各有其所組成的始末初終的部分;如果剎那是無時分的剎那的話,則不可能有由彼所積累的續流。
同理,外在的物質 —— 譬如桌子,當桌子的影像在心上顯現時,雖現桌子為自相有或自主有,但大體而言,若安立桌子為差別事,桌子的差別法便是形狀、顯色、材質即量度等;對此而作觀察,其實是可以評論其價值多寡、好壞如何 ……。譬如說,這張桌子材質不錯,顏色則差 —— 檢視顏色、好壞的根本依據處 —— 一張桌子是有的。雖然是有一個含具種種差別法的差別事,但予以區分並觀察部份與有分,發現在差別法及每一部分之外並無差別事,也就是說,這些一一予以分解去除後,就再找不到一個差別事了。因此如果沒有所謂的差別事 —— 因為必須觀待著差別事而安立差別法,必須觀待著差別法而安立差別事,那顯然地,也是沒有所謂的差別法的。
再以有一百零八顆珠子的一串念珠為喻。有分是念珠,部分則是一百零八顆珠子;固然部分與有分迥異,但一旦分解去除了部分,就再也找不到念珠。因為念珠為一串及彼一串念珠具有許多部分,所以念珠與其每一部分並非為一;反之,若就每一部分一一予以分解去除,也斷無另外的所謂念珠,因此兩者終究不是本質的或根本的為異。因為在念珠自身的部分之外,並沒有所謂的獨立自有的念珠,所以念珠不是自性有地依於部分,部分也不是自性有地依於念珠,兩者自性有地互依是沒有的。另外,念珠也不是自性有地具有珠子,又念珠的形狀乃是念珠的差別法,不僅念珠的形狀不是念珠,而且珠子、珠繩的聚合也是念珠所依待的施設處,所以珠子、珠繩都不是念珠,等等。如此一一觀擇尋求,發現所謂念珠以「七邊」的任何一邊去作推求都是無法找到的。
而且,就每一顆珠子來說,每一顆珠子與其每一部分也是非一非異的關係……等等,以如上述方式去作推求,同樣尋求不得。
所謂森林、軍隊、地區、國家等也是各依自身許多部分的集攝而安立,因此由其每一部分而尋辨觀擇是彼非彼時,都無可尋求。
此外,好壞、長短、大小、敵友、父子等皆須依待著其中一個而後始得安立另外一個,也是很清楚的。
地水火風等依待著各自的部分而安立,虛空依待著各自方位所含遍的部分而安立,佛與眾生、輪迴與涅槃 …… 等等,也都無一不是依待著自身的部分及施設處而唯假安立的。
另外,雖然果由因生是世間共許的事情,但觀擇彼「生」之義,不難發現,如果是無因生,則變成不是恒生就是根本無生;如果是自生,則自身的本質已然完具,並無再生的需要 —— 已生再生,即有無窮推延的缺失;如果是他生,則成為無論是因非因,一切因都可以為生,或者與果必須觀待因的理則相違,由是,安立自他共生亦不合宜,因此,所謂「生」,予作觀擇尋求,其實是無以安立的。龍樹菩薩的《根本智論》:
非自非從他,非共非無因;
諸法隨何處,其生終非有。
而且,雖如所共許的,以為果由因生,但作觀擇,所生品的果如果是早已實有,則己本具恒有,再再新予生起如何合宜呢?實已不需要因新予造作生起了。總的來說,因位時果未生或未成,果雖需待因新予造作生起,但如果自性實有的未生是真實的,那就與根本為無沒有差別了,由因新予造作生起如何可能呢?龍樹菩薩《七十空性論》說得最為簡明:
有故有不生,無故無不生。
綜言之,凡是必須依待著因緣及他法始得成立安立的,已非自主而有,因自主與依他是正相違,此如經云:
任由緣生即非生,
彼所生者自性無;
取決於緣說為空,
任知為空彼安樂。
龍樣菩薩的《根本智論》:
謂法非緣起,斯法未曾有;
謂法非為空,斯法未曾有。
聖天菩薩《四百論》也說:
任依他緣而生者,
此則不名為自主;
盡此無一自主故,
是亦不名為有我。
因此,若根本或本質不空,則各種有法根本不會依待因緣產生變化;由於是本然而有,已是本具恒有的好與壞等,則如何可為造作改易呢?像一棵果實堅美的大樹,若是自性有或根本為實有,怎麼可能會趨變為枯槁凋零華美盡失呢?此際自心任所顯現的,若是究竟的實相,若是真實,自己怎麼可能欺騙自己呢?其實,有許多印象與實相不相符順不相吻合的情事,即使一般世間也都一致地認許的,無始以來因無明的錯謬,雜染的心任是如何顯現都現為境上自性實有;當現為自性實有時,若所顯現的,就是究竟的實相,以根本究竟的心智予以觀擇尋求時必然會愈趨晰,然而事實上卻觀擇尋求不得,消失了也似,這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又,如果是自性實有,則吉祥月稱菩薩在《入中論》中說:
若謂自相依緣生,
謗彼即壞諸法故,
空性應是壞法因,
然此非理故無實。
設若觀察此諸法,
離真實性無可得,
是故不應興觀察,
世間所有名言諦。
於真性時以何理,
觀自他生皆非理,
彼觀名言亦非理,
汝所計生由何成。
所闡述的,如果萬法是自相有或是自性有,則不但應有聖等持智成為遮壞諸法的缺失,應有名言有亦為自性實有而堪為正理觀擇尋求的缺失,而且也應有在勝義中生可不予遮遣的缺失。是以《二萬五千頌般若經》上說:
「…… 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不見菩薩為真實。……」又說:「此義云何?舍利子,斯此菩薩亦菩薩自性本空,斯此菩薩之名亦菩薩之名自性本空。何以故?彼自性爾!空非空色,壞色非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寶積經》〈迦葉品〉也說:
空性並未令諸法為空,
諸法但自空寂。
等等。果真如上述及的,以為諸法實有,則許多經典中一切法是自相為空的自空的說法就變得不合宜了;是故,一切法斷無所謂本質或根本的實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