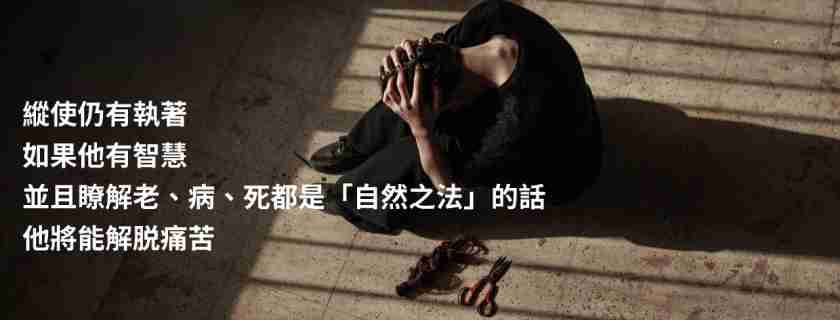
這世間的事物只不過是
我們自己製造的習俗(世俗)罷了,建立了它們之後,我們迷失其中,並且拒絕去放下,致使我們執著於個人的見解和觀念中;這種執著不曾停息,它是輪迴,無止盡地流動,沒有完結。而今,如果我們知道習俗的真相,那麼,我們將會知道「解脫」;如果我們清楚地認識解脫,那麼,我們會了知習俗。這就是去了知佛法,這其中是有完成的。
以人爲例:事實上,人們沒有名字,我們單純地,赤裸裸地誕生到這個世間;如果我們有名字,也只是經由習俗而來的。我曾經思索過這一點,並且瞭解到,如果你們不明白習俗的眞相,它會眞的有害。習俗只是方便我們用來使用的某樣東西;沒有它,我們無法與人溝通,那便沒有什麼好說,沒有言語了。
我曾經見過西方人在他們的國度裡一起禪坐,當他們起坐時,男人,女人聚在一起,有時他們會去互摸彼此的頭部(註)。當我看到這種景象時,我想:「啊!假如我們執著習俗,當下就會生起煩惱。」如果我們能放下習俗,捨棄我們的主見,我們就會有平靜了。
註・在泰國,頭部被看作是神聖的,去觸摸一個人的頭,被認爲是一種侮辱;又,依據傳統,男女不可在公共場合中彼此觸摸;另一方面,坐禪被視作是一種「神聖」的活動。或許這兒阿姜 查用了西方人行爲的一個例子,會特別震驚他的泰國聽眾。
像來見我的將軍、上校,有階級、有地位的人,當他們來時,他們說:「啊!請摸我的頭。」(註)假如他們這樣子要求,那沒有什麼錯,他們高興他們的頭被摸了。但如果你在路上輕打他們的頭,那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這就是因爲執著。所以,我覺得「放下」眞的是達到平靜的方法。摸人的頭違反我們的風俗,但事實上那沒有什麼,當他們同意讓人摸頭時,便沒有什麼問題了,就好像摸一顆甘藍菜或馬鈴薯一樣罷了。
註・在泰國,一個人的頭被一位德高望重的出家人觸摸,被認爲是吉利的。
接受、捨棄、放下 —— 這是個光明之道。無論何時你執著了,當下就有「有」和「生」,當下就有危險。佛陀曾教導關於習俗,他教導要用正確的方法去「解開」習俗,以達到解脫;這就是自在,不去執著習俗(世俗)!在這世間所有的一切事物都有一個習俗的眞實性,建立它們之後,我們不應該反被它們愚弄了;因爲迷失在習俗之中,確實會導致痛苦。關於規則和習俗,是極其重要的一點;能超越它們的人,就是超越了苦!
總而言之,它們是我們世間的一種特性,舉布曼先生爲例,他以前只是一個平民,但現在被推派當了地方代表。這只不過是個習俗,但那是我們應該尊重的習俗;這是世間人們的一部份。如果你認爲:「啊!以前我們是朋友,我們曾經在裁縫店那兒一起工作。」於是你便在公共場合裡拍他的頭,他將會生氣;那是不對的,他會怨恨。因此,我們應該遵循習俗,以避免人們怨恨的生起。瞭解習俗是很管用的,活在世上就只是有關這些而已;知道正確的時間和地點,知道人!
違背習俗爲什麼是錯的呢?「錯」,是因爲「人」的關係!你們應該要機靈,去瞭解習俗和解脫二者,知道每一個適當的時機。如果我們知道如何應用規則和習俗,那麼我們便是善巧的了。但如果我們在不正確的情況下,試著遵照高層次的眞理去行動的話,那就錯了;錯在那裏呢?錯在人們的雜染煩惱,如此而已!人們都有煩惱;在某種情形下,我們遵守某種方式,在另一種情況下,我們卻必須遵守另一種方式。我們應該知道進退,因爲我們生活在習俗裡。問題的產生是因爲人們執著於習俗,假如我們以爲某事是那樣,那它就是那樣;它會存在那裡,是因爲我們想像它會在那裡。但如果我們仔細看清楚些,實質上,這些事物都沒有眞正地存在。
正如我經常說的,以前我們是在家人,現在我們是出家人,我們曾生活在「在家人」的習俗裡面,而現在我們生活在「出家人」的習俗當中。依著習俗我們是出家人,但卻不是「解脫」其中的出家人。一開始我們建立像這樣的習俗,然而,如果一個人僅僅是外表出家,就不表示他克服了雜染煩惱。如果我們取一把沙,且一致地稱它爲鹽,這會使它變成鹽嗎?它是鹽!但只在名稱上是,而不是實質;你不能用它來烹調。它唯一的效用,只在共同的約定範疇下;因爲它根本不是鹽,只是沙。它變成鹽,僅只是透過我們的假設,它才會如此。
「解脫」這個詞本身正就是習俗,但它指的卻是超越習俗。在達到自由,達到解脫之後,我們仍然必須應用習俗以指出它就是「解脫」,假如我們沒有習俗,我們就無法傳達,所以它有它的用途。
例如: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的名字,但他們同樣正好都是人,如果沒有名字來區別他們,當我們想要叫人群中的某人時,喊道:「嘿,人!人!」這是沒用的。你不確知誰會回答你,因爲他們都是「人」。但,如果你叫道:「嘿,約翰!」那麼約翰就會過來,別人不會應聲:「名字」正就是滿足了這個需求。透過名字我們能夠溝通,它們爲社會行爲提供了基礎。
因此,你應該知道習俗與解脫。習俗有其用處,但事實上,眞的並沒有什麼在那兒。甚至連人都不存在!他們只是元素的聚合,依因緣條件而生,依因緣條件而成長,存在一段時間後,便隨著自然法消逝;沒有人能違抗或控制它。但沒有習俗,我們會沒什麼好說,我們會沒有名字、沒有修行、沒有工作。規則與習俗的設立,是爲了給我們語言,使事情方便,就那樣而已。
拿錢做個例子吧!古代並沒有任何的硬幣和紙幣,人們以物質和貨物互相交換,來替代錢。但是,這東西很難保存,因此他們改變方式,製造硬幣、紙幣作爲錢。也許在未來,我們會有一位新國王頒布法令說,我們不需要紙幣,我們應該使用臘,將它融解後壓縮成塊;我們說這是錢,全國通用。不要說是臘,他們也可能決定使用雞糞作爲地方貨幣 —— 除了雞糞外,其他東西亦能當作錢!如此一來,人們就會爲了雞糞而互相爭鬥殘殺!事情就是這樣。你可以用很多例子來說明習俗。我們利用的錢只是我們所設立的習俗罷了,在習俗裏它有它的功用;頒令它當錢,它就變成錢,然而事實上,錢是什麼?沒有人能說得上來。當某事得到了普遍的認同,而後就會產生一個習俗來滿足這需求,世間就是這樣。
這是習俗,但要使一般人瞭解解脫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的錢、房子、家庭、孩子以及親戚都只是我們創造的習俗,事實上,從佛法的眼光來看,它們並不屬於我們。也許當我們聽到這兒時,會感覺不太舒服,但事實就是如此。這些事物只有透過設立了的習俗才有價值。如果我們設立它沒有價值,那麼它就沒有價值;如果設立它有價值,它就有價值。它就是這樣,我們將習俗帶到世間來滿足需求。
甚至這個身體也不眞的是我們的,我們只是假設它是如此;事實上只是一種假設。如果你試圖找一個真實的、有實質的自我在其內,那是沒辦法的;有的只是元素的產生,持續一段時間,而後死亡。每件事物都像這樣。它沒有眞實的實質在,但是,我們利用它卻是合適的。好比一個杯子,有一天它勢必會毀壞,但當它還存在時,你應該使用它,而且好好地照顧它;那是供你使用的工具,如果破了便會有麻煩,因此,縱使它必然會壞,你還是應該盡力來保存它。也因爲如此我們有四種依持物(註),那是佛陀一再教導要去思惟的。它們是一位僧人賴以繼續修行的依持物;只要你活著你就得依賴它們,但你應該瞭解它們,不要去執著它們而讓貪愛在你心中生起 °
註・四種依持物:飲食、衣服、住所、醫藥。
習俗和解脫就是如此不斷地相互關聯著。縱使我們利用習俗,但可別信賴它,把它當成眞理;如果你執著它,痛苦就會生起。「是」與「非」是個很好的例子,有些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但最後誰眞的曉得什麼是「是」,什麼是「非」了呢?我們不知道。不同的人建立不同的是非習俗,但佛陀卻以「苦」當作他的指導方針。如果你想要去爭論,那就沒完沒了了。這個人說「對」,那個人說「錯」;這個人說「錯」,那個人卻說「對」。事實上,我們對「是」和「非」全然不知!但在一個有用的、實用的層面上,我們可以說,「對」,是不去傷害自己也不去傷害他人。如此一來這才有用。
因此,到最後,規則、習俗以及解脫兩者都單純地只是法;後者是超越前者的,但彼此卻相互牽連。我們沒有法子能夠保證任何事一定是這樣或那樣的,因此佛陀說就讓它去吧!讓它不確定。無論你多麼地喜歡它或討厭它,都應該瞭解它們是不確定的。
不管時和地,整個佛法的修行是在「什麼也沒有」當中完成的;那是放棄、空、放下負擔的地方。這是終了,而不像是有人說:「幡爲何在風中飄動?我說是因爲風的關係。」另外一人說是因爲幡的關係,另一人又反駁是因風的關係,這便沒完沒了!就如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老謎題一樣,無法得到結論;而這只不過是自然罷了。
我們所說的這一切都只是習俗,是我們自己設立的。如果你以智慧來了知這些事情,你將會瞭解無常、苦、無我,這是導致開悟的看法。
你知道嗎?訓練和教導那些理解層次不同的人們是非常困難的。有些人有某些觀念,你告訴他們某些事,他們不相信你。你告訴他們事實,他們說那不是眞的,「我是對的,你是錯的 ……。」沒完沒了,如果你不放下就會受苦。我曾經告訴你們關於走進森林裡的四個人,他們聽到雞叫著:「咕、咕、咕!」其中一位就懷疑:「那是隻公雞還是母雞?」其他三人異口同聲地說:「是隻母雞!」但另一位不認同,他堅持那是一隻公雞,「母雞怎麼會這樣叫呢?」他問道。其他人就反駁說:「哦!牠有張嘴巴,不是嗎?」他們爭辯又爭辯,直到眼淚掉了下來,弄得很不高興;但最後他們通通都錯了。
不管你說是母雞或公雞,它們只不過是名字罷了。我們設立這些習俗,說公雞是這樣子的,母雞是那樣子的,公雞是這樣叫,母雞是那樣叫 ……,這就是我們爲何受縛於世間的原因了。記住這個!事實上,如果你只說那眞的沒有母雞、公雞,便結束了。在習俗眞理的活動範圍裡,一邊是「是」,另一邊是「非」,而終不會有完全的相合;即使辯論到眼淚掉下來也是沒用的!
佛陀教導不去執著,我們要如何修習不執著呢?我們修習單純地去放棄執著;但這不執著是非常難以瞭解的,必須要有敏銳的智慧去觀察、透視,去眞正達到不執著。如果你想一想,無論人們快樂或悲傷,滿足或不滿足,並不依靠他們擁有的是多或少,它依靠智慧一切的痛苦只有透過智慧,透過看清事物的眞相,才能超越。
因此佛陀告誡我們要觀察,要思惟。這「思惟」的意思是單純地試著去正確地解決這些問題,這便是我們的修行。就好像生、老、病、死,它們是最自然且平常的事。佛陀教我們去思惟生、老、病、死,然而有些人卻不瞭解這個「那有什麼好思惟的呢?」他們說。他們誕生,但卻不知生;他們會死,但卻不知死。
一個不斷觀察這些事情的人終將瞭解,瞭解之後,他就能逐漸地解決自己的問題。縱使仍有執著,如果他有智慧,並且瞭解老、病、死都是「自然之法」的話,他將能解脫痛苦。我們學習佛法就只是爲了這個 —— 去治癒痛苦。佛教的基礎原理並沒有很多,只有生和死的痛苦,而佛陀稱這爲眞理。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也是苦。一般人不認爲苦是眞理;如果我們瞭 解眞理,我們便會瞭解苦。
這種個人主見的傲慢,這些爭辯,它們沒有結束。爲了使心休息,找到安寧,我們應該思惟我們的過去、現在以及爲我們準備好的事物,就像生、老、病、死。我們如何避免被它們折磨呢?縱使我們可能仍會有些許的憂慮,如果我們觀察,一直到我們知道遵循眞理,一切的痛苦將會終止,我們便不再擁抱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