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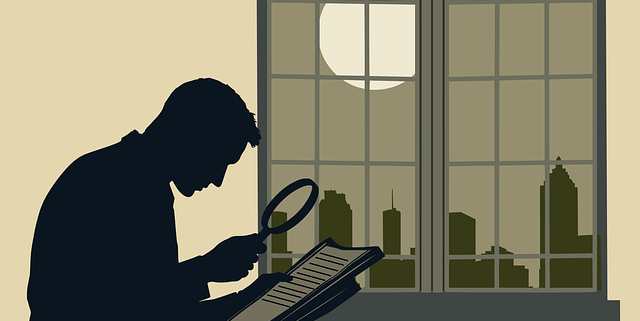
舍衛國生活物質豐富聞名,是古印度十六大國之一,比鄰於釋迦牟尼佛本生地迦毘羅衛國的西南方。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已成佛五年,與隨身衆千二百五十阿羅漢俱,遠從中印度東方摩揭陀國王舍城朝向本生地遊行而來,並已度化釋種,應出家者令出家受具足戒,應在家修菩薩行者令受在家具足戒。
釋迦牟尼佛及其隨身衆千二百五十人,雖然日中一食,樹下住塚間住,仍食住浩繁,所到之處必然是當時當地之負担,信衆若無求福利他之理念,僧團恐難以維持,求福乃佛法僧戒之基礎,失此基礎必無佛無法無僧無戒。而求福是自利利他行爲,是大乘菩薩行的標幟,釋迦牟尼佛便是實踐菩薩行以至成佛之當事人,即此身教便是菩薩行菩薩乘,誰昧此事實說菩薩乘建立於佛陀滅後呢?祇樹給孤獨園之建設建立在福德的基礎上,這是釋迦牟尼佛授意須達多長者所建,是釋迦牟尼佛建立菩薩乘的事跡,歷史變遷,佛法已滅,但祇樹給孤獨園的遺跡尚在,只可惜我們無視於此一遺跡之意義。
釋迦牟尼佛從小就已傾向出家思惟生老病死苦之眞相,及至二十九歲捨離欲患,捨家出家,夜出城門往東南方走,越過俱夷那羯國(將入滅時特地遠途跋涉來到此國雙樹林間示寂),經毘舍離國,度恆河到達摩揭陀國。此地風調雨順,人民純樸,禮敬沙門婆羅門,適合乞食修梵行,於是以王舍城爲生活中心,依止於鄰近的槃茶山,伽耶城,伽耶戶梨沙山,優婁頻螺村,尼連禪河。六年後於尼連禪河岸菩提樹下成佛,西行至波羅奈國鹿野苑度五比丘,度耶舍比丘及其眷屬,尋又回到伽耶度千二百五十阿羅漢衆,入王舍城安住塔度頻沙王,受王及迦蘭陀長者所施竹林園舍,建立了僧團制度,度迦葉,舍利弗,目揵連。佛法僧戒出現於中印度東方,只在摩揭陀國王舍城周圓鄰近的國家宣揚,尚未西向流布於他方。
此時,富商給孤獨長者從舍衛國來到王舍城,夜宿友人家,目睹友人全家大小婦孺都趁夜忙碌着打掃屋舍,備辦妙味飲食,忍不住好奇便問(見雜阿含五九二經):
「汝何所作,爲嫁女娶婦?爲請賓客國王大臣耶?」
時彼長者答給孤獨長者言:「我不嫁女娶婦亦不請呼國王大臣,唯欲請佛及比丘僧設供養耳。」
時給孤獨長者聞未曾聞佛名字已,心大歡喜,身諸毛孔皆悉怡悅,彼長者言:「何名爲佛?」
長者答言:「有沙門瞿曇,是釋種子,於釋種中,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爲佛。」
給孤獨長者言:「云何名僧?」
彼長者言:「若婆羅門種剃除鬚髮著袈裟衣,信家非家而隨佛出家,或剎利種,毘舍種,首陀羅種,善男子等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彼佛出家而隨出家,是名爲僧。
今日請佛及現前僧,設諸供養。」
給孤獨長者問彼長者言:「我今可得往見世尊不?」
彼長者答言:「汝且住此,我請世尊來至我舍,於此得見。」
時給孤獨長者即於其夜至心念佛因得睡眠。
給孤獨長者見佛心切,天還未亮就迫不及待來到佛陀住處,遙見佛陀露地經行,此時阿難等釋迦種姓兄弟親友都尚未見過佛,未出家,也沒有其他侍者隨行,給孤獨長者不知禮佛,趨前便以俗人禮節恭敬問候世尊。(雜阿含五九二經大正二册一五八頁中):
爾時世尊將給孤獨長者往入房中,
就座而坐,端身繫念。
爾時世尊爲其說法,示敎照喜已,
世尊說諸法無常,
宜布施福事,持戒福事,生天福事,
欲味欲患欲出,遠離之福,
給孤獨長者聞法見法得法,
入法,解法,度諸疑惑,
不由他信不由他度,入正法律,
心得無畏,即從座起,正衣服爲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已度世尊,已度善逝,我從今日盡其壽命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爲優婆塞,證知我。」
爾時世尊問給孤獨長者:「汝名何等?」
長者白佛:「名須達多,以常給孤貧辛苦故,時人名我爲給孤獨。」
世尊復問:「汝居何處?」
白佛言:「世尊,在拘薩羅人間,城名舍衛,唯願世尊來舍衛國,我當盡壽供養衣被飲食房舍床臥隨病湯藥。」
佛問長者:「舍衛國有精舍不?」
長者白佛:「無也,世尊。」
佛告長者:「汝可於彼建立精舍,令諸比丘往來宿止。」
長者白佛:「但使世尊來舍衛國,我當造作精舍僧房令諸比丘往來止住。」
由此經文而可證知,佛法尙在發源地摩揭陀國時,佛陀最初單獨爲給孤獨長者說求福之事,這是菩薩乘自利利他之法,設若給孤獨長者無菩薩心,供養佛及千二百五十僧衆一日食都難,遑論建設祇樹給孤獨園,盡形壽四事供養。今有祇樹給孤獨園之事跡,學者對菩薩乘法出自佛說無庸疑慮。向來聲聞法及菩薩法重疊,並無二法二致,見小見大都只是學者「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循業所見解。佛法隨順時代變遷變質,是時代文化思潮變易,隨其變易而曲解佛法,並非佛法順應時代文化背景由凡夫自創進步的大乘經典,雖然也有惡人存心偽造佛經以惑世人,不可因此否認佛說菩薩乘。
釋迦牟尼佛授意給孤獨長者建造精舍後,差舍利子佐助其事,此一事跡由給孤獨長者向舍利子所自述,記載於中阿含二八經,大正一册四六〇頁下:
我於爾時聞佛所說,善受善持,
即從坐起,爲佛作禮繞三匝而去。
於王舍城所作已訖,與尊者舍梨子俱往,至舍衛國不入舍衛城,亦不歸家,便於城外周遍行地,爲於何處往來極好,晝不喧鬧夜則寂靜,無有蚊虻亦無蠅蚤,不寒不熱,可立房舍施佛及衆。
尊者舍梨子,我時唯見童子勝園往來極好,晝不喧鬧夜則寂靜,無有蚊虻亦無蠅蚤,不寒不熱,我見此已便作是念:「唯此處好,可立房舍施佛及衆。」
尊者舍梨子,我於爾時入舍衛國竟不還家,便先往詣童子勝所白曰:
「童子,可賣此園持與我耶?」
爾時童子便語我曰:「長者當知吾不賣園。」
如是再三白曰:「童子,可賣此園持與我耶?」
爾時童子亦復再三而語我曰:
「吾不賣園,至億億布滿。」
我即白曰:「童子,今已決斷價數,但當取錢。」
尊者舍梨子,我與童子或言斷價或言不斷,
大共紛訟,即便俱往至舍衛國大決斷處判論此事。
時舍衛國大決斷人語童子勝曰:
「童子已自決斷價數,但當取錢。」
尊者舍梨子,我即入舍衛國還家取錢,以象馬車舉負輦載,出億億布地,少處未遍。
尊者舍梨子,我作是念:「當取何藏,不大不小可此餘處,持來布滿?」
時童子勝便語我曰:
「長者,若悔,錢自相歸,園地還吾。」
我語童子:「實不悔也,但自思念當取何藏,不大不小,可此餘處,持來滿耳。」
時童子勝便作是念:「佛必大尊,有大德祐,法及比丘衆亦必大尊,有大德祐,所以者何?
乃令長者施設大施,輕財乃爾,
吾今寧可即於此處造立門屋施佛及衆。」
時童子勝便語我曰:「長者且止,莫復出錢布此處也,吾於此處造立門屋施佛及衆。
尊者舍梨子,我爲慈愍故,即以此處與童子勝。
尊者舍梨子,我即於此夏,起十六大屋,六十拘絺(小房)。
文中童子勝就是祗陀太子,勝是祗陀的中譯。童子勝園就是祗陀園,祗陀太子私有的林園。祗陀太子是舍衛國波斯匿王的皇太子,深受給孤獨長者大布施之感動,於是合作建設園林以用供佛及僧衆,取名「祇樹給孤獨園」。
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釋迦牟尼佛回到本生地迦毘羅衛國後,宣揚佛法的中心,佛經中最常看到的說法處,便是「祇樹給孤獨園」,我們記不住經文,也不知法非法義非義,却牢牢記住祇樹給孤獨園。
我喜歡朗誦阿含經,往往脫口而出只誦到「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到此而住,奇特的名詞,奇特的音韻,不免留駐於此,回味又回味,「給孤獨」不就是布施的異名嗎?不就是福的異名嗎?祇樹給孤獨園不就是求福的事實嗎?祇樹給孤獨園不就是求福不厭倦之園林嗎?住此園林中之僧衆若不是求福之衆,豈不慚愧?從此園林中流布出來的佛法若不是自利利他求福之法,豈非母牛不出牛乳?
我頷首,我肯定不疑,由於有求福之事乃孕育出佛法僧戒,佛法的本質就是求福,祇樹給孤獨園的事跡彰顯此事,我們不承認佛法是菩薩法只是自我障礙,不承認菩薩法出自釋迦牟尼佛,只是昧於事實畢竟不害佛法的本來,不害釋迦牟尼佛歷劫求選擇(雜阿含一〇〇經)而成佛之事實。
有問菩薩法若出自釋迦牟尼佛說,阿含經中何以沒有菩薩名?當知,經典結集是人爲編輯,分門別類,路歸路,橋歸橋,世尊入滅後知法見法者也相繼入滅,循業所見,見小見大對立紛諍,編輯經典之內容,語文使用,都已有人爲刻意之企圖,流布佛經便也是見取我知我見,南傳沒有菩薩法就是刻意見取使然。若不劃地自限,並非阿含經中都無菩薩名,四阿含中之增一阿含經便遍處有菩薩名,菩薩法,菩薩行,如增一阿含經護心品之五,大正二册五六五頁上: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阿那邠持長者便往至世尊所,
頭面禮世尊足,在一面坐。
世尊告曰:「云何長者,貴家恒布施貧乏耶?」
長者對曰:「如是世尊,恒布施貧乏,於四城門而廣布施,復在家中給與所須。
世尊,我或時作是念:『並欲布施野飛鳥猪狗之屬。』
我亦無是念:『此應與,此不應與。』
亦復無是念:『此應與多,此應與少。』
我恒有是念:『一切衆生皆由食而存其命,有食便存,無食便喪。』」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長者,汝乃以菩薩心,專精一意而廣惠施,然此衆生由食得濟無食便喪。
長者,汝當獲大果得大名稱,有大果報,聲徹十方得甘露法味,所以然者?
菩薩之處恒以平等心而以惠施,專精一意念衆生類由食而存,有食便濟無食便喪,是謂長者,菩薩心所安處而廣惠施。」
爾時世尊便說偈曰:
盡當普惠施,終無恪悔心
必當遇良友,得濟到彼岸
「是故長者,當平等意而廣惠施,如是長者,當作是學。」
爾時長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文中阿那邠持長者就是給孤獨長者,釋迦牟尼佛所稱讚之菩薩。釋迦牟尼佛授意給孤獨長者建設的祇樹給孤獨園,如今遺跡尚在,佛法的遺跡便也尚在,學者莫待遺跡消失,空遺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