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在坐中觀的時候,即是集中心力在思考的時候。佛法中的苦、集、滅、道、緣起、四念處的道理,都有它們一定的理路。待能觀的作用凝集了,我們即可依著所理解的理去觀、去思考、去分析。這個時候,我們會更順暢且親切地領悟其道理。
修行的心態與觀念
倘若這時我們觀察妄念,也可以從妄念的流動中,明白更多的佛法或佛陀所要告訴我們的正見。因此,理必須通過實際的修行才能深入。我們要真正地領悟佛法,不只在行動上要去實踐,內心也要深細地去思考;然後還要不斷地熏習,法的力量才會愈大而有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才有能力依法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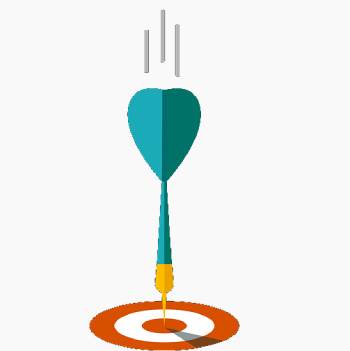
當佛法成為我們思想的主流,我們在觀念上就會有很大的改變,生活也會隨著調整。
我們的行為,也會很自然地與佛法相應。修行,就是要修我們的心。調心工夫做得好,修養也會跟著提昇,這些都會在生活中自然地流露出來。我們的修行工夫到哪裡,是可以從自己的行為反映出來的。
有時候我們的正念會被煩惱覆蓋,比如本身沒有這樣的工夫,卻要撐門面告訴別人自己有這樣的工夫。這種煩惱是與癡心所相應的,當然間中也包含了貪。我們貪染世俗的某些利益,比如名聞利養之類的好處,所以要撐場面讓別人認為自己很有修養。我們只有兩分的工夫,卻要表現出五分或七分,剩下的幾分都是假的。然而這種現象能夠維持多久呢?
像臺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一些用空油桶撐起來的房子,很快就倒塌了也一樣,如果你用太多這種「空油桶」撐著,別人稍微「震」你一下,你就倒了。你認為自己很有修養,但是別人說你兩句,你的空油桶很快就跑出來了。因此,修行工夫是不能用撐的。不過,有時是因為我們對自己不了解,所以常常誤以為自己達到什麼境界了。這種情況在佛法裡稱為「增上慢」,屬於一種慢心。
有人靜坐不久,覺得好像有點動靜了,就以為自己「悟」了,應該是初禪了。這種經驗多了幾次之後,他就想:「這是第四次了,應該是四禪了。」也有人以為自己證到什麼果位了。他們在不知的情況下,誤以為是,然後到處宣揚自己的境界怎樣怎樣了。為什麼四處向別人說呢?因為想要表現自己的境界比別人高。坦白說,能夠講得出來都是一些淺淺的東西。倘若我們真正能夠用到很深的工夫,別人問到時,我們是很難用語言文字清楚地傳達那個境界的。
其實打坐中出現的狀況,可以找老師談談或和朋友切磋,了解朋友在打坐時是否也有這些狀況?知道它們只是一個過程,最好放下,不要那麼執著。如果你喜歡四處講,講多了會愈來愈執著、喜歡那種境界,那時你就很麻煩了。一方面你不會再進步,另一方面你會繼續加強它。而你在加強它的時候,也只是在原地跑步。你叫自己快!快!快!但是,你跑來跑去還是在原地,並沒有走動。你只是把動作弄大一點,以為自己愈修愈好了。其實你在和別人說的時候,即不斷地與慢心、貪心相應。你愈講,執著就愈深,境界也愈容易出來,因為你已經變成慣性了。
你一打坐,要氣動,它就可以動得很開心,然後你就可以和別人說:「我今天又這樣動了。」明天你如果有另一種動作出來,又可以告訴別人。但是,你這樣動來動去又怎樣呢?我們是在「靜坐」,不是在「動坐」啊!如果你的體內有氣在動,最後還是要讓它靜下來的;氣順了以後,就會靜下來,氣不順才會動。身體調得好,色身會轉化、氣會順,這時氣就不知跑到哪兒去了?打坐不需要用到氣,因為不是在練氣功啊!
一個人的工夫到哪裡,它會自然地流露,不需要覆蓋什麼,但也不需要裝飾或到處向人炫耀。你的工夫用得好,別人如果要學習,你懂的就教他;而你告訴別人的,是一些比較普遍性、共通性的修行過程。像智者大師的著作裡,即提到一些普遍性、共通性的善根發相與惡根發相。你在對別人解說修行所會出現的情況時,有一部分可能是你自己的經驗,有一部分是你與別人切磋時知道的,還有一部分是你從經典或論著裡所理解的。我們常常喜歡向他人炫耀自己的工夫,其實能夠不談,最好少談一點。除非對自己的一些過程不是很清楚,才請教別人,大家互相切磋、了解,也是一種向上進步的方法。
修行是很内在的修養,不是屬於向人炫耀的東西,所以我們在用功的時候,應該只是很單純地用功。修養到哪裡,它很自然地就會流露出來。至於裝飾出來的東西,很容易就會讓人揭發的。比如有些女生打禪七時,晚上洗臉後就不敢見人,如果早上要三點起來,她一點就要起來了,在臉上塗塗畫畫一番,才敢出來。如果晚上十點休息,她則要到十二點或一點才能睡覺,因為她要一層一層地將它們洗掉啊!其實何必這麼辛苦呢?晚上捧一把水,洗個臉就可以去睡覺了;早上再捧一把水,就可以出來了。在禪堂打坐就要清純一點嘛!但是,我們都不喜歡自己的「本來面目」,要塗它、畫它才甘心。
因此,用功前的心態與觀念很重要。基本的正知見或觀念具足了,我們在生活中再不斷地去調整自己的言行,盡量與法相應,這就是我們的修養。在修行的過程中,我們常常會看到自己的弱點,正確的心態與正知見,能夠幫助我們漸漸地走上正軌。
專注與覺照,相互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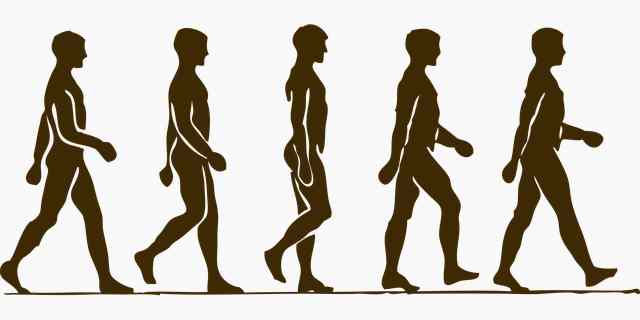
在打坐的時候,當心力加強了,你就能夠有自主的力量,觀想的工夫也會加強。
然而很多時候你坐在那裡,卻不知道要觀想什麼?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你對佛法的掌握不是很清楚,就不知道該如何觀起?而這種觀還是屬於理觀。但理觀也是有作用的,你從理一直觀下去,慢慢地就會了解到諸法的本性。實際上理就是在傳達這個訊息,你要見到本性,就要通過這個理。
然而理還是理,你要以理去印證事、從事來印證理,才能真正地見道,也才能體會到更深一層的法義。在過程中,你會發覺自己的心愈來愈接近法;在生活中,你也會表現出順於法性的行為。當你的心住得比較深、比較沉時,心會有一股力量,很自然地就會遠離惡行。
從經典中,可以看到證初果的聖人一定遠離殺生。經典裡說,他們在鋤地時,蟲兒一定離開他們四寸。所以修行修得很好或是證到果位的人,在外面用功打坐是不用擔心的。你卻會感到害怕,為什麼呢?因為怕「好朋友」—— 猛獸或蟲蟻來找你;你害怕,是因為有太多的罣礙,太多的執著,太多的瞋心。
禪師們不會擔心這些東西,他們的心靈修到那種境界時,就會有一種感應。他們可以跟這些猛獸在一起,因為他們沒有傷害牠們的心。而你呢?一看到這些猛獸就害怕,就想要自衛。當你生起害怕、恐懼的念頭時,動物們也會感受到,所以牠們會先攻擊你來保護自己。這和我們一般上看到的情況是一樣的:愈沒有安全感的人,愈容易侵犯別人,即所謂「以攻為守」。所以你的心靈修養到什麼程度,它會直接地反射到外面。你要不斷地修行,對法有更深的體會,你的觀念才會明確,知見才能與法相應;然後你的心靈空間會愈來愈廣,修養也會愈來愈高,它是這樣一直上去的。
然而人卻習慣不斷地攀緣,要求這個、要求那個,攀緣的心總想抓一點東西。比如開始用功時,就抓呼吸,若不抓呼吸,心便不知道要放到哪裡去;然後又怕抓不穩,就用數目字來幫自己抓穩一點。抓一次、兩次、三次,慢慢地它穩住了,就可以放掉數目字而只抓呼吸。但是,有些人一放掉數目字,呼吸又不穩了。這是因為心不穩,所以呼吸也跟著抓不穩。
倘若你的工夫用得好,呼吸會愈來愈細微,你會發現呼吸的進出還是一種動。當你的心想靜下來時,可以在意念裡把它觀想成一個點或一個境,把心安住在那裡。但是在用功專注時,心有時也會感覺到很茫然、很空洞,坐到好像失去了什麼似的。於是它會想抓一點東西,你就再找回自己的呼吸,把呼吸弄粗一點,繼續數呼吸。我們的心習慣了要抓東西,沒有東西抓時,就不知道要做什麼?抓的東西太小,看不清楚,就找大一點的東西來抓。
在日常生活中,你常抓什麼呢?你習慣抓這個、抓那個,這個也要、那個也要。你以為你抓的都是這些東西嗎?不是的,你抓的是自己的欲望。你内心的欲望想要這個東西,你就去抓,所以你攀緣的都是外在的東西,而且是用你的心、你的貪欲、你的煩惱去攀的。現在你要慢慢地調整,學習放掉一些東西。方法很簡單,就是守住你的呼吸,然後守住止靜。你覺得安止在那個點的時候,心很穩、很充實,不會想要再找什麼東西來填補,就繼續止靜在那個點上。如果你的心穩住了,專注的作用與覺照的作用會結合,你就這樣安住在一個境上,繼續用功。
倘若你專注的作用愈來愈強,覺照的作用比較弱,就會慢慢地進入到比較深的定。但是,如果專注的作用與覺照的作用保持均等,專注的作用會幫助覺照的作用進行觀照,兩者還是可以定型發展的。因此在禪定方面,佛教比較重視四禪,因為四禪是專注和覺照作用皆均等。我們還沒有進入色界定之前,覺照的作用比較強,還會一直在覺照外境,一直在攀緣。
所以我們在觀察妄念或思惟義理時,還是在欲界裡,欲界裡的覺照作用才那麼活躍。待你進入禪定時,它就不再那麼活躍了,但是作用還在,還是可以依一心的禪定提起覺照的作用進行觀想。在這個時候,不管你是觀當下的境界或是觀法性,都會很有力量。但是,如果你進入更深的定,覺照的作用會減弱,不容易做觀想了。
另一種會障礙我們修行的現象是昏沉,而最初出現的昏沉是比較粗的。比如你打坐時打瞌睡,身體在那邊晃動,這很容易看得出來。多數是你平時沒有調好,睡眠不好或是一種慣性。但有時它只是一種過渡的情況,尤其在吃飽後會很想睡,所以午餐過後的第一支香,可能會比較昏沉,第二支香通常就會好一點。如果你感到昏沉,不要和它對抗,就好好地沉一下,專注地睡一覺;醒過來時,這種現象可能就會過去了。昏沉有一個過程的,有時候你也可以在這段過渡時間裡去對治它。當有一些徵兆讓你知道自己差不多要睡著了,就把念頭提起來,讓頭腦活躍。
有時坐到第三、四支香還是會昏沉,為什麼呢?因為身體太累了。如果你的工夫用得不是很好,會消耗很多體能的;體能消耗多了,身體就會累。這時如果你能夠躺下來睡,全身放鬆,那是最舒服的。但是,在禪堂裡打坐就沒辦法了。你就坐在那裡「點」幾個頭,好好地沉一下,它就會過去了。這些比較粗的妄念或昏沉,是可以調的。
然而有的人只要一上座就昏沉,這和他的身體狀況有關係。有的人因為生活或工作壓力大,身心各方面都很緊繃。即使在睡覺時,他的身體還是繃住的,晚上常做夢,只是淺淺地睡著。隔天起來要做事時,他就亢奮;一亢奮,人就更緊繃。讓他休息睡覺,他又不能好好地睡。這種現象,需要長時間從生活中去調整。因此,要睡得好,就要心情平和,身體放鬆。
還有一種放鬆的方法,是晚上睡覺前,按摩你的全部腳趾,讓它放鬆。身體最緊的部位就是腳趾,腳趾放鬆了,人就會放鬆。曾看過一些報告,指出人在睡覺前穿上襪子五至十分鐘左右,讓腳保持一點溫度後再脫下來,就可以睡得好。其實中國人很早就一種很健康的養生療法 —- 泡腳,很多老人家在睡覺之前,腳都會泡溫水,以幫助睡 眠。睡眠調得好,昏沉現象就會減少。
你的工夫用得好,昏沉的現象也會減少。但是,有些昏沉是在工夫用得好時才出現的。比如到了某個階段,你專注的力量太強了,會忽然失去覺照的作用,心一下子沉下去或「掉」一下。這是工夫用上去時才可能發生的現象,工夫用不上去,就不會有這種情況。而且這種情況過了之後,你並不會感覺累或疲倦,人還是滿有精神的,因為剛才你很專注。但是,基本上你的工夫還是沉的,只是在那個時候失去了覺照。在用功的時候,專注的作用與覺照的作用要互相配合。然而有時因為你有太多的雜念,一直設法要把心拉回到方法上,就不斷地加強專注的作用而一時失去了覺照。
倘若你在數息時會昏沉,這種昏沉多數是比較粗的。當你放下數息,隨息一段時間之後,你可能會忽然間「掉」一下,好像睡著了又醒來。你知道自己是有用上工夫的,只是一時失去覺照的作用;沒有這個覺照的作用來支援著身體,身體就會「掉」一下。只要你繼續用功,這種情況會慢慢過去的。
昏沉在出現之前,有時候會有些徵兆,但是因為它來得太快了,所以你無法覺察到。幾次之後,你繼續專注,慢慢地提起覺照的作用,它就會過去了。這種沉不是昏昧,它只是屬於失去覺照的一種情況。如果身體平時沒有調好,調身與調心的工夫不能配合得很好,心會對身體失去覺照的作用,身體就會「掉」一下。如果身體平時調得很好,數呼吸的方法也用得很好,工夫就會穩穩地一步一步進去。
其實數呼吸的方法,可以幫助人不斷地提起覺照的作用,進入隨息。但是,如果你常常會在專注的時候失去覺照的作用,再繼續用功下去,可能就會進入無想定,心會陷入一種無記性的狀況。這是與癡心所相應,是不理想的。這時你的心失去了覺知,好像什麼都不知道,沒有分別的力量,觀想的作用提不起來。不只深定會這樣,有時在一些不是很深的定境中,也會出現這種茫然的情況。因此在用功時,一定要不斷地提起覺照的作用。
你是依覺照的作用或正在觀照的那個境去做觀想的,觀想是一種思惟的作用。如果你是依一心的禪定來用功,它就不同於一般的思惟。一般上只是聞、思,但是如果你的思惟與禪定相應,就進入到修慧的階段。也就是說,在這個階段你已具備了正見,能夠擇法、分辨;從比較粗的善惡,慢慢地分辨到比較微細的部分,那即是法性。
從生滅中領悟無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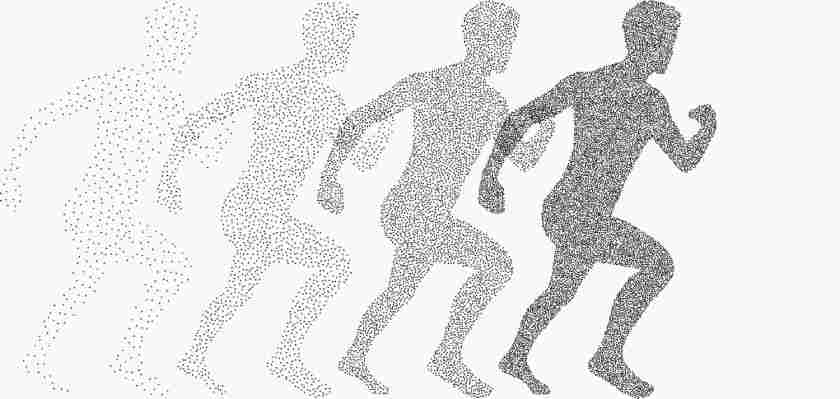
在佛陀時代,一些哲學家或是外道都有非常精細的思惟,他們都有一些智慧。
但是,佛陀認為這些都是不究竟的,因為他們沒有見到法性。這些人如果向佛陀修學,只要不是很好勝或好辯,佛陀稍微點醒一下,他們很快就明白了。有些很好辯的人常常喜 歡和佛陀辯論,佛陀並沒有和他們辯解,只是告訴他們一些道理,他們聽了便有所領悟。尤其是一些婆羅門教徒,常常和佛陀談理論,佛陀每每只是三言兩語就將他們的問 題解決了,或把他們那種很微細的不正見糾正過來。這些人,很多就這樣皈依了佛陀。
只要我們依法而修,在思惟過程中,即能愈來愈進入深細的部分,然後去抉擇、分辨。一開始觀想時,我們會比較注重在理路,然後用事相去印證。但是觀到最後,一定要契入到理的中心,即所謂的法性。我們從觀心不淨、觀心是苦,明白了佛法的基本正見:有善、有惡,有業、有報,有過去、有未來,有凡夫、有聖人。我們要從凡夫進入聖人的道路,就要從流轉門轉入還滅門;而要轉入還滅門,一定要進入到法性的觀想。
法性的觀想,是以無我為中心。一般上我們不容易直接去分析無我,而會先從無常入門,所以觀心無常、觀心無我。世間一切都在變化,平時我們看到的無常,它的變化都是比較明顯的,但是有些變化卻要等到發生一件突變性的事情時,我們才會知道什麼叫無常。
我們總會覺得自己好像沒有什麼改變,實際上我們每年、每天都在改變,你每年拍一張照片來對比一下就知道了。不過,現在的拍照技術愈來愈好,可以把照片修美一點。比如現在的新人大都會拍結婚專輯,照片裡的新娘,眉毛修得細長,對照本人看一下,好像不是她。不知是人比照片美?還是照片比人美?哪一個比較美?不敢講!如果講照片比較美,意思就是新娘本人不美,所以修得比較美一點了!所以有時候我們知道她有改變,但是不太能看得出來;或是幾年沒見,一看:「哎喲,怎麼老了那麼多!」可是我們不要忘記,當別人衰老很多時,我們也是一樣變老。我們常常只看到別人老,卻看不到自己老。我們的身心一直都在變化,心的變化比身體的變化更快,但是不容易覺察到,因為我們有所執著。
無常是一種相續性的變化過程,它前前後後、生生滅滅,都有相續的作用。我們可以拿一根蠟燭來做比喻。蠟燭在燃燒的過程中,看起來好像變化不大,其實它一直都在變化。如果我們把它切段,後一刹那的蠟燭,已經不是前一刹那的蠟燭了。但是後一剎那的蠟燭,卻又不能離開前一刹那的蠟燭,因為它們前後有著相續的作用 —- 前一刹那過去了,才把後一刹那推出來。
所謂「等無間緣」的作用,主要是指我們的心在思考或運作時,一個推一個生滅、生滅。比如水的流動,我們可以看到後浪推前浪,後浪被後後浪推,前浪又推前浪的現象。它們一直相續地推動著,沒有一個不變的個體,只有連續不斷地生滅變化。我們看、看、看,還悟不出無常,有善根的人就知道這是無常,他可能就開悟了。又如聽水聲,嘩啦…… 嘩啦 ……,好像只是一個聲音。其實在那個聲音裡面,有著許多前前後後的聲音。如果我們聽雨聲的時候,只是用耳根聽,不用心去分別,便會聽到聲音真的是一個一個滴滴答答的。聲波的波動也是如此,若我們能夠在那個時候聽得到,就悟無常了。如果用心去分辨,我們的分別心會連貫過去、現在、未來,連貫成一個聲音,我們就會好像只是聽到一個聲音。如果只是用耳根去聽,耳根的作用是刹那剎那的,我們便能夠聽到刹那剎那的聲音,就會比較明白無常。
在觀呼吸或經行的時候也一樣。我們通常是觀站立的那隻腳,另一種方法是觀移動的那隻腳。起先我們觀腳一步一個生滅,然後從比較大的生滅再去看比較小的生滅。腳提起來,就是一個生滅;向前放,也是一個生滅;踏下去時,又是一個生滅。我們繼續慢慢地走,就會愈來愈細;若我們只是快步地走、走、走,是看不清楚的。拜佛時也一樣,如果我們的心很細,會看到自己的動作其實是一個一個連貫起來的。
我們在覺照的時候,往往只是覺照到動作而已,並沒有把法放進去。我們要在覺照之中就去觀想法,才能夠看到它的生滅;然後從生滅之中,去明白無常、印證無常。如果只是看到事物發生的過程,這是覺照的作用而已。我們要在事物發生的過程中,見到它的生滅,再從生滅中去領悟無常;或用無常的理來印證這個事物的過程是無常的,那才是觀想。因此,觀想的背後一定要有法。如果我們在觀照時,只是看到動作或聽到聲音,這還是眼根、耳根或身根的作用而已。這只是覺照的作用,還不是真正的智慧,要再進一步去觀想。
有些人又以為覺照到妄念的生滅、呼吸的生滅、動作的生滅,就是覺照到當下的因緣了。其實我們無法覺照到真正當下的因緣的,除非我們的心很細。當你的心很細時,就可以從事物的過程中,看到一個剎那、一個剎那的生滅變化。這時,你必須以無常、無我的道理來印證事。
從無常之中,我們可以看出為什麼一切相不斷地在變化?因為它是因緣和合的,所以一定會變動。於是你明白了無我,再用本性來印證,才是真正見道,才是觀想。觀想到很細時,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契入當下那個刹那;證道之後,就是真正出世間的智慧,真正證到無我。
我們在觀想的過程中,可以用無我的法性來印證現象,或用現象來印證法性。這樣理和事互相印證,會發覺到理和事愈來愈接近;當它們完全契合時,我們就悟道了。悟道是一個質變的過程,非常迅速地過去。此後就不會再退轉了,因為我們已經跨過生死心、流轉心的範圍了。此時我們的心才是真正活在當下,安住在每一刹那的因緣裡。因緣在剎那生滅的過程中,生滅生滅,非常快速。前一個因緣滅了,在現象上的運作裡,它會一直繼續推延。但是,我們的心不住過去、不住未來,就只是安住在當下的因緣或當下那個剎那,不會期盼下一個剎那,因為當因緣具足了,下一個剎那自然會顯現。過去的那一刹那一過,我們的心就捨掉了;滅而不再生,我們才不會繼續流轉。
但是由於我們的心比較粗,因此所觀照的,都已經是過去的動作。所以在拜佛時,看到的都是過去的動作,怎麼活在當下呢?而我們卻以為這就是活在當下了。我們把整個拜佛動作當成是一個現在,以為看到的都是現前的因緣。不過,當我們的心專注到很細微的時候,真的可以看到每一個動作,會感覺自己的心與動作是一致的,念頭與行為好像是靠在一起的。這時我們會有相當好的定力,但是還要再進一步去觀本性;不觀本性,就不能夠真正地覺悟。這個階段,覺照的作用與專注的作用很敏銳。我們的每一個動作在運作時,心念與動作是一致的。當我們的定力發揮它的作用時,去觀無常、無我、空,就能夠悟道。
我們現在還是在訓練的階段,當自主的力量和能觀的作用加強時,就可以從現象中去觀。一般上我們在這個時候所住的境會比較深,倘若這時我們聽聲音,會感覺它不是外在的聲音,而已經變成我們意識裡的聲音。如果我們聽到的還是外在的聲音,那是不能入定的。不管觀什麽,觀聲音也好,觀呼吸也好,我們所緣的境一定要從「外所緣」慢慢地轉入「內所緣」,才能夠進入定。
但是,一般上我們習慣要攀一樣東西,所以開始觀的時候,所觀的境是依前五根。我們觀呼吸是依身根的觸覺,這還是外在的。當我們觀到比較細的時候,會感覺這個呼吸好像不是身根的作用,在意識裡面就有呼吸的作用;或者在止境時,會感覺到這個點不在鼻子了,它已經變成意識裡的一個影像。如果我們已經安住在內所緣,就可以觀念頭的生滅。
從生滅中領悟無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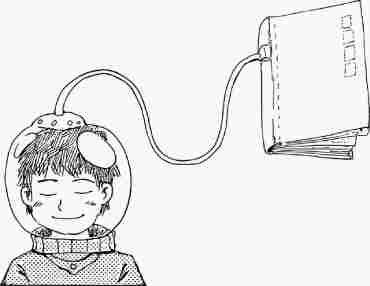
緬甸的禪法中,有一種觀色聚的方法;它把身體的色法分成幾種。
觀時是用意識去觀,是一種非常微細、複雜的觀法。它先分析地、水、火、風,再去觀色、聲、香、味、觸。這種禪法的主要目的在破我執,每一個顯現的因緣都是一個組合體。如果你能夠這樣分析身體,最後會發現它是無常、無我的。
我們進入止的時候,就可以觀法,觀心所緣的法塵是無我的,即觀法無我。觀每一個念頭都是一個組合的作用,都是無常的。你把心的生滅觀得非常細,就可以看到它組合的作用。每一個認識的作用生起來,都包含了種種心識、意識的作用,是一些心所法組合起來的作用。這樣剖析到最後,會發現它沒有一個中心,也沒有一個不變的作用。比如一棵芭蕉樹,你一層一層地剝它的樹皮,剝到最後,看到它沒有一個中心,就會明白無我的道理。
你要依本性修、觀想本性,在法或理方面就要很穩。如果你的知見不具足,是觀不進去的。你要先從聞思,去明白真諦法是無常、無我,以空為中心的。佛法所講的法性,並不是本體。一一法含有本性,一切法也含有本性,而一切法的本性和一一法的本性其實是一樣的。
你觀法性,就是在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就是在觀本性。你要清楚地觀到本性,就要對理、知見有很明確的概念。因此,修行不是坐著起觀就可以成就的,一定要有聞思 做為前提。從聞思去分析這個身心是五蘊(色、受、想、行、識)和合的、五蘊是空的,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你再分析身體色聚的作用,然後把它們全部分開,沒有一樣東西是所謂的我,就能理解空的道理。也即是先通過聞思建立正見,然後再依一心的禪定,用事來印證聞思所明白的理,或用理來印證事;慢慢地理和事愈來愈契合,達到無礙的境地時,你就真正證到事理無礙的智慧。
你要觀無我,一定要對理有透徹的了解。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邊想:「無我…… 無我…… 」這樣做是觀不進去的,因為你背後沒有一個可依止的理。在進入觀想時,你不是在分析無我,而是知道無我就是法性,然後用這個無我的理來印證所觀的境,或用所觀的境來印證無我的理。這樣的觀法,才是觀想。只要你的工夫做得紮實,即使沒有真正地證到,你的觀念也會慢慢地改變、提昇。而在過程中,你不斷地分析無我的道理不斷地熏習,你的心會與理愈來愈靠近;當你對理愈來愈有把握時,生活上的許多問題就可以調整過來了。這就是智慧,但它還不是出世間的智慧。
有了智慧,我們在判斷事情或採取行動,會和沒有智慧時的情況不一樣。比如從十二因緣,我們知道觸在運作之前需有六入(又名六處,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或「色、聲、香、味、觸、法」六塵;六根為內六入,六塵為外六入),而六入裡面有名色,名色裡面有識,它們組合起來便形成生命的個體。我們的前五根緣外 塵,緣了之後會有作意的作用。根、境、識和合便形成觸,觸就會產生受。
如果你在觸境時是與無明相應,無明緣行,接下來就愛、取、有、生、老死;如果是與智慧相應,當下無明滅、行滅,其他也都會跟著滅了,受、愛、取、有的作用就不會生起。在觸的當下,眼根觸到外塵所生起的眼識就不是眼識,而是智慧,即所謂「轉識成智」智慧照見所有作用組成之後所顯現出來的事相,同時見到這個事相的本性。如果當下一切都滅了,流轉也就滅了。
雖然我們的智慧還不能停止這種流轉的作用,但至少可以讓它的作用緩慢下來,或不會那麼有力量。平時我們一觸境,動作滿快地就跑出來,因為它是由無明引導的,所以這個動作一定和煩惱相應。現在你一觸境,覺照的作用立刻生起來,發覺煩惱生起了,就用智慧來觀照它,就可以慢慢地調伏煩惱。
有時候,你一觸境產生了一些問題,因為定力不夠,沒有辦法生起智慧來觀照它,就回到你的呼吸,觀察呼吸也是一種方法。無論發生什麼事,當你感覺情緒很波動,就回到你的呼吸,注意你的呼吸,慢慢地吸進去,再慢慢地呼出來。這樣調和數次,你的呼吸會漸漸緩慢下來,心跳也會減慢。呼吸,反映了人的身心狀況。當呼吸調和了,心也會慢慢地調和,這時你處理事情的方式就會不一樣。
覺照的作用與觀想的觀念,能夠幫助我們在觸境時提起一顆明覺心。如果我們能在生活中常常這樣去修,就可以減少流轉的作用,這就是止和觀。注意呼吸、回到呼吸,就是止;心平和了,便可以進一步去觀照。
我們常常因為煩惱太多,心被它蓋住了,所以心力提不起來。我們要長時間不斷地行,訓練自己的心,心才會愈來愈敏銳,自主的力量才會愈來愈強。這時你對現前的因緣就能夠看得比較清楚,便能減少製造惡業。少造惡業,你在打坐時就不會有那麼多妄念;妄念減少了,你的心就可以調得更好。當你回到生活中,再減少造惡業,它就形成了一種良性的循環。
因此,修行不是你坐在那裡,等著入定、等著開悟:「悟境為什麼還不來?為什麼我還沒有開悟?我怎麼還沒有進入初禪?」一直等 ……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呢?禪宗有一句話說:「等到驢年。」為什麼說等到驢年呢?因為十二生肖裡面沒有驢。你要不要等到驢年?就看你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