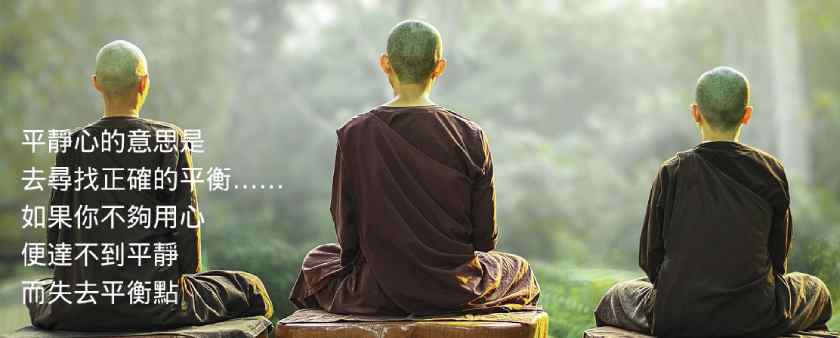
平靜心的意思是,
去尋找正確的平衡。假使你太過於強迫心,它會太超過;如果你不夠用心,便會達不到平靜而失去平衡點。
通常,心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時地在動搖,可是,卻缺乏力量。使心有力量和讓身體有力量是不同的。要使身體有力量,我們必須做運動,去逼它,以使它健壯。可是,使心健壯的意思是,使它平靜,不去胡思亂想。對我們大部份的人來說,都不曾平靜過。心不曾擁有三摩地(註)的力量,因此,我們要在一個範圍內將它建立起來。我坐於禪坐中,與「覺知者」同在。
註:三摩地(samadhi),是專注於平靜的狀態,是由禪修中所得的結果。
假使我們強迫我們的呼吸,使它太長或太短,我們就不平衡,心也不會變得平靜。就好像我們初次用裁縫機一樣:在我們實際看到東西以前,剛開始,我們只練習去踏那部機器,以使我們的步調正確。追隨呼吸也近似於此,我們不要去在意它是長或短,是強或弱,只要知曉就好。我們就讓它順其自然,追隨自然的呼吸。
一旦平衡時,我們以呼吸做爲我們的禪修對象(所緣境),當我們吸進時呼吸的開始是在鼻端,呼吸的中間是在胸部,呼吸的結尾是在腹部,這是呼吸之道。當我們呼出時,呼吸的開始是在腹部,中間在胸部,結尾在鼻端。我們只要知曉呼吸之道在於鼻端、胸部和腹部,然後在腹部、胸部和鼻端。我們知曉這三點,爲的是要使心堅固,去限制心的活動,使正念和自我的覺醒能夠輕易地生起。
當我們熟練於知曉這三點,而可以放下它們並且知曉出入息,以及完全專注於鼻端和氣息出入的上唇時,我們就不需要去追隨呼吸了,只要在我們前面的鼻端建立起正念,並且在這一點上知曉呼吸 —— 進、出、進、出。不需要特別去想些什麼,現在,只要專注在這簡單的工作上,繼續保持當下的心。只有出入息,除了這些外,沒別的了。
不久,心就會變得平靜,呼吸會變得細密,身、心也會變得輕安,這就是禪坐功夫的正確狀態。
坐於禪坐時,心變得細密了,不過,無論我們是在什麼狀態裡,我們都應該設法去覺知它、認知它。在那裡,心的活動和平靜是在一起的,那兒會有「尋(vitakka)」。「尋」是將心帶到思惟(觀)的主題上的行爲。如果沒有很強的正念,就不會有很強的「尋」。接著,「伺(vicara)」—— 環繞在那個主題週圍的思惟(觀),會緊接而來。種種「微弱」法塵會一而再 地生起,可是,我們的自我覺醒是樁很重要的事 —— 不論發生什麼,我們都繼續不斷地覺知它。當我們進入更深層時,仍要繼續不斷地覺知我們坐的狀態,覺知心是否穩固地被建立起了。因此,專注(定)和覺知(慧)兩者便都現前。
要有一顆平靜的心,並不意味著沒有事情發生,法塵仍是會生起的。例如,當我們談到平靜(禪那)的第一階段時,我們說有五個因素。伴隨著「尋」和「伺」,「喜(piti)」會和思惟(觀)的主題一起生起,然後是「樂(sukha)」,這四個要素全都在平靜的心中,它們猶如一個狀態。
第五個要素是「一境性(ekaggata)」。你也許會想知道,當這些其他的要素都存在時,怎麼可能有「一境性」。這是因爲它們都在平靜的基礎上被統一起來了。它們在一起時,稱作「三摩地(定)」的狀態。它們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心的狀態,而是平靜的要素。雖然有這五個要素存在,可是,它們不會去干擾基本的平靜。「尋」存在,可是它不會去干擾心;「伺、「喜」、「樂」生起,可是也不會去干擾心。心於是和其他要素就如統一了一般。平靜的第一個階段(初禪)就是如此。
我們不必去談論初禪(jhana)、二禪、三禪(註)等等,讓我們就稱它作「一顆平靜的心」罷。當心逐漸平靜下來時,它會將「尋」和「伺」丟掉,只留下「喜」和「樂」。爲何心會將「尋」和「伺」丟掉呢?這是因爲,當心變得更細密時,「尋」和「伺」的活動由於太粗,所以無法保留。在這個階段,當心停止「尋」和「伺」時,極「喜」的感覺便能夠生起,於是淚水就會湧出。可是,當三摩地更深時,「喜」也會被捨棄,只留下「樂」和「一境性」。直到最後,連「樂」也離去,而心則達到最細密的階段,只有平靜和「一境性」存在,其餘的一切都捨棄於後,心住於冷靜中。
註:襌那(jhana),三摩地(定)的進階層次,在那裏,心會專注於其禪修主題(所緣境)。禪那分爲四個層次,每一層次都比前者更細密。
心一旦平靜之後,上面的情況是會發生的,你不需去想太多,它自己會發生。這就叫作「平靜之心的力量」。在這個狀態下的心,不會昏沉;五蓋:貪欲、瞋恚、掉擧、惛沉、疑惑都消失了。
可是,如果心的力量仍然不強,正念也弱,偶而就會生起一些會干擾的法塵。心是平靜的心,但平靜中又彷彿有一團「模糊」存在,卻又不是平常的那種昏沉。有些法塵會出現 —— 我們也許會聽到某種聲音或看到一隻狗等等,但不眞的很明顯,卻也不是一場夢。這是因爲這五個要素已經變得不平衡而且微弱。
心會在這些層次(禪定)裏玩弄把戲。心在這種狀態時,「意象」有時會透過任何感官而生起,禪修者可能無法很準確地說出正在發生什麼事。「我在睡覺嗎?不。是夢嗎?不,不是夢。」這些法塵是從中等的平靜中生起,可是,假使心確實是平靜且清明的話,我們就不會去懷疑種種生起的法塵或意象。問題諸如:「我在睡覺嗎?我睡著了嗎?我迷失了嗎?」是不會生起的,因爲它們是一顆依然疑惑的心的特徵。「我是沉睡的,還是清醒的?」模糊不清!這就是心迷失在自己的情緒之中。就好像月亮跑到一片雲之後,你仍然能夠看到月亮,但雲卻遮蓋了它,使它模糊不清。這不像從雲後所顯現出來的月亮,如此清明、皎潔與光亮。
當心平靜且正念和自我覺醒被穩固地建立起時,對於我們所碰到的種種「有爲法」,都不會有疑惑,它將會超越障礙。我們會對一切在心中生起的事物清楚而如實地了知。我們之所以不會去懷疑,是因爲心清明且光亮;達到「三摩地」的心是這樣子的。
可是,有些人發現要進入三摩地很難,因爲那不適合他們的性向。雖然有三摩地,可是並不堅強和穩固。不過,我們可以藉由運用智慧。運用思惟(觀)和看見事物的眞相來達到平靜,以這種方法來解決問題。這就是運用智慧,而不是利用三摩地的力量。在修行中要達到平靜,並不一定要處於禪坐中,比方說:只要問問自己:「啊,那是什麼?」當下就解決你的問題!一位有智慧的人就是這樣 —— 也許他無法達到三摩地的高深境地,雖然他的增長只足夠長養智慧。就好像種稻和種玉米的差別,我們在生計上依靠稻米比依靠玉米還來的多。我們的修行亦可如此,我們比較依靠智慧來解決問題。一旦我們見到眞理,平靜就會生起。
這兩種方法是不同的。有些人有「內觀」,智慧強,但定較弱,當他們坐下來禪修時,他們並不很平靜。他們會想得很多,思惟(觀)這兒,思惟(觀)那兒,直到最後思惟(觀)樂和苦而見到它們的眞相。有些人比較傾向於此,不論行、住、坐或臥,法的覺悟都能夠發生。透過瞭解、透過放下,他們都達到平靜。他們透過毫無疑問地了知眞理而達到平靜,因爲他們自己已親身見到。
其他人則擁有少許的智慧,但他們的「三摩地」卻非常強。他們可以迅速地進入甚深的「三摩地」,可是,智慧卻不多,他們抓不到自己的煩惱,也不認識它們。他們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
可是,不論我們用何種方法,我們都必須遠離妄見,只留下正見;我們必須捨棄煩惱,只留下平靜。這兩種方法我們都歸結於同一個地方。修行雖有兩面,可是,這兩面 —— 止和觀,是並存的。我們是缺一不可的,它們必須並存。
那個「觀照」在禪坐中生起的種種要素的,就是「念」,這個「念」是透過修行而能夠協助其他要素生起的條件。「念」是生命,只要我們一沒有正念,我們心不在焉時,就好似死了一樣。假使我們沒有「正念」,那我們的言語和行爲就沒有意義了。這個「念」很簡單地就是當下的心,它是造成自我覺醒和智慧生起的「因」。如果缺少了「正念」,不論我們長養了什麼德行(戒),都會是不圓滿的。所謂的「念」是在行、住、坐和臥中觀照我們的東西,卽使我們不在三摩地時,「念」都應該不時存在。
不論我們做什麼,我們都得謹慎小心,這樣慚愧心就會生起,我們會對於我們所做的錯誤行爲感到慚愧。當慚愧心增強時,專注力也會隨之增強;當專注力增強時,散亂就會消失。卽使我們不坐下來打坐,這些要素也會在心中現起。
這種現起是源自於長養「念」的緣故。增長「念」—— 這就是觀照我們正在做的工作或過去曾做過的事的法,它有眞實的用處。我們應該在一切時中覺知自己,如果我們這樣來覺知自己,「對」自會分辨「錯」,「道」於是會變得清晰,造成一切慚愧的因也將消失,智慧於是生起。
我們可以將修行總結爲戒、定和慧。專注、控制,這是戒;而那個在控制中穩固地建立起來的心,是定;對於我們所做、所爲的活動都能完全、全面的了知,是慧。修行,簡而言之,就是戒、定和慧;或換句話說,就是「道」。除此之外,沒其他方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