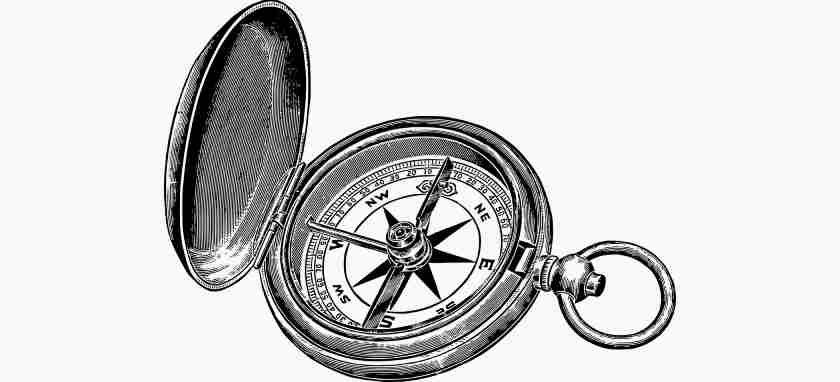
「信仰」,是一件莊嚴的行爲,是一種聖潔而可以供諸於殿堂的磐石;信仰必須伴以一定的純度。人類的行爲一旦投向一種眞理之後,他必須付以終身之代價,信守不渝,寧可犧牲身命,也得保衛「貞堅」、純明如玉。
這項原則,是一個有宗教信仰之人的「人格基點」標準;如打破這一原則,便流於世俗,永難進入聖者之殿堂。
「信仰」,彷彿「聖女貞德」,毋視於敵人的槍口;信仰必須如聖者釋迦,能「捨身飼虎」,「割肉餵鷹」,心無所繫;信仰必須如「焚城錄」裏的基督徒,在羅馬暴君尼祿的迫害、殺戮之下,能在監獄、石窟之中,唱起他們的聖歌。——信仰能令一個懦夫成爲强者;信仰,能使貧乏之人,變爲富有。信仰,足以使缺乏道德意識之輩,產生「道德勇氣」。
西藏領袖達賴喇嘛之所以令世人重視其行踪,這不在於他的權力象徵與特殊的政治形勢,而在於他能與「信仰」共死生。一個人對於信仰,必須「落實」到心靈深處,到生命盡頭;信仰一旦出現多頭馬車現象,便流入形而下的商品式多神崇拜之中。
信仰,一方面是感性的產物,但必應賦以「理性」來平衡,使其眞理能獲得客觀的肯定,而不入於邪道、盲從。人之生命價值,端在他的智慧之抉擇,而非水上浮萍,任「業風」飄浮。
弘一大師有詩云:
亭亭一支菊,高標聳晚節;
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
信仰必須有這種強度與純度,血肉塗地而不移,金流山焦而不動,才是釋迦的信徒。試問:我們今天不知能從何處尋覓幾個「信仰如斯」的純一之人?信仰如變爲商品,變爲人情,可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羊亡歧路,誠不知此爲何種信仰?
現在,我們當知,在「觀音、城隍、蠱」三重世界裏的游離羣衆,佛國裏是不收這批人的!
——一九八一年五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