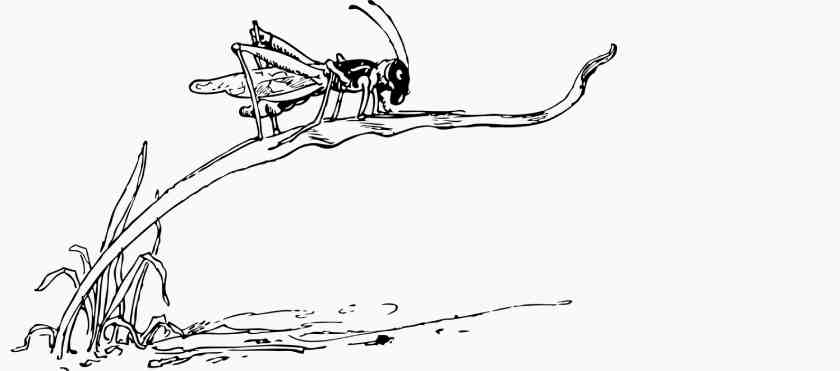
佛家所謂「悲情」,可以透過兩方面來解釋:一,悲情卽是儒家的「生知之性」,所謂「良知」、「理性」;一,是經由佛道的薰修、精進、發露而來的成全他人、犧牲自己的偉大情操;是體悟衆生同體的悲心大願。
人,不是天生的聖賢。一切聖哲,也都是經由人這一關提煉薰修而來。佛陀與孔孟老莊,同是一樣。因此,人不能不以聖賢相期許;如以聖賢相期許,則又不可以「我非聖賢」,「所以我可以與城狐社鼠同流」。“矯情” 不能以「悲情」來掩飾其虛偽面目。悲情必須出自對於一切有情的深關摯懷;彷彿母之與子,骨之與肉,唇之與齒,串連一體的相依相賴,而不容寸絲片縷的虛情假意與施恩布德的太上權威。
悲情必須是將對方的生命份量放在第一位,自身則降於空相之境。悲情應將全體的權益超越於個人,社會的權益超越於團體,地球的權益超越於國家,衆生的權益超越於族類。一個修道者,是否接近聖賢的階梯,應該從「悲情」中見分曉,凡自視過高而毋視於悲情之發露者,在人我之際太分明,利害之間過細膩,不能以地藏菩薩心胸容納同流,不足以言「道」。
人之一生,曲折猶如「山陰道上」,得失頗難判定。今日之得,也許是明日之失;今日之失,焉知非明日之得?何況三世,因果森密如「帝網蛛宮」,非佛菩薩難窮其奧;是以佛弟子雖未見道,但具 “悲情”,亦足言道矣。無相的悲情,有無限的回流;無限的悲心,有無窮的福田;福慧雙修,不能不以悲情爲基礎;純一的「慧解」,如果銳化成一股悍戾的靈氣,彷彿塗蜜的劍蕊,不僅傷害別人,也將會誤刎到自己。
悲情,悲情!必定是一顆悲天憫人之心!「悲情」,源自無相之慈、之悲、之喜、之捨;而它的回饋——彷彿投射出去的光,它將爲你自己在黑暗中舖出一條金色的道路!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