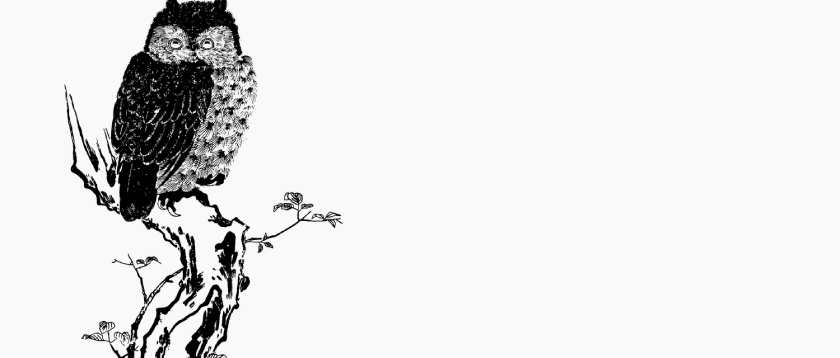
黃崗熊十力先生,確是儒門一代龍象。但我們應該提醒的是——他却不是佛門之龍象。民國九年秋後,熊氏與呂澂、黃懺華、王恩洋、景昌極等(後來均成爲佛學家)同門受教於南京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此其間,與梁漱溟、湯用彤,亦先後承沐,他們終因緣會不同,「出佛入儒」,而成爲中國近代哲學思想界的一代宗師。
中國文化自民初到流寓海涯的今天(因爲儒門淡薄,收拾不住。)以承傳儒家血脈、重建儒家文化的所謂「新儒家們」,自熊十力先生以次,有「梁漱溟、張君勱、張東蓀、馮友蘭、錢穆、方東美」諸氏;而接承熊十力一脈之學人,則有潛習有成的唐君毅、牟宗三諸大德。論至熊氏同一等層的新儒家,其所學所創,亦各自不同,此猶如顏、曾與朱、程之不同然。
▉梁漱溟以思想家兼實踐派,成爲中國聖壇一位堅强人物。其重要著述代表,有「印度哲學概論」、「中國文化要義」、「東方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等書。
▉張君勱,爲中國當代憲法起草人,中國民社黨元勲,重要著述「新儒家思想史」(英文本),因晚年寄寓海外,對中國思想界影響不大,但他確是一新儒學者。
▉張東蓀,爲一「道德哲學」極有成就的「新儒」。其重要著作有「道德哲學」、「新哲學論叢」,及有關政治思想方面的作品。
馮友蘭,除「中國哲學史」外,有「貞元六書」,足以代表他的「新儒家的面目」。錢穆,爲史學大師,他的「朱子新學案」及「湖上閒思錄」等書,都可以代表中國儒生的形象。方東美,民國十四年與熊十力同時任教於武昌大學,晚年雖著力於華嚴,但其學思仍屬於儒家範疇。
上述諸儒,包括熊氏在内,他們對佛學均有所浸染,唯他們之浸染程度各有不同;事實上,正如宋明儒生一樣,沒有佛學底子,似乎他們未見得能產生這麼大的成就,而他們思想從佛學翻滾過後,也與宋明諸儒一樣,反身「闢佛」(按方東美晚年入佛,並未闢佛。);最低限度,他們對於生命第一義諦,以佛性而言,他們是未加考慮的。—— 這是他們的文化使命之預鑄。
現在,對於新儒家之重要人物——熊十力,我們可以提供的著作資料,是:
(一)新唯識論(文言本民國十二年成稿,二十一年正式出書。語體本,民國二十九年印行。)本書兩種版本,包括「破破新唯識論」(係破呂秋逸之「破新唯識論」)在內,爲出佛入儒,自立境量的代表作。(二)十力語要:(民國二十四年初篇第一、二卷成書,續篇第三、四卷民國二十八年出版)本書爲語錄性指導典範。
(三)佛家名相通釋;(民國二十五年成書)訓解唯識法相之作。
(四)中國歷史講話:(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出版)泛論中國歷史文化問題。
(五)讀經示要:(民國三十四年成書)指示儒經之思想義理問題。
(六)正韓(韓非子評論):(民國三十八年出書)評法家思想。
(七)原儒:(民國四十三年大陸陷後,在上海成書。)肯定儒家文化超越唯物主義,受到中共嚴厲批判。
(八)因明大疏刪注:剔抉原書「疵疑」。
(九)乾坤衍:宏揚易學思想之作。
(十)明心篇:究明心性思想之學。
(十一)體用論:出入佛儒之書。
(十二)政道與治道:經世思想之書。
上述十二種著作,第八種以下手中無書,出書年代可能在大陸淪陷之後,歷經輾轉送出鐵幕,先後在香港出版、臺灣出版商加以翻印。復次,近年有李霜靑著:「一代大哲熊十力傳」,可以覆按熊氏之生平及著述槪觀。近三十年來,熊氏思想及其著述,備受海内外人文學界重視,尤其他的門人承其衣鉢,各有弘揚,而成就尤具特色,因此,熊氏儒學,照遍了世界漢學園地。
熊氏在中國新儒家陣容之前,與其他諸子不同的是,他獨專於儒家純義理的深入、檢討、與創發而不及傍鶩。同時「糅合」佛儒思想,以易學爲根,建立了儒家第一義。似乎熊氏既宗儒,便不能不在思想上有所「闢佛」。他的批判佛法思想的「新唯識論」,據他自述,他於民國十一年,在北大授「唯識論」時,「忽不自安,輟講。翌年,改造新論。······」「新論」一出,則佛家上自無著、世親,下至玄奘、窺基諸佛門大德,具成「疑難」矣!
案:熊氏「新唯識論」,確實承認佛法淵深浩瀚、圓融究竟,然於「出世」一途,難圓「生生化育」(按熊氏謂「生化」,有「功能、流轉」之生生不息義。)之機。雖然佛家能親證「空寂」,「若不通於儒,則唯蕩然出世,沈空滯寂」,走入非人生的路向。熊氏云:「佛家原期斷盡一切情見,然彼於無意中,始終有一『情見』存在,卽出世觀念也。」「所以佛學談本體,不涉及生化。」熊氏在「新論」功能章,反復衍述「生化」思想,認爲佛家沉空滯寂,終是一偏。卽使佛家之空寂,能含攝「生化」,亦疏忽其大用。——而觀乎熊氏立論,皆以易學爲經,調和儒佛,另立「新意」,同時亦批判了佛學。
我們用較粗淺的比喻,來疏解熊氏之論:「如果天下人都成佛證道,便難免於生命頓滅,生機絕續,卽使人人成佛,又有何補於宇宙之空虛、枯槁?」雖然佛家認爲「衆生無盡」、「世界無邊」,衆生界不可能人人成佛,物物情空;宇宙終仍是衆生營務之場所;但是在「邏輯」的大前提下,熊氏之論,依然是可以假定成立的。這也是熊氏面對佛道,所不能解決(呼不自安)的一點。因而,由此自造新論,對唯識法相(也兼及全部佛理),作一總判(判得對不對是另一問題)。
熊氏深於思辨,筆力精鍊、文字雋敏,誠是中國最強勁的儒生,而他的「新論」一書,也因而震驚了整個中國思想界,民國十一年中國佛學界呂秋逸的「破新唯識論」,以及日後印順長老的「評熊十力新唯識論」(見〔妙雲集〕下篇「無諍之辨」第一篇),比起「新論」,「其「光」其「熱」,也都微不足道了。而且,這兩篇文字坊間根本看不到。問題是,擺在知識份子面前的,全是「新唯識論」,在思想界,是一面倒。同時更吃緊的是,熊十力之筆,生花蘊霧,卽使你馬上產生一部偉大的「破新論」,也難以掩蓋知識份子心中初次投入視覺的深刻印象與主見(除非他能有所「獨超」、慧眼。)其實,熊十力確是一位深具「宋明儒家性格」的讀書人——當他淪入大陸之後,尤具此種顯明氣質。他的水平,也絕不遜於朱程陸王。他能不倚前人,開立自己門戶,文字、思想(除佛學之外),均能震響中國知識份子的良心,因此,他能得到王陽明以來——他的門生和後輩的高度崇敬。
可是,熊氏也有如中國古代儒生一樣,其思想之深,但無法補救其性情之切與悲情之薄;如說他「棄佛入儒」,他是不肯承認的。由於薰染佛法較他爲深,所以他亦無法作違心之論。因此,在唯識思想上,我們希望佛學界,能有一本大書,解決熊十力所遭遇的「唯識難題」。
我是根淺慧薄,不知熊十力是「超越佛學」還是「知解佛學」;抑是對儒學「護之太深」,還是「實踐太切」。我總覺得,儒家沒有勇氣面對生命流轉之眞象,而直下承擔,「難疑」因此祗能局限於易學的範疇,陷於「人天」情境之樊籬而不自覺。卽使儒者能體會此點,恐怕也放不下這一份歷史的包袱,眞正地撇開「文化」成見,混同儒佛,自立甚麼新意。
這些年,有些學佛人,嘔心浴血,宏揚熊十力,我覺得是「數典忘祖」,沒弄清對象。宏揚熊氏術學者,多的是中國後生儒者,又多得了幾個楞頭佛子來「佛頭着糞」?
[後記]
熊十力,清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生於湖北黃崗,青年時期,參加一系列革命運動,民國九年冬入南京支那內學院,浸染內典,民國十年,出內院,至北大授「唯識論」,此後專闡「儒學」,著述與授徒不輟,大陸陷後,於民國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逝世於上海,享年八十六歲。
附註:本文成稿之當晚,細讀印順導師的「評熊十力新唯識論」,始發現熊之「疑難」已解決一半。心頭塊壘,也爲之平消。唯印老之書,豐贍不足,理路略簡,難掩熊氏之光燄,請讀過「新論」者,可覆印老之文。
——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