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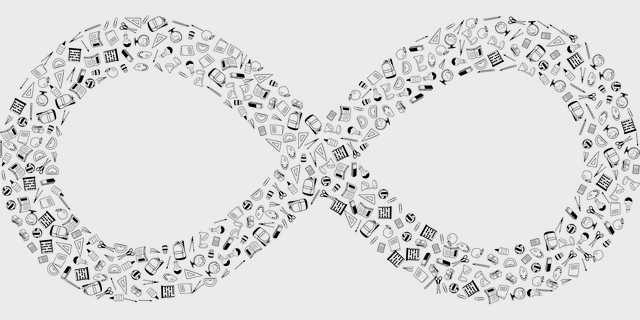
佛這一稱號,自從釋迦牟尼佛入滅之後,便漸漸模糊不清,時至今日,所謂佛,已非釋迦牟尼佛所說之佛。一般世間思惟下的學者把佛定位於歷史人物,佛只是個勸人向善的道德家,若是小乘學者自比阿羅漢是佛,若是大乘學者,佛梵一如,佛上帝一如,佛儒一如,若是禪者自比見性成佛,若是修密者自比是活佛,若是神棍自比是濟公活佛,觀音古佛,彌勒佛,阿彌陀佛,若是一般人以爲佛就是供在寺廟中的神。
學佛人若不釐清佛陀的定義,而自稱學佛人,怎麼能責怪他人譏嫌我迷信呢?
佛是梵語佛陀的簡稱,中譯叫做覺者。覺知什麼而號稱爲佛呢?
雜阿含一〇〇經大正二册二八頁上:
佛見過去世 如是見未來
亦見現在世 一切行起滅
明智所了知 所應修已修
應斷悉已斷 是故名爲佛
覺遍一切過去未來現在任何事,包括現代的科技,醫學,以及未來的文明發展,事無巨細無不了知,所以覺者又叫做一切智者,一切種智者,這個定義極爲明確,可以釐清流行中種種模糊不清的佛。
阿羅漢不是佛
學佛的初步要有正見,正見的第一課目就是於苦聖諦如實知,苦聖諦就是闡述有過去世有未來世有現在世,有父母有衆生生,三世輪轉苦不堪言。但是初學者都無法相信三世之說,三世之說若無法建立信心,則於苦聖諦有疑,雜阿含四二〇經:「於苦聖諦有疑者,則於佛有疑,於法僧有疑。」若於佛法僧有疑而研究佛法只是世間知識之研究。若要入佛知見解脫生老病死苦,初階苦聖諦不如實知,雜阿含四三六經:「若有說言,不登初階而登第二第三第四階昇堂殿者,無有是處。」學佛要深信苦聖諦三世之說,才可能如實知集聖諦、滅聖諦、道聖諦,於四聖諦無間等,然後才能融銷貪瞋癡,心解脫、慧解脫而自證阿羅漢果。
因此,初學者的學佛目標便是如何使自己相信三世之說,無論閱讀佛經,或親近善知識聽聞佛法,都爲了如實知苦聖諦,瞭解三世因果,乃至於苦聖諦不疑,於佛法僧戒不疑,得法眼淨證初果。頗有學者誤會已悟已證,更有冒充已悟已證,這是很容易檢別出來。凡是把佛法定位在世間思惟,不相信三世之說的人都是未悟的人,凡是未持戒的人連冒充已悟的資格都沒有,凡是主張淫欲不障礙修道的人,也都是未悟的人,爲什麼呢?行淫欲與淫欲界相應,緣下界必下說下見下想,終將下生墮入地獄,以其不信三世說,是故不信學佛應當離欲離諸不善。
若已悟已證初果,深信三世因果,但不能證明三世之實況,雖然如此,以其深信三世因果,如實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善不惡有不善不惡報,樂於離欲離諸不善行,貪瞋癡諸煩惱未斷誓願斷,心解脫慧解脫尚未證誓願證,佛法未修誓願修,精進於八正道,若今生不成阿羅漢,最遲七生,於心解脫慧解脫時,三明六通一時具足,善能證明過去世未來世現在世,自知自證不受後有,成阿羅漢。
世尊入滅後,頗有學者誤會已成阿羅漢,更有很多人冒充阿羅漢。事實上冒充初果都很難,只能騙騙初學者,若冒充阿羅漢,當知阿羅漢心解脫具足三明六通,神足通能點石成金,能飛行自在,若有說他是阿羅漢,請他現場飛行三圈,即刻使他下不了台而以「顯神通犯戒」來欺蒙他人。冒充阿羅漢而得逞,這是中國人誤會慧解脫者,以爲慧解脫就是阿羅漢,所以有未具足三明六通之阿羅漢。事實上若慧解脫阿羅漢必有三明六通,若無三明六通之慧解脫者只是向阿羅漢果的階位,慧解脫者心未解脫,貪瞋癡未斷便不是阿羅漢。縱然有神足通,能飛行自在,若有脾氣,有欲心,他就還不是阿羅漢。
阿羅漢雖具足三明六通,善知過去世未來世現在世,但所知有限,他未曾修學的世間知識學問,以及出世間的無量法義仍然不知不見,所以沒有一切智,雖然心解脫慧解脫,於日常生活中非犯戒的過失仍然層出不窮,如迦留陀夷坐死嬰兒,孫陀利難陀被妓女強姦,周利槃陀伽不善說法義但能顯神異,滿三千大千世界阿羅漢的智慧也不及佛陀千萬億不可算數分之一的智慧,是故阿羅漢不是佛。
阿羅漢不是佛,也不會有阿羅漢冒充佛,唯有於苦集滅道四聖諦未如實知的人,不信三世因果,不畏懼善惡報,才會冒失自說已悟已成阿羅漢,自比阿羅漢就是佛。若有堅持阿羅漢就是佛者,顯然他所說之佛並非釋迦牟尼佛說之佛。
梵不是佛
梵是婆羅門宗教徒敬畏宇宙神祕,於森林中禪坐冥想出來的知見,以爲宇宙萬象都是梵的化身,梵是眞我,常恆不滅。此種知見與大乘佛法如來藏見相似,佛教學者分別不出二者的差異,於是認同梵我,而使佛梵不二。
學佛的瓶頸是無法開放世間思惟,固執有我,有此世間,以此爲障礙誤會了如來藏之意趣。小乘者無法信受,大乘者認同外道。殊不知名之爲如來藏便是一種施設,否則我們如何能有此知見呢?既是知見範疇的什麼,都只是循業所見,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有如來藏見而使如來藏淪爲有我之糟糠。若無我,不壞如來藏知見,宇宙萬法皆是如來藏化身,爲什麼呢?識緣色住,識緣受想行住,宇宙萬法唯識唯心,即是集聖諦所說,六入觸所顯現之世間(見雜阿含二三〇經二三二經)
心地不善良,唯識唯心所發現的宇宙萬法必然不可愛不可戀,任識任心生活在五欲中,樂少苦多,是故久遠以來便有智者尋求解脫之道,婆羅門突破世間思惟發現三世之說,更進一步發現梵,已盡了人類思想的極致,婆羅門自慢爲第一種姓,第一等優秀人,也不無道理。大概是人類思想的極限,無法再突破有我之盲點,不能發現梵我也只是一種作用,沙門婆羅門的最高境界到此爲止。於是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間,所謂一大事因緣,便是爲了突破人類的盲點,說明法住法空,梵住梵空,無我,空,無我我所,坐禪婆羅門都因此突破,見法涅槃,一群一群的婆羅門湧入佛法中,應得度者都已度,佛陀也入滅了,不得度者依然固執有我,保持了人類的水準,執迷常恆不滅梵,學佛人異其梵爲如來藏,爲自性,爲佛性,爲眞如,爲法界,爲空,佛梵一如,經由中國再傳播至其他國家,流行於世界各國。
佛法中的名相來自婆羅門固有的文化,藉其名相闡述四聖諦,闡述無常苦空非我思惟,以此思惟打破人類的黑漆桶,趣向湼槃而得解脫。此思惟法的正方便就是道諦「非我」思惟。婆羅門雖然能開放世間思惟,却無苦集滅道思惟,無法發現梵住梵空,梵非眞我,非我。「非我」是佛梵的分際,佛法一旦把非我拋棄,如來藏便等於梵,王子淪落爲乞丐,怎不可惜!
佛是一切智者,拈出梵我爲生滅法,梵只是糟糠,是故說梵不是佛。
上帝不是佛
如來藏思想流行於六祖惠能時代,當五祖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時,惠能言下大悟而說:「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又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語中之「何期」若做讚歎詞用,自性等同有我如來藏,何期若做否定詞用,自性等同無我如來藏。但中國學者都把何期當做讚歎詞解,自性能生萬法,等同上帝能創造萬物,頗有基督教及天主教徒便認爲,上帝與佛只是異名,若是如此,佛法難懂只是故弄玄虛,不如信仰上帝來得簡單可靠。
眞常如來藏之信仰的確不如基督教信仰,這是學佛人不辨眞實自墮黑漆桶中。
六祖若已大悟,何期是否定詞,因爲自性能生萬法,自性便是一物,此一能生萬法之物是誰生呢?若不待他生,自性與上帝相同,已盡了邊際,就是有邊之偏見,修梵行者所不應當有。六祖大悟是故一語道破當代有我如來藏見,「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待自性能生萬法呢?」六祖之後誤會了六祖之本意,禪宗一路發展下來,不立文字毫無法住智,背離佛法而與外道相通,所參所悟者都已非釋迦牟尼佛所說之佛法,禪者自墮黑漆桶中不辨眞實,洋人基督徒涉獵佛法,旁觀者清,一眼便認出禪宗所參所悟的就是上帝。部分中國學者索性建立了三教合一,五敎合一。
佛是一切智者,如實知宇宙人生眞相,法住法空,宇宙萬法是每一衆生循業所見,每一衆生所見之宇宙觀個個不一樣,譬如作夢,每一個人所夢的夢境都不同,夢境是循我心境而顯現,有人作帝王夢,有人作小丑夢,信仰上帝者作上帝夢,信仰佛教者作佛敎夢。作上帝夢只是百千萬億種夢中之一種夢而已,而夢本空,法住法空,何有上帝創造萬物?何有自性能生萬法呢?於夢中說夢話不知覺醒,上帝何堪比作佛?是故說上帝不是佛。
佛儒非一如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這是中國文化,和印度婆羅門文化同等齊觀,是不離世間思惟的知見,是不離有我有我所,有一形而上常恆不滅,就叫做「天」,此天和婆羅門梵,佛教有我如來藏,基督教上帝,異名同義,只是子不語怪力亂神,未使儒學發展爲宗教,此或孔子勝於其他賢聖之處。可惜,後來者不甘寂寞,論性善,論性惡,論性善惡混,論性未善,竟然不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若本善可謂之爲善道,性若本惡率惡性謂之爲惡道,若善惡混論率性之謂爲善惡混道,若性未善,率性之謂爲未善道,已背捨孔子本意:「性相近習相遠」。
但無論所論如何只是世間思惟之生滅法,及至相似佛法傳入中國,心性之論與眞常唯心論相呼應,半斤笑八兩,在笑中把儒學推向宗教範疇,有倡佛儒一如,三教合一,五教合一,也有尊儒排佛說,但中國文化已變質。理學爲了與相似佛法唱對台戲,凡夫不出世間思惟,所謂窮理以盡性,盡說一些不儒不佛的理念,只把儒家思想玄虛化,似已無濟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事實上,孔子祖述之道在於世界大同,只及於釋迦牟尼佛說轉輪聖王之知見,未及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間之旨趣。儒家學者只須嚴守本分,不與宗教交涉,中國文化之光輝常照於世間法,自從強出頭與出世間法抗衡,違背了先賢本意,儒家學者自以爲高明,殊不知所對罵的相似法是已變了質的佛法,眞常如來藏是錯把水仙當做大蒜的外道法,儒家學者不查,於學說中屈辱釋迦牟尼佛,實已減損中國文化的光彩。
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間,開示顯發因緣法法住法空,法住就是不壞世界大同,法空就是不待世界變滅本空,闡述宇宙人生的眞相,是不捨世間法教說出世間法,開放世間思惟,使人類大開眼界,入佛知見,空我我所,空並非遁空,是補述孔子不談之「天」,說明天住天 空。儒家學者若修天人合一,當知天人合一與梵我合一及上帝與我同在,反聞聞自性,法界觀,都只是循業所見之生滅法,要當法住法空,永斷貪瞋癡,應修已修,應斷已斷才叫做佛,這是儒家所不知,是故說佛儒非一如。
見性成佛不是佛
見性成佛是禪宗所標榜,用中國通俗話說叫做悟道。此道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之道,此道常恆不滅,不可名狀,雖然不可道不可名,但可藉由無和有觀察其妙及其邊際,「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道是宇宙人生萬法之本元,此種知見和婆羅門梵,基督教上帝,儒家之天,相似佛法眞常如來藏,異其趣味而同一旨歸。道的理念深入中國諸子百家,影響中國文化之取向至深且鉅,不論政客,隱士,販夫走卒,士子、武夫都知歸根復命入於道,「道」經常掛在中國人的口邊。
相似佛法傳入中國,見性成佛正合中國人的口味,認爲見性即是悟道,道是宇宙萬法之本元,悟道即是佛,禪者所參即是參此道,有說悟道者即是悟此道,於是佛道被劃下等號,佛道一如。禪宗不立文字之風盛行後,學者都欠缺法住智,都不知參禪修道未嘗學佛,所謂明心見性,所謂見性成佛,只及於道家之道,在佛法中尚未得法眼淨,尚未證悟,機鋒轉語只是文字語言遊戲,禪詩只得文學趣味。
中國學者不知佛道有別,是昧於民族感情,以爲中國文化中自有應身佛所傳述之無上道,讚揚祖師禪,貶損如來禪,致使學者不知所學非佛法,還洋洋得意不立文字光大了佛門。
中國學者和婆羅門打不破梵的黑漆桶一樣,無法突破道的迷思,也如基督徒走不出上帝的威勢,自願做道的生物,所以聞說「自性能生萬法」毫不思索頂禮膜拜,此是老祖宗所傳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殊不知能生物也是被生物,譬如我是母親生,母親能生却也是祖母所生,若說母親不待祖母生,道不待他生,這是耍賴的邊見,自盡於邊際,儒家叫做畫地自限,似乎人類不分東西方都走不出世間思惟的極限。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的「自然」若是現代人所知自然界之自然,道有摹擬自然的作為。道法自然的「自」若做自己解,道法自然便是道師法其自己,一樣是有摹擬 的作爲,若是如此,雖然道不可道不可名,只是不可道不可名,如同上帝,是有我有我所,未出生滅無常之範疇,參此道,悟此道,縱然已悟,只不過是悟了一個生滅道,錯把水仙當做大蒜。
若是正法律,法住法空,道住道空,所謂道只是循業所見,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譬如作夢,每個人循其心境而顯現夢境,夢境不眞實,本空,夢醒夢中山河大地滅無去處,智者不待夢醒而知夢空,無有作者。比況現前,宇宙人生是有我而有此世間,若知非我,則趣入空,澈知宇宙萬法法住法空,所謂道,所謂天,所謂梵,所謂上帝,所謂佛性,所謂自性,所謂如來藏,所謂眞如,所謂空,也都只是統攝一切萬法的法,當知法住法空。此法住法空之思惟是苦集滅道思惟,是無常苦空非我思惟,是如來智是如來禪,不若中國禪者所謂「見性成佛」之禪,中國禪所見之自性,只見道家之道,初果都未得,遑論成佛,是故說見性成佛之佛,不是釋迦牟尼佛所說之佛,是自我陶醉佛。
要當見過去世,見未來世,見現在世,一切行起滅,明智所了知,所應修已修應斷已斷,是故名爲佛。
活佛不是佛
活佛是蒙古西藏靑海一帶喇嘛敎政敎領袖的稱呼,活佛只是當地人民對該領袖尊稱,與佛教之佛不相干。雖然當地人民自稱也信奉佛 法,收藏印度本土抛棄不要的佛教典藉,五體投地拜佛,這只是民俗宗敎歸屬正統宗教的依附行爲,殊不知所收藏所信奉之佛法並非正法律。
佛法原本不是某一區域的文明,雖然發源於印度,世尊入滅之後,婆羅門文化復興,梵我含攝諸方民俗宗教的神而建立了印度教,佛法却日漸變質而墮落而形成密教,教徒沉迷於咒術及男女性愛之術,名爲無上瑜珈,名爲金剛乘,於污染中而不染,如蓮花出污泥而不染。
一向禁欲的學者於性開放之後肆無忌憚與金剛上師與佛母行淫欲之 樂。所謂佛母就是供學者於性愛中修氣修脈,修喜樂大定之女性,以其協助學者即身成佛,故美其名爲佛母。密教盛行後,男女雙修的行爲格格不入於印度傳統文化,成爲印度文化負担。當回教國家統治印度時,淫穢的密行更不見容於回敎,與佛敎同時發展於印度的耆那教,印度教,以及其他宗教未受摧殘毀滅,獨獨密教化的佛教滅亡了。若說佛敎滅於回敎之侵略,不如說印度文明乘勢把印度文明中的垃圾抛棄焚毀。
就在此時開展西藏文化的喇嘛敎如獲至寶收藏了印度文明的抛棄物,這些抛棄物又輾轉流布於中國。畢竟人類貪欲,不離欲而成就菩提之法被視爲無上法寶,普受貪欲的衆生熱愛護持,流行於世界各地,金剛上師及佛母所到之處,活佛之威德也隨之流傳,一般佛教信徒不辨眞實,以爲活佛就是活生生的佛。
其實男女雙修只是性愛遊戲,反而令行者墮落而不知自拔,活佛也只是凡夫,也許有其過人之處,是傑出的凡夫,却不是佛。爲什麼呢?活佛標榜轉世,當知凡夫才受轉世,凡夫才有淫欲行爲,是故說活佛只是凡夫。我們基於世間思惟,認爲人只此一生之命,居然有能轉世再生者,不視他爲活佛則何,我們認爲人類於性愛中不堪久戰,不能不漏精,而金剛上師能久戰能不漏,不視他爲活佛則何?假使我們開放世間思惟,以苦集滅道思惟來觀察宇宙人生,人生是性愛的人生,所以於六道中輪迴不休,不捨淫行而與欲界相應,再生轉世乃不得不爾的業報,性行爲的本質不待漏精不待漏氣不待漏神就是有漏,於雙修時不待漏精已剎那剎那與有漏欲界相應,已剎那剎那間有漏慧命,終至墮落。要當離欲,與欲界劃清界線,不與欲界相應,貪瞋癡永斷無餘乃名爲無漏,不再生不受轉世乃名爲佛?而今我們顛倒是非,把行淫欲轉世再生的凡夫視爲聖者,把釋迦牟尼佛視爲已不存在的過去佛,適足以說明少有人知道什麼叫做佛。
生與死是循業所見,若趣入因緣法法住法空,生住生空,死住死空,我們以爲釋迦牟尼佛已入滅,已死,這是我們有生死煩惱的知見,若空我我所見,生死是夢幻中事,不再生不受轉世,譬如不再作夢,無夢中我,夢境本空,何有斷滅呢?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非終不終皆是戲論。若有我則有生死見,不出生死輪迴,轉世再生的活佛乃有我凡夫,是故說活佛不是佛。
神不是佛
我們有生死的恐懼,有禍福無常的恐懼,窮人類的智慧乃想像宇宙間有不生不滅的,形而上的什麼,所謂梵,所謂天,所謂道,所謂上帝,所謂如來藏,所謂佛性,所謂自性,所謂眞如,所謂空,以用安慰,以用解釋宇宙人生的現象。在此知見上而又想像掌握此奧秘者,若掌握此奧秘便可超越生死禍福,有誰掌握了此奧秘?我們可求他賜福,求他避禍,求他保佑。宗教乃應人類生活上的需要而發展出來。
印度由婆羅門演變開展出梵,毘濕奴,濕婆三位一體的印度教。在中國,儒家思想雖然與宗教掛勾却堅持非宗教,提倡但當盡人事聽天命。而道家神仙道之外,又發展出多神宇宙觀的道教。西洋則信奉上帝建立了基督教和天主教。至於佛法,原本不是印度文明,在印度曇花一現,佛陀入滅後,佛梵一如,淪爲佛神教,難怪史家說佛教是一神教。
佛被佛教徒視爲神,雖然是事實,但佛教徒都不承認,憤憤不平的認爲佛不是神,佛高於一切神一切宗教,却一面抗議一面誦持咒語以用祈福消災,闡述自性能生萬法,見性成佛,也拚命拜佛求懺悔,捨命殘身,朝山,巴望佛陀賜予成就,冀求從凡夫變成初果聖人,從初地變成八地菩薩,甚至以心印心即刻成佛。
頗有神棍看準佛教徒的迷信,自稱是濟公活佛,自稱是彌勒佛,自稱是阿彌陀佛,自稱是觀世音菩薩,自稱是文殊菩薩,自稱是地藏王菩薩,都可輕易騙取信徒頂禮膜拜,傾家蕩產甚至以身供養,用爲滅除罪業,祈福消災。
祈福消災是人類離苦得樂的行爲,原無可厚非,如印度教,如道如基督教,如天主教,都是以信仰而得救的宗教,都是神教,若信他,在信仰上符合其教義,雖不切實際,至少心理上獲得些許安慰。若學佛也如信仰神教那樣,視佛如神,不但不符合佛陀所教,也得不到祈福消災的目的。爲什麼呢?佛不是宇宙人生的主宰,不是神,祈求佛陀保佑,除罪消災,如緣木求魚。
學佛若要祈福消災,當知苦集滅道思惟,我們的生死禍福是貪瞋癡所招集,循業所見之宇宙人生並非有主宰神,若要趨吉避兇,要當去除貪瞋癡,實踐布施以用去貪,實踐慈心以用去瞋,實踐戒律以用去癡,饒益諸有情乃能實現所願,無須盲目的求神憐愍,若至所應修已修,所應斷已斷,智慧顯發,知過去世知未來世知現在世,如實知宇宙萬法法住法空,遍一切智就叫做佛,人人都可發心而成佛。
一向所迷信之神只是無奈於生老病死憂悲惱苦而假設之主宰,幸勿也視佛爲神,神棍冒充諸佛菩薩自也不能得逞,是故說神不是佛。
世間思惟不見佛
釋迦牟尼佛出生於西元前六世紀,印度十六國之一的迦毘羅衛國,剎帝利種姓,父親淨飯王,母親摩耶夫人。母親於娘家嵐毘尼園波羅叉樹下生產,適滿七日便命終。釋迦牟尼佛幼年乃經由姨母波闍波提養育長大。
釋迦是姓氏,未成佛前名叫悉達多,幼年時便顯露悲憫一切眾生的慈心,頗傾向出世思惟解脫生老病死苦以用救度衆生憂悲惱苦。父親淨飯王恐其出家不能繼承王位振興國力,十九歲時爲他娶妻,一名耶輸陀羅,二名摩奴陀羅,三名瞿多彌,並有衆多婦女前後圍繞,享盡人間五欲之樂。然而止不住與日俱增的出家念頭,於二十九歲時趁黑夜離家出家,捨一切榮華富貴。
先於阿羅邏仙人處問梵行之法,證空無邊處定即捨空無邊處定,又於鬱陀迦羅摩子仙人處證非想非非想處定,也隨即捨非想非非想處定。什麼叫做非想非非想處定呢?人類思想的邊際處,如道家所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已盡了人類智慧的極致,不可名狀之處,修觀而止於此,即是非想非非想處定,實際上還是有爲處定,未出苦的邊際。釋迦牟尼佛捨家出家至此,已自知人類的極致不出人類的苦況,乃捨一切婆羅門所傳遞下來的奧義,及一切沙門義,於尼連禪河邊優樓頻螺村,日食一麥專精辦道,六年苦行不可得乃受牧羊子羊奶之供養,再受村女乳糜之供養,飽食沐浴之後於菩提樹下永盡貪瞋癡,顯發四聖諦十二因緣法住法空之理趣,證無上正等正覺,成佛,時三十五歲。
牟尼是能仁,聖者之義,釋迦牟尼就是釋迦姓聖人。而所謂佛陀,過去有無量佛,未來也將有無量佛,現在世也有無量佛,釋迦牟尼是專有名號,故名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最初在波羅奈鹿野苑中度憍陳如比丘,最後在俱夷那竭國雙樹林中度須跋陀羅比丘後入滅。我們若把釋迦牟尼佛定位於歷史人物,釋迦牟尼佛既已去世,以世間人文知識來看,從此世間無此佛。自詡現代學者之流,往往稱許釋迦牟尼佛爲諄諄教誨衆生不知厭倦的宗教家,稱讚他人格偉大,殊不知這是殺佛,爲什麼呢?
世間思惟只承認現前實在的宇宙人生,不承認三世之宇宙觀,既不承認三世宇宙觀,建立在三世因果的四聖諦十二因緣法便被曲解爲世間法,超越人文知識的經句法語一概變成虛妄語,釋迦牟尼佛既然善說虛妄語,而又稱讚他人格偉大,這是殺佛再敷衍兩句以用脫罪之辭。
如果我們不設限於世間思惟,我們沒有理由武斷說現前的人類文明是宇宙間唯一的文明,也無法武斷現前的人類文明之前沒有更先進的文明。我們所面臨的世界,包括歷史地理以及各民族文化,都只是循業所見,譬如小學生便只見小學程度的知識,大學生便獲知大學程度的知識,若超越大學生程度便又別有發現。因此,我們不能以世間思惟的狹隘知見否定三世宇宙觀,只把釋迦牟尼佛定位於人間的歷史人物。
若開放世間思惟,一切佛經,無論大小乘經都鮮活起來,宇宙之寬廣令人心花怒放,我們能信受佛法,相信釋迦牟尼佛之前有無量佛。現前世間存在的宗教思想,如婆羅門梵,如基督教上帝,如儒家之天,如道家之道,如相似佛法中之如來藏,自性,眞如,如耆那教素食苦行論,無非也是過去先佛流布於世間而變質之法,當人類文明發展到成熟階段,各區域民族依其文化背景發展出不同的宗教思想及教義,釋迦牟尼佛也出現於世間再開示顯發佛法,重整人類對宇宙萬法的迷思,所應說已說,所應度已度,便入滅了。
據此而知,釋迦牟尼佛所開示顯發之佛法不是受印度婆羅門文化之影響,也不是取自耆那教或其他教之教義,而是藉用當地文化闡述佛法。釋迦牟尼佛入滅後,縱觀佛教史的演變,也沒有理由證明大乘 佛法創自凡夫之手。佛法變質咎由學佛人循業所見。釋迦牟尼佛入滅了,如來終不終,見不見佛都是個人知見,用世間思惟終將不見佛,無正法律可學。

